伊沙:永遠有“做到”的目標而無“得到”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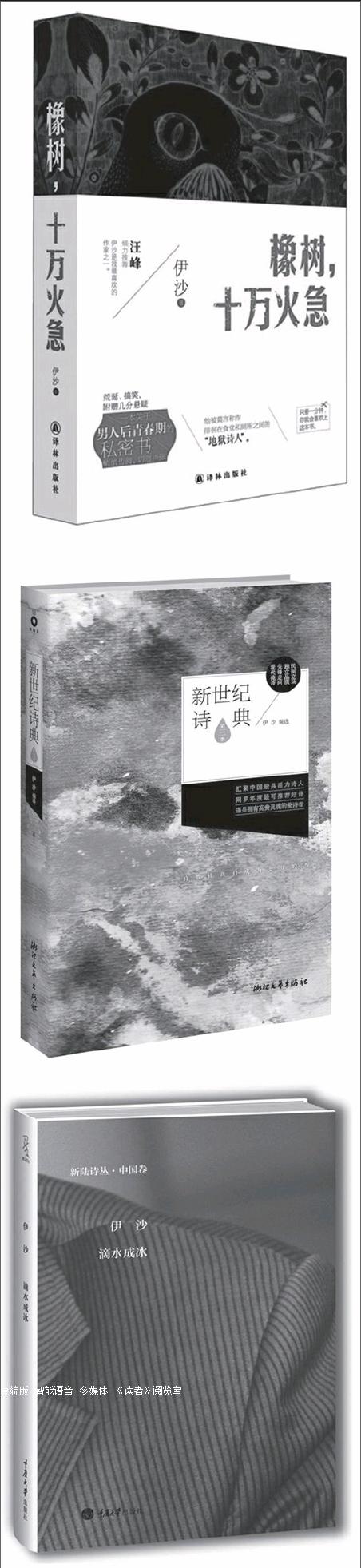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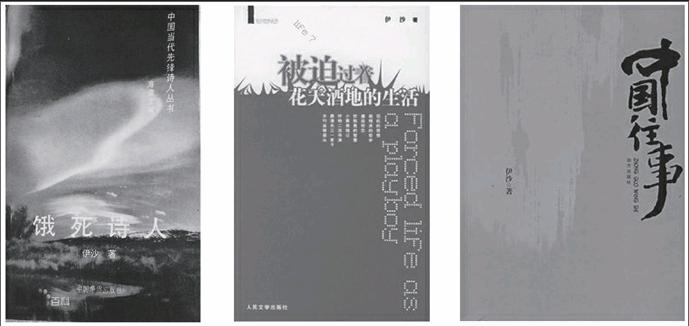
伊沙,原名吳文健。詩人、作家、批評家、翻譯家、編選家。1966年生于四川成都。1989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xiàn)于西安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任教。出版著、譯、編70余部作品。獲美國亨利·魯斯基金會中文詩歌獎金以及中國國內(nèi)數(shù)十項詩歌獎項。應邀出席瑞典第16屆奈舍國際詩歌節(jié)、荷蘭第38屆鹿特丹國際詩歌節(jié)、英國第20屆奧爾德堡國際詩歌節(jié)、馬其頓第50屆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jié)、中國第二、三、四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jié)、第二屆澳門文學節(jié)、美國佛蒙特創(chuàng)作中心駐站作家、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為其舉辦的朗誦會、奧地利兩校一刊為其舉辦的朗誦會與研討會等國際交流活動。
回到“初心”
王 琪:伊沙兄你好!提起你的大名,在詩壇可以說一直享有盛譽,不但非常勤奮,也創(chuàng)作出一批影響深遠的詩歌,比如《結結巴巴》《餓死詩人》《車過黃河》等等,堪稱你的代表作,為什么你對詩歌這么多年如此熱衷?
伊 沙:王琪你好!用現(xiàn)在比較熱的一個詞,回到“初心”吧。在我很小的時候,上小學那陣子,就有“分行神圣感”(對不起,我又發(fā)明了一個詞),覺得詩歌高于其他文字,將寫詩看做非常偉大的事情,我后來所受的教育所學的知識佐證了我最初的認識。除了初心,還有際遇吧。2006年我的母校北師大舉辦了“知名校友作家返校日”的活動,蘇童跟我聊起他當年在北師大就讀時(大我五屆),也是詩與小說雙管齊下的,但詩只發(fā)過三首短詩,小說卻發(fā)表了一個中篇并且還獲了獎,于是他畢業(yè)之后就只寫小說了……我跟他際遇相反,詩發(fā)了有二三十首,小說一篇未發(fā),于是畢業(yè)后就先攻詩歌了。我13歲寫了平生第一首詩,17歲發(fā)表詩歌處子作,詩齡在三十年以上,還是覺得自己適合做這件事,是個天生的本質(zhì)的并且拒絕異化的真詩人,因此越來越熱衷,越寫越堅定,這沒啥奇怪的。
王 琪:是的,除了詩歌,你在小說、散文隨筆、翻譯等領域也成績斐然,比如你的幾個長篇小說、你翻譯的著作、你編選的書刊等等,都曾引起了熱烈的反響,這對于一位詩人嘗試文學創(chuàng)作的多樣化是非常可貴的。對此,你是怎么考慮的?
伊 沙:如你所說,我是一不留神我竟成了一個“全能王”,近一年里我有兩次向人提供簡歷,一次寫的是“文學家”,一次寫的是“文學家,主要是詩人”。至于我是怎么考慮的,這不是一個老謀深算的結果,你得真有才華,并且做過專業(yè)準備。譬如小說,如上一問的回答中所供述的,我在大學期間寫了一堆小說,有短篇有中篇,只不過未發(fā)罷了,但我訓練了自己;譬如翻譯,我1995年就與妻子老G將布考斯基的詩首譯成中文,那時候現(xiàn)在好多活躍的翻譯家還沒上手呢。我想人的一生,所謂“圓滿幸福”,就是要盡量多地去實現(xiàn)自己各個階段的心愿,少留遺憾。當然,我也是紅塵中人,不是沒有功利心,有人不是哭著喊著蒙著騙著要當“大師”嗎?我真當一個給你看看,尖,咱們就比尖;專,咱們就比專;寬,咱們就比寬;厚,咱們就比厚;重,咱們就比重。得到與否是身外之物,做到?jīng)]有是分內(nèi)之事。
王 琪:在詩壇上,你是出道非常早的,而且至今仍然在堅持不懈地寫,我想聽一聽你的文學追求是什么?相比來說,你更愿意讓自己成為一名詩人,還是一位小說家、散文家?
伊 沙:這個問題是這樣的:我想我終其一生全部的作品將回答這個問題——好在我有追求,且都放在了作品里面。我當然最愿意成為詩人——我相信在中國詩人中我這樣回答的誠實度最高——因為大概只有我真心覺得:做一名詩人是最牛最高的,“詩人的桂冠,用國王的王冠也不換”(莎士比亞語)。
爭議不可避免,我習以為常
王 琪:在很多人看來,你是一位有爭議的詩人。有爭議某種程度上也是好事,你對自己是如何評判的?
伊 沙:“網(wǎng)絡時代,誰無爭議?”——有一次我在網(wǎng)上對加在我頭上的這個俗詞兒表示抗議,廣西詩人劉春(你好像也認識?)說,一般人誰關心他(她)有無爭議,只有影響大的才談得上爭議。那么好吧,那就繼續(xù)戴上這頂帽子吧。我是這么認識自己的:自1988年寫出成名作《車過黃河》迄今27年間,我一直是中文現(xiàn)代詩領域最前衛(wèi)最先鋒最創(chuàng)新的詩人(沒有“之一”),受爭議不可避免的,我習以為常。
王 琪: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你極力倡導并推崇口語寫作,而且你非常注重與國際“接軌”,比如翻譯國外優(yōu)秀詩人到國內(nèi),又將國內(nèi)詩人推介到國外,由此可見,你為推動詩歌的發(fā)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你的初衷是什么?
伊 沙:如你所知,我在北京讀的大學,對比之下深知陜西在信息、資訊、意識、平臺上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我記得當年畢業(yè)離校當日一大早,藍棣之老師(當年在北師大,后調(diào)清華現(xiàn)退休移居美國)來跟我道別,他說:回西安創(chuàng)作沒問題,搞研究就會有問題——說的就是這個差距。我怕自己一步退回來退成一只井底之蛙,所以很注重與北京甚至國外的聯(lián)系,這個好習慣一直保持至今。中國這三十多年就是在艱難反復地“走向世界”,我是其中一份子。
王 琪:當今的文學觀念、生態(tài)環(huán)境呈多元化,對于當下仍以傳統(tǒng)抒情的方式進行詩歌寫作,你有什么看法?是否由近代歐美發(fā)展起來的自由詩更有發(fā)展前景?
伊 沙:我所在的圈子是這么劃分的:“新詩”與“現(xiàn)代詩”(參見徐江詩論《新詩與現(xiàn)代詩》)。我的立場肯定是站在后者一邊的,更為具體地說是站在現(xiàn)代詩中的口語詩這一邊的(參見拙論《口語詩論語》)——這是我作為詩人的立場,作為編選家(《新世紀詩典》編選者),現(xiàn)代詩的外延是我接受的疆域(包括抒情詩與意象詩),新詩是我拒不接受并在言論上經(jīng)常討伐的。
王 琪:詩歌寫作有時是信手拈來,有時需要提前做功課的,你通常屬于哪一種?
伊 沙:兩者都有,短詩寫作前者居多,長詩寫作全屬后者。
我的“鄉(xiāng)愁”和經(jīng)歷有關
王 琪:你老家成都,出生西安,后求學于北京,畢業(yè)后又回到西安工作至今,農(nóng)村生活可能經(jīng)歷得不多,對于一個長期呆在大城市的詩人,你是怎么看待“鄉(xiāng)愁”這個詞眼的?
伊 沙:是的,連“老家”這個字眼對我來說都很陌生,這是代代都在遷徙、移居的家族特有的情況,成都更準確地說是我的出生地。我履歷表上籍貫一欄填的是:湖北省武漢市——那是我父親的出生地,我祖父曾經(jīng)的工作地。兩歲就到西安了,我就是一個西安人,是喝冰峰汽水吃鐘樓小雪糕羊肉泡饃長大的典型的西安城里人,誰說城市人沒有“鄉(xiāng)愁”?我的故鄉(xiāng)就是我的城、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寫作,我所有的“鄉(xiāng)愁”都與此相關。
王 琪:你的母校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曾培養(yǎng)了很多活躍文壇一線的作家詩人,比如徐江、侯馬、桑克、沈浩波、朵漁等等,都是北師大的杰出校友。畢業(yè)后,你又分配至西安外國語大學任教,你覺得大學校園的文學氛圍對一個作家詩人的成長,起多大的作用?
伊 沙:周遭環(huán)境的影響,作用不可謂不大。但到了我這個歲數(shù),有些事情看得更清楚:也可以說是我們改造了北師大,在我入校的1985年,在校的師兄師姐中也有詩寫得好的(甚至在當時的全國校園詩人中意識領先的),但我感覺他們太滿足于做一名“著名校園詩人”了,一個小范圍的才子才女,我有一個鮮明而強烈的意識:打出校園去!介入到中文現(xiàn)代詩的發(fā)展進程當中去——我的意識影響了我周圍的同學甚至于后來的師弟。至于我后來教書所在的西外,我更要感謝它,我在49歲這一年已經(jīng)出版了74本書,并不算老,“著作等身”,我想說:沒有大學教師這份相對清閑的職業(yè),沒有中文專業(yè)在西外邊緣化的地位所帶來的輕松,我不可能寫這么多。
王 琪:很多作家詩人寫作時,比較注重周圍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請問你一般是在什么狀況下提筆寫作呢?比如喝酒之后,還是夜深人靜,或者有感而發(fā)、提筆就寫?
伊 沙:謝天謝地!我兒子吳雨倫開始寫詩了(《詩潮》3期、《延河》4期上都刊有其作),這是令我無比欣慰的事。更令我欣慰的是,作為一名95后,他竟然表現(xiàn)出罕見的多思,一首詩要想很久才寫。起初我以為這與我不同,我總是相信直覺出手很快,但后來越來越發(fā)現(xiàn),我與之相同,還是會想很久。沉淀久,想得多,寫則快,所以我雖然寫得多,但成活率卻很高。是我兒子讓我看到了自己的真相。我的詩一般不含酒精,不分晨昏。
“無冕之王”比“桂冠詩人”厲害
王 琪:迄今為止,你出過幾十部著作,其中2004年以長詩《唐》單行本獲首屆“明天·額爾古納”中國詩歌雙年展“雙年詩人獎”,并獲得兩百畝牧場的巨獎,可以說轟動一時。時隔11年,這兩百畝牧場如今怎么樣了?
伊 沙:時間過去很久了,具體情況不大清楚,我只是希望它永葆牧場的模樣:年年歲歲,綠了又黃,風吹草地見牛羊。
王 琪:你因為寫作獲獎無數(shù),坊間流行這么一句話:真正的獎項不一定是官方頒發(fā)的,相比更具公正性和透明度的,其實是民間獎。關于名目繁多的評獎活動,你怎么看待?
伊 沙:實話實說:我只關心我獲過的獎和我評出的獎。詩歌乃至文學并非典型性“競技”,為獎項寫作的人行之不遠,謀獎、跑獎、買獎更不是真詩人所干的勾當。作品不硬,得再多的獎也全然無用;作品過硬,即使不得任何獎,也是“無冕之王”——在文學藝術的王國里,“無冕之王”可比“桂冠詩人”厲害多了。
王 琪:了解你的人都知道,你是詩壇內(nèi)外人人知曉的鐵桿球迷,六七年前,我就曾在央視無意中看到過你在球賽直播間進行的現(xiàn)場評述,是不除了寫作,看球賽是你最大的愛好?
伊 沙:是的,從小到大的愛好,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喜歡。加繆說什么來著:“我明白了足球永遠不會從你預料的方向過來。這個道理在生活中幫了我大忙,特別是在大城市和那些言行不一的人群中生活的時候。”“只有通過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靈魂”、“足球教給我們道德和責任”……說得真好,足球一直伴我成長,給我足球內(nèi)外的東西很多,我以為,熱愛足球的孩子長大后不會成為猥瑣之人或陰暗小人,做文學也會有血有肉有骨頭。
王 琪:生活中你更希望自己是一個優(yōu)秀的大學教授,一個稱職的兒子、丈夫和父親,還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詩人呢?
伊 沙:一個都不能少。因為有愛,必須盡責。
陜西主流文學的生態(tài)首屈一指
王 琪:你是中國先鋒詩歌代表性人物,也是國內(nèi)外重大詩歌活動、詩歌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你認為陜西詩歌在全國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伊 沙:數(shù)一數(shù)二,坐二望一。四年前你要問我,我還真不知該如何回答,甚至于我還一直以為陜西是現(xiàn)代詩欠發(fā)達省區(qū)呢。但現(xiàn)在是四年后,我已經(jīng)做了四年《新世紀詩典》,在四年入選首數(shù)的排名中,第一季,陜西第二;第二季,陜西第一;第三季,陜西第二;第四季,陜西第一,另外兩個第一名和另外兩個第二名都是北京。對比之下,大家看得清楚,北京有多少“北漂”?陜西有多少“陜漂”?你便知道這塊厚土之厲害,數(shù)千年傳統(tǒng)之強大。我本以為自己是這塊土地的“異數(shù)”、“逆子”,現(xiàn)在看不過是必然產(chǎn)生的果熟蒂落的結果。
王 琪:閻安老師2014年曾以詩集《整理石頭》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相信你一定讀過這部詩集,請你以客觀、真誠的態(tài)度,對這部獲獎詩集作以評價。
伊 沙:前兩天我還在感嘆:閻安是中國最有膽識的詩歌編輯,從《延安文學》到《延河》始終如一——誰來見證這個事實?我們這些當作者的不說出來,大概就無人指認了。這是由人所決定的,我很喜歡、欣賞、欽佩他這個人,挺二,挺狠,敢干。他作為一個陜北人倒更像關中人說的“冷娃”,用我的話就是“男子漢”、“很爺們兒”。1995年,我和他還有李巖出現(xiàn)在同一屆“青春詩會”上,有“同窗之誼”,從此以后,他一直很幫我,他是在作協(xié)體制內(nèi)少數(shù)公正待我的好人之一,在陜西更是如此。他的詩集獲魯獎,我替他感到高興,在第一時間在新浪微博上祝賀他!我并不認同那個獎所代表的價值觀,但我為朋友得償所愿而高興。我知道他一直在追求一種宏大、冷峻、哲學的詩歌,并且在自己的追求上越寫越好,《新世紀詩典》已經(jīng)推薦了他兩首佳作,即將推薦第三首。我覺得所有陜西詩人都應該感謝閻安。在他來西安之前,陜西文學的主流話語中已經(jīng)沒有“詩歌”二字多年了,是他憑借一己之力改變了陜西主流文學的生態(tài)。
王 琪:人常說:五十知天命。就在將要進行這次訪談之際,你剛好過完49歲生日,明年年滿50了。對于將來,你還有什么樣的創(chuàng)作計劃和人生目標?
伊 沙:我確實是個愛做計劃的人,這與我生在一個科學之家有關。我也確實是個敢于提前發(fā)布自己計劃的人,不是顯擺能耐而是督促自己: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但未來10年的計劃我不想在此公布了,50—60歲這一段,身體最重要,我會慢下來,一項一項,扎扎實實,繼續(xù)提高成活率。目標嘛,我永遠有“做到”的目標而無“得到”的目標。
王 琪:時間過得真快,我們這次的對話就要到這里結束了,謝謝伊沙兄支持!
伊 沙:謝謝王琪!
許多年過去了,伊沙兄以詩得名、以詩傳名,且一直活躍中國詩壇,被傳為佳話。他也因盛產(chǎn)小說、散文隨筆、譯著等,而在文壇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
一座偉大的城市,不因她在歷史長河的時光流轉中失去她煥發(fā)的青春、詩意的棲居,是榮光和值得驕傲的。對于久居長安,擅于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的伊沙兄來說,他的靈魂里無疑注滿了詩歌的力量,愛的情懷。他在詩歌藝術之路上,求新求變,勇于探索,起到了“帶頭羊”的作用。他的詩歌從傳統(tǒng)抒情寫作到口語寫作,從早期青春夢幻式的書寫到生命意識的開掘和社會人生的多維度表現(xiàn),已經(jīng)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展現(xiàn)出獨立的個人寫作姿態(tài)。
這,正是一位真詩人的集中體現(xiàn)。我由此祝福伊沙兄!
責任編輯:閻 安 馬慧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