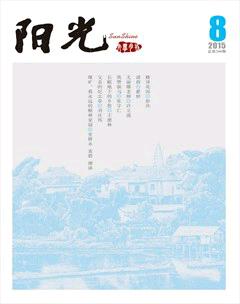煤礦,我永遠的精神家園
史修永 袁碧 譚談
時間:2015年1月
地點:毛澤東文學院
史修永:譚老師您好,非常榮幸能有機會向您請教關于文學創作方面的問題。在中國當代文壇上,您一直堅持創作煤礦題材的文學作品,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您曾說:“煤礦,在有些人看來,是一個又臟又危險的地方。不知怎的,我卻覺得這里好,待在這里,心里就踏實許多。”請您談談,你和煤礦有著什么樣的感情,為何您如此執著于創作煤礦文學?
譚 談:這要從我的出身和成長說起,我的家鄉就是煤礦區,我很小就進了煤礦,可以說是在煤礦長大的,我在那里參軍入伍,復員后又回到那里,在煤礦前后工作了13年,我的童年伙伴也好,難忘的人生記憶也好,全都跟煤礦有關。煤礦養育了我的生命,也養育了我的文學夢。這些難忘的記憶印在心里,伴隨著我的創作過程,體現在我的作品中,成為我創作的源泉。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山道彎彎》是寫煤礦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風雨山中路》也是寫煤礦的。當然,我也寫過一些其他題材的作品,如寫政治改革的《橋》《美仙灣》等,但無論什么題材的作品,都能從中找到煤礦的影子,都能找到與煤礦相關的人物,都能感受到我在煤礦養成的性格和精神面貌,這是我對煤礦真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非刻意安排。雖然我離開煤礦已有幾十年,但我跟煤礦朋友們的情誼并沒有因時間而淡化,到現在我還經常回煤礦去看看我的老朋友們。我甚至在礦區買了套房子,并取名為“三友會所”,“三友”即工友、戰友、文友。我和我的朋友們經常在那里相聚,交流思想,交流創作題材。我們湖南作家中有很多都是礦工出身的,如姜貽斌、賀曉彤都是從煤礦走出來的作家,我經常組織他們一起回礦里去看望礦工朋友們,并取名為“工人作家回娘家”。我和煤礦、礦工的這種割不斷的感情伴隨著我的人生,我把煤礦作為自己永遠的精神家園。我希望煤礦越來越好,也希望礦工們越過越好。
袁 碧:您在《人生路彎彎》中曾經說:“我雖然深深地愛著煤礦,卻又感到反映煤礦生活的作品委實難寫。井上井下,黑乎乎的,缺少色彩。”在寫作過程中,您是如何克服這個困難的?您認為煤礦文學與其他題材文學作品相比有哪些特點?
譚 談:我覺得煤礦作品比較難寫。相比而言,農村題材的作品色彩豐富,生活畫面更加亮麗;同時,農村地區有世代家族定居,時代之間的交叉、復雜的人物關系引發的恩怨情仇更容易產生吸引人的故事。而煤礦色彩單調,道路是黑的,煤炭是黑的,包括從礦井里出來的礦工都是黑的;礦工們在礦井里工作時間長,生活單調乏味。我曾經也苦惱過,煤礦題材的作品到底該怎么寫才出彩?后來我領悟到,無論是農村題材、城市題材還是煤礦題材的作品,其實質都是寫人。文學是人學,因此文學創作的關鍵是要塑造出生活于一定環境中的人,這些性格各異的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共同構成了作品的特色。煤礦文學就是要書寫礦工,表現他們的內心世界和生存狀態。把握好他們的性格特點和生存方式,實質上就表現出了煤礦文學的特點。比如煤礦環境的惡劣和工作的辛苦造就了礦工們的獨特的性格;礦工身上有著特殊的記號,如果他們在工作中受傷了,煤就會埋進傷口里,煤炭和血液融在一起,傷愈后慢慢變成墨綠色的煤瘢,煤的色彩就永遠留在身體里……把這些特點表現出來,作品才有煤礦的味道,而這正是煤礦文學創作的亮點和難點。
史修永:因此,在創作的過程中,您特別注重刻畫人物的特色,著力表現人與人之間復雜的關系。
譚 談:是的。打個比方,假如你走在大街上,能吸引你注意的通常是那些長得非常漂亮或非常丑陋的人,正是他們的獨特性吸引了你的目光,而那些長相一般的很難引起人們的注意。同樣的道理,寫作中比較重要的就是要寫好人物特色、設計好人物之間的關系,挖掘出吸引人的特點來。我的長篇小說《風雨山中路》寫了很多年,但我總覺得差了那么一點點,差在哪兒呢?《山道彎彎》的成功帶給我一些啟示,即小說創作必須要從人物塑造、人物關系設計上突破。《山道彎彎》中的金竹和二猛之間的叔嫂戀讓一些讀者難以接受,他們建議我為金竹安排一個妹妹,讓她嫁給二猛,這樣就能避免倫理沖突。然而,如果這樣安排,《山路彎彎》根本就無“彎”可言了。這讓我意識到人物關系對文學作品的重要性,因此,我把《風雨山中路》中的人物關系做了一些調整。小說中的主人公某煤礦黨委書記岳峰是一個忠誠正直的老干部,而我卻把他的老婆由一個善良賢淑的女性寫成一個自私、虛榮的女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生活在一個家庭里,故事就是從這種善與惡的強烈對比和沖突中生發出來的。這種反常的人物關系的設計,為小說注入了鮮活的血液,讓人印象更深刻,也更容易打動人。果然,我這樣修改了之后,《風雨山中路》獲得了成功。可見,無論寫煤礦也好,寫農村也好,寫城市也好,寫改革也好,都要寫好人物,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設置巧妙的人物關系,這樣,作品才能夠成功。
袁 碧:您剛剛說,煤礦色彩單調,但是我讀您的作品,不但沒有感到色彩單調黯淡,反而覺得您筆下的煤礦區帶有湘中山區的詩意美,充滿生機和活力,是一個富有詩意美和人情味的空間,因此,讀您的小說會有一種力量感和希望感。您能談談您構建這樣的詩意的礦區空間的用意嗎?
譚 談:我創作《山道彎彎》這部小說正是“傷痕文學”盛行的時候,當時控訴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文學、電影很流行。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的確,現實生活中充滿黑暗面,煤礦也是“黑乎乎”的。然而越是黑暗的地方,越能看到光亮,除了黑暗之外,煤礦還有很多優美的東西,這種美不應該被我們忽視。我寫煤礦礦工及家屬們,表現他們身上溫暖的人性之美,并結合充滿生機的山區來寫,如礦山上的花草樹木,山溪里的魚蝦、螃蟹,將這些充滿生命力和情趣的意象寫到作品中。我覺得文學不能把所有的鏡頭都對準黑暗和丑陋,我要在我的作品中表現出美的一面,讓人們感受到那一段歷史并不是只有黑暗,那段歷史中的人也并不是全是壞人,把這些美的東西呈現給讀者,給人以生活的希望和動力。
史修永:您是不是有意識地想跟當時的主流如“傷痕文學”區別開來?
譚 談:是的。我不愿意跟著主流文學走,我想從中跳出來。我在作品中塑造的環境、塑造的普通礦工都能跟主流文學區分開來,這跟我的個人經歷是分不開的,我當兵的時候,社會上正好是“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當我復員回礦當工人的時候,正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當我當上了記者、作家的時候,又正是全國上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候。和其他作家相比,我很幸運,我沒有被打成“右派”,我的生活經歷賦予了我獨特的創作素材和生命體驗,因此在作品中表現的內容與主流文學有所區別。
史修永:在許多煤礦作家的作品中,男性通常是被書寫的主體,女性大多在作品中作為男性的陪襯而存在,而在您的作品中,讀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您對每一個生命、每一個個體的靈性的表達和尊重,這尤其表現在對礦區女性的關注,即使為生活所迫,您也舍不得讓她們淪為生活的奴隸,她們身上依然閃耀著人性的光芒,呈現出善良樸實、賢淑忠厚等中華傳統美德。您能談談為什么您對礦區女性如此關注并賦予她們以美和善的個性特征嗎?
譚 談:我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礦區女性形象,尤其是寡婦形象,為此,有人說我是“寡婦作家”。自古以來,做女人比做男人更難,在農村是這樣,煤礦更是如此。而女性當中,寡婦的生活是最艱難的,她們的苦難是最深重的。我決定寫她們是由于在礦上聽到幾個真實的故事,這些真實的故事對我觸動很大。有天晚上,一個礦工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悲慘的故事:一個礦工死了,按照當時礦山的政策,未滿30歲的妻子可以頂職,而他善良的妻子則認為礦山更需要男性,于是她放棄寶貴的頂職機會,讓小叔子代替自己去礦里工作。后來在家人的撮合下,她和小叔子結了婚。婚后半年,小叔子也出事故死了。我聽了這個悲慘的故事后非常難受,我覺得我應該為她們做點兒什么來顯示社會對她們的尊重。在我當了記者以后,我給湖南出版社的《芙蓉》雜志編輯講了這個故事,并表明我想寫這個故事,想寫那些默默支持著煤礦事業的礦工妻子們。他很贊賞我的想法,并問我:“你的創作主題是什么?”我說:“我想寫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特別是表現在女性身上的傳統美德。”礦山女性身上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這種美不應被遺忘,應該通過她們傳遞出來,傳承下去。后來我將我所聽到的礦山女性的故事和我小時候從老人們那兒聽來的田螺姑娘這一民間傳說結合起來,寫進了中篇小說《山道彎彎》,發表在1981年第1期《芙蓉》雜志上,贊美那些默默奉獻自己的光和熱的礦工妻子們。這期刊物出來以后,我的那篇小說被很多刊物轉載,如《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等,也被很多廣播電臺廣播,另外還有60多個電視臺將其改成地方戲劇,可以說,這篇中篇小說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影響,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肯定。
史修永:同樣作為湖南作家,沈從文曾說:“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傾向不可分。”水成為他追求素樸人性美的載體。作為大山的兒子,山與您的成長和創作分不開,您的許多作品都與山有關,如《山道彎彎》《風雨山中路》《山女》《山霧散去》等等,在您的煤礦作品中,礦工們都如同大山一樣,沉著憨厚而內心蘊藏著巨大的能量,是否可以說,山和您的創作的關系,就如同水和沈從文創作的關系一樣?您是怎么理解“山”的?
譚 談:沈從文的作品我非常喜歡,我看了不少。但是周立波的作品對我影響更深。的確,我的文學作品中有很多的“山”,我的家鄉在山區,我所在的煤礦也在山區,開門見山,開窗戶還是山,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大多數作品都離不開山村、礦山、山民。首先,大山為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我的作品中有不少都是來源于礦山里的真實故事,如《山霧散去》《山女淚》《山女》等。有一次,我和姜貽斌從一個招待所女服務員那兒聽到這樣的一個故事:一位勞模采煤工人在一次事故中毀容了,礦工們本來就很難找老婆,毀容后就更難了。為了解決這位勞模具體的困難,礦領導做出一個決定:招工,哪位姑娘愿意嫁給他,就為她安排一份礦里的工作。不久,一個漂亮山區姑娘嫁給他了,但是婚后這位山區姑娘生活得并不幸福。在我們去采訪的時候,她總是完全不做聲,眼睛里還有眼淚,表現得非常憂郁。原來是因為礦里給了她很多的榮譽,她沒法跳出這個籠子去尋找自己真正的愛情,她覺得很痛苦,卻又對現實無奈,沒有辦法。這使我們非常感慨,我覺得從中可以挖掘出很深的內容,于是,我就寫了一篇中篇小說《山影》。另外,我認為山特別能體現礦工精神。礦工有山的性格,有山的擔當,他們像山一樣厚重沉穩、富有力量感,礦工是大山的希望,也是礦區的脊梁,他們外表平常,內在卻蘊藏著豐厚的寶藏,這正是礦工精神之所在。
史修永:您剛剛談到“礦工精神”,您也曾感慨過:“煤礦,有那么一種精神!礦工,有這么一種精神!”您能具體談談這種“礦工精神”嗎?
譚 談:我曾經寫過一篇散文叫《發光發熱的土地》,就是贊美礦工精神的。礦工是社會中最有擔當的一個群體,他們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下井工作,等他們從井下出來的時候,天早已黑了,為了工作,他們每天幾乎見不到陽光,而他們采出來的煤炭,被送到發電廠、鋼鐵廠等,在社會各個領域發光發熱。他們默默無聞地在黑暗的礦井里奉獻著生命和青春,送給別人的卻是光明和溫暖。礦工就是一塊煤,在沒有被投到爐膛之前,他們黑不溜秋的,很普通,很不顯眼,但是一旦被拋到爐膛里,他們就化為熊熊火焰,發光發熱。我在礦上碰到過好幾次這樣的事情,有一位礦工姓曹,平時沉默寡言,表現并不突出,別人甚至認為他是落后分子,但是在一次事故中,他勇敢地沖上去,犧牲了自己,挽救了別人。礦工們大多文化程度低,講不出大道理,又很老實,當眾發言時臉憋得通紅也講不出幾句話來,但是他們淳樸憨厚、正直善良,內心涌動著巨大的能量,一到關鍵時刻,特別是在工友們有危險的時候他們總是走在前面,把危險留給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給別人,用實際行動溫暖他人。
史修永:您多次提到湖湘文化,您怎么理解湖湘文化?
譚 談:湖湘文化是由苗蠻時期的部族文化、戰國的方國文化浸淫發展而成的一種文化,它是地域文化的一種,主要在湖南地區傳播,在這種文化的滋養下,湖南人的性格大多有一股韌勁,總結為一句話就是“吃得苦,霸得蠻,敢為人先”。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敢面對別人不敢克服的困難。這條文化河流孕育了一批批英才,從曾國藩、譚嗣同到毛主席、彭德懷,他們都有湖南人倔強的性格,不怕困難,不怕吃苦,不怕犧牲。
史修永:那么這種文化對您的創作有什么影響?
譚 談:文學創作不是一個復制的過程,文學創作者就是要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要有敢為人先的反叛與創新精神,而這恰巧也是湖湘文化的一種。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地域文化養一方人。在我很小的時候,老人們給我講的民間故事、神話傳說,都體現了這種文化。我在我的小說中引用過很多民間流傳的神話故事,如長篇小說《美仙灣》一開頭就講了仙女戲水的故事,中篇小說《山道彎彎》里講了田螺姑娘的故事,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色彩。這種文化精神滋養著我的生命和文學,不管走多遠,不管后來的環境發生什么變化,這種文化印記都不會被時間抹去。
史修永:您不但自己潛心創作反映礦區生活的文學作品,而且還鼓勵并支持青年礦工們參與到煤礦文學創作中來。可以說,您非常重視培養青年礦工作家。您覺得青年礦工走向創作之路有哪些困難?您對當今煤礦青年作家的創作有那些建議和期望?
譚 談:青年礦工作家在創作的過程中主要面臨兩個問題,一是經濟問題,礦工們大部分家境困難,他們要為生存而奮斗,無法集中全部精力進行文學創作;二是文化知識問題,許多礦工文化水平不高,而文學創作正是需要文化知識的支撐。根據礦工們存在的這些問題,我們做了一些工作,如建立文學扶助基金、青年文學獎、毛澤東文學基金等,主要幫助青年作家和老年作家,鼓勵他們創作,通過這些基金推出了一大批在全國產生影響的作家,如蔡測海、何立偉、葉夢等;另外,我們建立毛澤東文學院作為青年作家培訓基地,由作家協會和省委宣傳部門出資,每年培訓40到50位青年礦工作家,培訓開設文學交流活動、大家講堂,并邀請王蒙、張煒、陳建功等文學家們為礦工作家做文學講座,這對青年作家有很好的引導作用,他們有了更多的學習和文學交流機會,這為他們快速成長提供了有利條件。煤礦環境艱苦,但是煤礦也走出了很多有影響的作家,如陳建功、劉慶邦等,我們湖南的“湘軍七小虎”中有兩位作家也是從煤礦走出來的,環境改造人,環境造就人。青年礦工們是光明的采掘者,我相信,只要他們抓住機會努力奮斗,展現自己的才華,他們的文學創作之路也一定會更加光明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