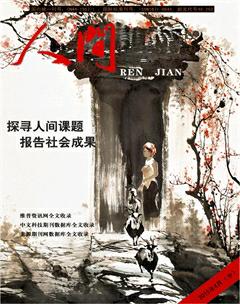《黃金時代》是怎么“敗給了”《小時代》
作者簡介:李新宇,女(1993-11-7),民族:漢族,籍貫:山東省濟南市,當前職務:學生,當前職稱:學生,學歷:本科,研究方向:戲劇影視文學。
摘要:美學是研究人與現實審美關系的學問;電影美學,則是針對電影的“美與丑”進行思考的一種方式。在美學中有很多特征與分析方法,本文旨在從美學的審美規律性即從審美關聯律、審美權重律、審美穿透律來分析影片《黃金時代》,探討以《黃金時代》為例的國產文藝電影的“失敗”。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5)04-0140-01
關聯性的機理是,個體因為對象的某種關聯性而感到親切或者疏遠,或者是個體因為對象形式本身所具有的關聯性而被打動了;審美穿透律的定義是對于對象的整體結構與人的生命結構相對應,產生共鳴,從而使個體產生一種“被擊中了的感覺”。 審美權重律,在促成審美感受的眾多因素中,每種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即審美因素的指標化和多元化不同,是有不同的量化標準和多維度的。時代不同、性別不同、國家不同等等其審美的標準都是不同的。
一、從審美的規律性分析電影《黃金時代》的“失敗”
(一)從審美關聯律分析《黃金時代》。現在,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發展,人們都開始普遍重視精神生活,看電影的人群也不再為了研究學術或者單純的電影專業的“電影觀眾”,而是更多的缺少最起碼的電影只是與文化素養的“非電影觀眾”。“非電影觀眾”幾乎占據了觀影人的絕大部分,而他們看電影僅僅是為了消遣或者是當做情侶間談情說愛的催情劑,對于這樣一個民國時代的傳奇女作家——蕭紅,他們沒有更多的認識與認知,最多也只是去看劇情,看故事,但是當一部電影擔起電影的責任,做深,做厚重,而看得人因為缺乏相對應的文化素養,不能與電影所講述、所展現的事物同“深”,同“厚”,那么這時,觀影人就與電影作品之間產生了隔閡,一條無力逾越的“洪溝”。“洪溝”里的《黃金時代》制作的再精良用心,故事講的再完整,歷史還原的再客觀,人物塑造的再個性真實,都是無能為力的,“洪溝”外的“非電影觀眾”不愿意“屈身”去看、去救,甚至還會沖著在“洪溝”里沒有放棄掙扎的《黃金時代》留下自己的幾口唾液,并對后來的人說,“別看了,別靠近,撈他上來多麻煩,我們換個熱鬧看去。”所以這時,他們看到了《小時代》里奢靡的生活,華麗的衣服,看到了《后會無期》里青春的“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傳奇的際遇等等,直觀、淺入淺出的感官刺激輕易的滿足了“非電影觀眾”們的心理需求,他們滿心歡喜的追捧著、把這些電影供奉在最高的山頭,以為這山就是“神”,盲目的樂觀著,甚至覺得都可以與另一個叫做“好萊塢”大山相匹敵,相媲美,殊不知,自己這座“山”根本經不起風吹日曬,一旦崩坍就是萬劫不復。美學審美關聯律中提到:關聯律的基礎是人對事物的關注。而不被關注,被置于、遺忘于“洪溝”里的《黃金時代》,終還是等到一些搭救自己的人,他們關注蕭紅,關注蕭紅的時代,關注蕭紅時代的文化,他們看到了《黃金時代》的認真與努力。
(二)從審美穿透律分析《黃金時代》的“失敗”。生死,故事的內核本就是主人公蕭紅從生至死的過程;愛恨,與蕭軍、與端木蕻良的愛情情仇交織與蕭紅的一生;戰爭,這更不用說,大背景就是戰爭下文人們的覺醒與反抗。盡管如此,“他們另擇路徑,沒有試圖去捕獲蕭紅,而是環繞著她,以對蕭紅的記憶和講述去勾勒她的形象和所在。毫無疑問,這讓影片的接受門檻有點高了”。《黃金時代》,不像《小時代》中廣告與流行語的濫用與拼貼、十分鐘一個極度戲劇性的事件而后瞬間冰釋;《后會無期》,一個懸浮舞臺上的片段偶遇;《心花路放》,一個“開心麻花”式的舞臺劇,那么直接、直觀與容易觸摸,所以仍是不被“非電影觀眾”們所喜歡,所認可的。其實仔細用心、耐心看完這部178分鐘的電影,很多細微的地方都是會被善于讀解與愿意讀解的觀影者們所感動的。比如愛情,雖然沒有《小時代》里顧里、顧源互送的嬌艷名貴的玫瑰花、一起開著寶馬奔馳去赴的燭光晚宴,但是《黃金時代》里,蕭軍終于找到工作當了家教,二蕭與車夫們擠在一起幸福的吃著肉丸子,兩分錢的豬頭肉,還有那句“有肉得有酒啊”,處處是感動,但是“人們看到的是三人同床,看到的是蕭紅的吃,似乎那是一份風情,一種怪誕,好像我們已完全無法想象戰爭與災難的時代,不知饑餓、貧窮與匱乏為何物”。而走在冬日的街頭,蕭軍蹲下身子用玻璃割下自己的一節鞋帶給蕭紅系上,那樣的場景,著實感動著我,也一定感動了很多人。比如友情,雖然沒有《小時代》里有錢的可以給沒錢的朋友買別墅住,但是《黃金時代》中一直照顧蕭紅,危難之際幫過蕭紅的白朗、丁玲、羅峰、蔣錫金、駱賓基等等同樣讓人心暖。即使是這樣有一部著深刻“向死”與“向生”的電影,卻也是因為很多“非電影觀眾”的無知與文化、歷史的匱乏與空缺,讓電影中的感動無處安放。
(三)從審美權重律分析《黃金時代》的“失敗”。現在的人們只喜歡快餐文化,喜歡視覺瀏覽接受信息,很少還有保留著看書的習慣,而看書的也只有為數很少的一部分人還愿意捧起一本中國古典、現代文學書籍耐心讀解。更多的則是喜歡看韓寒、看郭敬明、看可以肆意揮霍的青春、看“或走就走的”的旅行,看“可以不顧一切愛一回”的愛情。《小時代》和《后會無期》正是響應了“大家”的心聲,而《黃金時代》,講蕭紅與蕭紅那個時代的一批文人,沒有側重講愛情,愛,就在一起,分開,就分開;沒有給一個觀眾都喜歡的“happy ending”,本就是講的歷史,歷史又怎么可能都是皆大歡喜,真實,本就是殘酷又平淡的。所以“非電影觀眾”們不喜歡,他們看不到自己想看的曲折離奇又引人入勝的“好故事”,也沒有看到自己想要的圓滿結局,所以,《黃金時代》“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