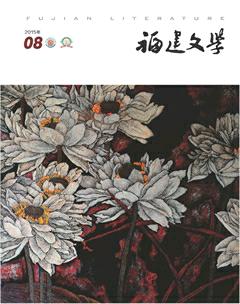神奇的酒釀
葉立夏
每到冬天,我都要釀酒,在自家的儲藏間里。
說是我釀酒,其實跟我無關。曲是老娘買的,飯是二姐夫蒸的,水是先生從戴云山深處載來的生泉。七十多歲的老娘人來熟,總能通過好人緣買到上好尤溪紅曲,一粒粒色澤鮮艷、色調純正、圓潤飽滿。飯是二姐夫放在大鍋上蒸的,這里面有不少講究:米要泡透,蒸飯的時候要不時開蓋點水,還要用筷子在小山似的米飯中戳幾個小窟窿,要蒸到飯粒膨脹發亮、松散柔軟、嚼不沾齒才算火候。量是要備足的,因為熱氣騰騰中上鍋時,誰都抵擋不住那樣的誘惑:隨手抓上一把,團在掌心,往嘴里一送,兒時守在灶邊等鍋巴搶飯團的記憶,就在舌尖上的松軟清香中融化了。下釀也不難,但我沒想學。為什么要學呢,有二姐呀。看她把蒸熟的糯米飯在竹匾上攤開、放涼,按一定的比例在酒壇中放入泉水,然后加一層米飯撒一層曲,再一層層攪勻……很簡單的,一看就會是不是?
剛下的釀,酒壇是不能封蓋的。由于發酵的力量,米飯和紅曲會不斷上涌,因此每天都要翻拌攪動,讓它們沉到最下面。這可是個苦力活。為了攪拌均勻,最好要用手。我個矮手短,所以這活兒我還是靠邊站——我是多么感恩我的小個頭呀!有一回先生外出,到家已經十點多了,又剛好寒流來襲,接近零下,他凍得臉發紫。可是一回來就脫外套,脫得只剩薄薄的秋衣,還得高高捋起袖子,看得我直發抖。我說,多冷的天啊,不然用飯勺吧,不然用撐衣桿?他說不行不行,撐衣桿不衛生,飯勺比你還要短。我說可是多冷的天啊,以后我們不釀酒了真的不釀了。先生想了想,找出跳繩跳一百下,又跳一百下,臉上血氣回來了。
那幾天我特別喜歡進儲藏間,因為總能聽到一些奇怪的美妙的聲音。辟辟撲撲,辟辟撲撲,是不斷膨脹不斷上涌不斷撞擊的無數小氣泡在嚷嚷。那一定是一趟奇異的旅程,酒曲、米飯和山泉一起,正在竊竊私語著它們一路上的小發現小歡喜。它們擠擠挨挨地說說些什么?這里面正在發生什么樣的事?——還有比酵場更不可思議的世界么,一邊腐朽,一邊神奇!我想扒開它們,仔細聽聽那樣的嚶嚶嗡嗡。可是我一動,那聲音就停下來;我一停下,它們又鬧騰起來了。后來我用手機和MP3進行種種嘗試,卻都沒法把那些神奇而細微的聲音錄制下來。原來有些聲音機器的耳朵是聽不到的,只有人的心靈才能聽到。
還有一些變化悄悄進行著。那之前,飯是白的,曲是紅的,水是清的,是來自不同世界的聲音,各走各的路。下釀之后,它們開始試探性地相互滲透,往白里摻進一點紅、紅里兌入一點香;慢慢慢慢地它們渾然一色不分你我,顏色變深變甜,變成了酡紅——還沒釀出酒來它們就自己先醉,醉成消隱了的漿果,醉成一整座秋天里的山。
古人造詞,妙不可言。酒曲之為“曲”,確實有音樂的婉轉曼妙。酒曲譜音,飯粒填詞,山泉主唱,在整個酵場里纏繞芬芳,余音不絕。七天之后,酒紅越來越深,酒香越來越濃,壇子卻要蓋上了,所有的聲音和氣味都被封存,酵場里的世界從此靜默如謎。但我知道,它們一分鐘都不會休息,一刻鐘都不得空閑,因為所有的佳釀都不會從天而降——那些來自不同方向的山泉、大米和酒曲啊,裝滿光,裝滿塵,裝滿大地的愛寵和原野的秘密,如今開始結伴遠行,走入另一個世界的芬芳!
差不多過了25天,壇子開蓋了,儲藏間芳香四溢,是音樂無孔不入的清透綿緲。這時候,糟是糟酒是酒,糟沉在下面一片暗紅,而上面的酒液卻清澈透明,是一塊琥珀亮亮汪汪。用勺子打上小半勺,入口又涼又甜、清冽芬芳,從喉舌入肚,又化成釅釅的暖,在血液里緩緩流動,再靜悄悄地抵達五臟六腑,抵達毛發指尖。可別急!還得在壇子里放個酒籮,下壓,讓酒汩汩地流進籮里,讓糟巴巴地留在籮外——這時候,你就可以放心打酒了。如果饞,你可以邊打邊喝的,不過小心,可別酒還沒打好,你就已醉倒在壇子邊上了。
說起來這釀出來的酒,也有等次之分。水多米少,酒精度低,酒色清澈淺紅;水少米多,那酒紅愈深、酒深成碧,是深秋老林里的暗生青苔。但無論酒深酒淺,這家釀的糯米紅酒,都一樣甘甜芳醇,補氣養血。德化海拔高,地氣濕,紅酒便是不可缺少的家常飲品。要是熱了鍋,茶油、生姜、地道農家雞,翻炒,然后“噗”一聲倒下大半鍋酒,小火慢慢煨,那煨出來的滿室飄香,就是德化頂頂有名的“月子酒”了。坐月子的時候,新媽媽是要把酒當水喝的。如果一喝就是一大碗,一天喝它五七次,那么一個月下來,壇子空了,媽媽胖了,寶寶也就壯了。
我怕酒,跟大姐一樣是站壇子邊醺一醺都會醉、吃一點紅酒調味就臉紅的人,所以月子里沒怎么喝酒。于是問題來了,體虛血冷,冬天遇風就起疹。醫生給我開了方,就是猛喝月子酒。我遵了醫囑,每到臨睡前酌它一小杯,連喝一個月,不但風疹好了,竟連深夜里痙攣的胃也聽話了。
怕是怕,但到過年就不同了。老娘有八個子女,連同孫兒曾孫已經三十多人,過年總要擺上三大桌的。當然是輪流請客。到了我家就只有一桌——為啥?那張乒乓球桌派上用場了。桌上放三個火鍋,三四十人鬧哄哄圍擠著,那煙火味十足的喧鬧簡直奢侈,不,簡直土豪!什么菜?無所謂;什么酒?“月子酒”——我家的酒就是為這個時刻釀的,我稱它為“年釀”。熱氣氤氳中,親人圍裹里,我們都像回到了母親的子宮,溫暖而又穩妥。酒入三巡,話多了,記憶里的時光跟著一一醒轉過來,帶著我們走進另一個神奇的酵場:那年老爹是多么固執啊,那年老娘多么不容易;那年二哥是多么調皮啊,那年三姐又多么爭氣;那年二姐幫我梳頭,我坐在條凳上,雙腳還懸在空中晃蕩呢;那年小弟誤把酒糟燉過的蘿卜塊當肥肉,一咬,哭了;去年小外甥帶外婆逛北京了,那么明年由誰陪老娘游臺灣?
我喝了一碗還是一碗半?反正以我的酒量不可能兩碗。我是容易失態的人,一喝酒就把持不住,大笑、抽煙、說瘋話。一樣瘋的是姨丈,怎么能少得了姨丈一家呢?——記得當時年紀小,我從鄉下到城里讀書,就像是劉姥姥進大觀園,周末到他家蹭飯,又像林黛玉般“不肯多說一句話,不肯多走一步路”。他卻從周五就開始準備,鹽水腌豆腐,加入剁碎的肉末和炸好的蔥花。吃飯時我當然眼睛只盯著自己的碗。姨丈也不說話,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夾菜。飯后我默默地收拾了書包,到客房假裝用功去了。不一會兒姨丈的腳步聲到了,他一樣不說話,卻悄悄地從窗戶放進削好的蘋果或者剝好的桔子——年年聚會,老姨丈都還是記憶中的模樣,高、胖,靦著大肚皮,笑得像彌勒。喝了酒,他那彌勒般的臉紅成關公樣,話多了,“抽煙,你抽煙,不怕他們,”拿出打火機咔一聲幫我點著了。本來該我給他請煙該我給他點煙的不是?我踉踉蹌蹌站起來,接煙、接火,卻撲通一聲坐地上去了。男人不為所動地繼續喝酒,女人手忙腳亂地跑來扶我——侄兒侄女外甥外甥女什么的,就別指望給我倒水醒酒啦,他們紛紛拿出手機,拍照的拍照、攝像的攝像,一一記錄我的丑態,傳到微博微信去了——那上面有個“家和圓”,連接著四面八方,是那些沒能趕回來過年的骨肉至親。
接下來,男人猜拳拼燒酒,女人八卦看春晚,孩子們嬉笑打鬧、到天臺燃放爆竹煙花……當然都沒我的份:他們押送犯人一般把我架進房間,扔到床上去了。接下來再接下來,新年跟舊年是怎么交替的?有哪些兄弟隨手拿過琵琶二胡和笛子,來一場家庭即興演奏會?又是誰家小孩假抱琴琶、陶醉其間,任由鼻涕在臉上橫流也無心擦去?唉,那樣芬芳濃烈的時光是酒,而我,我已經成了沉在底處、隔在籮外的糟啦!
責任編輯 林東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