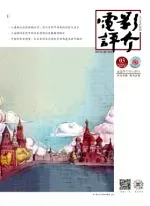從文學語言到電影語言:空間敘事策略的運用——以小說《昨日當我們盛年》電影改編為例
趙 嵐 王曉英
一、電影語言與文學語言
電影語言如何重現文學語言,一直以來都是電影對文學原著改編的關鍵所在,盡管電影語言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但由于文學語言與電影語言在表現上的差異性,造成兩種語言難以達到平行架構,從而使得小說文本在電影改編過程中或多或少地造成藝術效果上無法完整重現的窘境。然而,在文學原著改編的過程中,我們依然看到能夠忠實展現原著語言及藝術的電影作品,本文通過分析安·泰勒小說《昨日當我們盛年》的電影改編,認為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小說原著的空間敘事策略,恰恰利于文學語言在電影語言中的再現。
電視電影《昨日當我們盛年》(Back When We Were Grown Ups)改編自美國當代著名作家、普利策獲獎作家安·泰勒的同名小說,該片曾獲得包括2005年金球獎提名等眾多獎項的肯定。該劇本忠實于安·泰勒的小說原著,影片的電影語言與原著的文學語言融合緊密。安·泰勒善于使用后經典敘事策略,將電影、樂曲等多種藝術元素融合于文學文本之中,如小說《伊恩的救贖》(Saint Maybe)中就巧妙地運用了音樂中賦格曲的敘事手法[1],而《昨日》則運用了空間敘事策略,展開了一幅以動態場景空間敘事為基調的圖景式敘事畫面,這使得小說本身能使讀者體驗到阿爾貝·拉費在《電影世界的召喚》一文中探討的幾近真實的“現實印象”(l'impression de réalité)[2],從而使得其小說文本呈現出電影特有的敘事效果,這也是其電影劇本能在最大程度上忠實于原著的重要原因。約瑟夫·弗蘭克認為,現代主義小說家棄絕時間和順序,偏愛空間與結構,常把他們的小說文本對象當作一個整體來表現,其統一性不是存在于時間關系,而是存在于空間關系中,這導致了空間形式的發生;而讀者也必須把這一小說文本當作一個整體來閱讀和認知,方能將獨立于時間順序之外的關聯物在空間中連接起來。[3]這種特殊的文學文本敘事效果,使得小說敘事不再拘泥于時序,而可以以場景繪制的方式展開敘事進程,這樣的敘事手法使得文學語言能夠自然地通過電影語言來表達,體現了文學與電影在藝術形式上和諧一致的生命力。
二、《昨日當我們盛年》概覽
作為美國當代文壇頗具影響力的作家,安·泰勒自1964年起至今已出版了20部小說,其中不乏獲得普利策小說獎、美國圖書批評家小說獎、福克納文學獎、卡夫卡獎等眾多獎項的作品。家庭和情感主題是安·泰勒作品所關注的重點所在,同時她以后經典的敘事手法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現了美國南方城鎮生活的真實畫卷,原著《昨日當我們盛年》即是其中的一幅。
同名電影講述了年過半百的婦人雷貝嘉尋求自我認同的故事,展現了現代人的迷惘和困惑。雷貝嘉在年輕時選擇與男友艾倫比分手,嫁給年長許多、帶著三個女兒的離異男子喬·戴維奇,她與丈夫生育了一個女兒,喬過世后,雷貝嘉獨立支撐四個女兒和一家人的生計。電影伊始,雷貝嘉面臨“中年危機”,這是人生中較為平穩卻疲憊的階段,她已經成為經營家族生意的老手(提供所住的大宅子“熱情洋溢”供人辦派對),與此同時,繼女們已長大成人卻似乎仍然沒有將她當作母親,而喬99歲的叔叔則完全依賴她照顧。雷貝嘉突然對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懷疑,她開始思考當初若順理成章嫁給前男友艾倫比,人生會展現何種可能性。于是,她開始與已經離異的艾倫比聯系并約會,影片由此展開。在經歷了約會的悸動、緊張、甜蜜、沖突和反思之后,雷貝嘉終于認識到這段關系的不可取,也肯定了自己當時婚姻選擇的正確性。影片最后以戴維奇老爹(喬的叔叔)的100歲生日聚會為結尾,在聚會上,其樂融融的戴維奇大家庭讓雷貝嘉感受到了家的溫馨,也明白了自己當時之所以選擇喬的原因:那樣一個熱鬧的大家庭所帶給她的快樂與溫情,正是艾倫比的理智與冷漠所不能給予的。
三、動態轉換的場景空間
不論是《昨日當我們盛年》的小說文本還是電影敘事,都采用了動態場景空間敘事手法。場景作為空間敘事的基本單位,對敘事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對敘事時間的干預,二是場景之間的轉移及銜接形成了敘事的基本結構。在敘事作品中,場景空間因其本身的客觀性及物質性,成為敘事作品(文本或影片)以地理學方式最直觀的構建,它囊括了角色互動的諸種語境、范圍以及具有結點的集中,體現了敘事的地理學景觀。同時,它不不僅僅是對外部環境的直觀展示,也是作者/編劇借以表現時間、展示敘事結構、推動敘事的重要手段。
影片的主要場景空間有三處:其一為戴維奇家老宅,一幢位于巴爾的摩的叫作“熱情洋溢”的大房子;第二是雷貝嘉娘家,教堂谷的一棟小房子;最后則是前男友艾倫比的住處,位于馬凱頓的一間教授公寓。這三個主要場景空間為影片大部分取景的場景空間,它們均為室內場景空間。室內場景取景的影片通常意味著靜態的電影場景敘事方式,但本片區別于一些典型的靜態敘事,如電影《這個男人來自地球》中始終囿于某單一的室內空間而單純以人物言語對話來鋪開電影敘事的方式。影片《昨日當我們盛年》在上述三大主要場景空間中通過閃回、蒙太奇等電影手法,在三大場景空間中不斷切換,以動態場景空間轉換敘事鋪陳電影情節,這不僅有效避免了單一室內空間場景通常會帶給觀眾的沉悶和平乏的感覺,而還在敘事表現手法上與原著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電影中取景最多的場景空間是戴維奇家的“熱情洋溢”老宅,這一室內空間在安排上極具匠心,同時也體現了原著的精髓。作為聚會承辦屋的“熱情洋溢”,在空間指涉意義上,與另外兩大主要場景空間——“教堂谷”及“馬凱頓”——相比帶有微妙的轉換意義。它既是戴維奇一家的居住場所,又是向客戶開放租賃的聚會舉辦場所,在這幢老宅中,聚會參與者、水電修理工、送貨工、園丁等外部人員在人數和滯留時間都遠高于除雷貝嘉和“老爹”以外的戴維奇家多數家庭成員。在影片中,與另外兩大主要場景空間的重在室內取景不同的是,對“熱情洋溢”老宅的取景同時重視其周邊環境,包括小區道路、周遭房屋、花園等。不難想到原著中的一句話:“有人來家里……就會發生這種事:他們會強迫你從外頭看你自己的生活,強迫你領悟。”[4]這句話幾乎可以視作對這一場景空間設置的隱喻。“熱情洋溢”老宅作為一個半開放的場景空間,標示了從相對隱蔽的私人空間向相對開放的公共空間的轉移,這一轉移不僅僅是地理空間的轉移,也是文學空間景觀的轉移。
四、圖景式空間敘事進程
小說《昨日當我們盛年》重在人物塑造而非跌宕起伏的情節,小說依托三大主要場景空間,在空間動態轉換的同時,以繪制圖景的手法進行推動敘事進程。電影在老宅“熱情洋溢”場景空間中涉及到的主要圖景有五幅:第一是雷貝嘉在熱鬧的聚會中突然對自己的人產生懷疑,畫面聚焦于其面部特寫,那種遲疑、欲言又止的神態與周圍眾人寒暄形成了鮮明對比;第二是她回憶在老宅舉辦的同學生日聚會中首次與喬·戴維奇相遇,畫面聚焦于青春年少的雷貝嘉笨拙的打扮和歡快的笑臉,突出了其單純快樂的心情,也喻示了喬帶給她的不一樣的感受;第三是雷貝嘉與艾倫比重逢后在家的單獨約會,畫面重點描繪了雷貝嘉的緊張、躊躇與矛盾,同時也展現了兩人并無默契的窘迫感,這樣的窘迫被園丁的對話以及提前回家的老爹打破,展示一副原該浪漫卻最終尷尬殘缺的約會圖景;第四則是雷貝嘉邀請艾倫比參加家庭聚會,一場介紹艾倫比的聚會卻使得雷貝嘉頓悟兩人結合的不可能,畫面最后切換到雷貝嘉在晚間的薄霧中單獨走出屋子,與屋內的熱鬧氣氛鮮明對照,將她的孤獨陰郁展現得一覽無余;最后則是老爹100歲的生日聚會在老宅舉行,聚會盛大而熱鬧,老爹快樂而嘮叨,在聚會中播放了以戴維奇家生活攝影制作的回憶影片,畫面中出現年輕的雷貝嘉開心的笑臉,這一圖景展現了她在戴維奇大家庭中真實的快樂,她終于意識到自己內心的真正自我。成為“鬧哄哄的大家庭一員,一如兒時的夢想”。[5]上述這些圖景均是小說以影片方式原汁原味的再現,它們以白描的手法涵蓋了情節發展的大部分重要場景,不論小說還是影片的敘事進程,都在這一層層圖景中得以推進和深入,完全展示了帶有鮮明電影特征的“敘述作用”。
小說的空間敘事策略契合了電影的敘事手法,使得空間敘事在文學語言與電影語言之間架起橋梁。克里斯蒂安·梅茨在其著作《電影的意義》中是如此定義電影的“陳述作用”(diégèse)的:“我們在電影中能得到現實的印象并非由于演員的有力呈現,而是由于銀幕上夢幻一般的影像活動,而這種影像活動迫使我們不得不認同其‘虛構的現實’,這一觀念我們稱之為‘陳述作用’。”[6]正因此,小說《昨日當我們盛年》在改編為劇本時,才有著得天獨厚的敘事優勢,能夠最大限度地忠實于原著而呈現給觀眾。
結語
電影和文學的聯系微妙,盡管有著諸多差異性,究其本質而言兩者均為文本的衍生,是文本的不同表現形式和解讀方式。[7]改編為電影的小說文本不在少數,但往往容易因對原著存在誤讀,不能充分展現其主題,或由于電影與小說文本在表現手法上的不同而使得影片不能完全展現小說的風貌等原因而遭到詬病。然而,安·泰勒的眾多研究者與讀者都認為影片《昨日當我們盛年》完全再現了他們對于原著的文學想象。審視這部電影改編何以達到如此成就的原因,不得不歸功于原著的空間敘事策略。
原著《昨日當我們盛年》運用了明顯的后經典空間敘事策略,小說敘事的一大特點在于其并未著力于從傳統的時間和順序入手,以跌宕的情節來推動文本敘事,而是致力于描繪細致的空間場景,塑造豐滿的人物形象,從而以繪制圖景的方式展開一幅幅敘事畫面,推動敘事進程。電影的改編同樣忠實于原著的空間敘事策略,恰又突出電影本身的影像優勢,對原著的圖景進行真實詳盡的再現。梅茨認為:“電影顯然應該是一種語言……電影的組織顯然是一種段落組合的方式,而且其來源乃是某種定型的圖例范圍。”[8]馬塞爾·馬丁更是在其著作《電影語言》(Le langage cinématographiqu)中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與文學語言相比,電影語言由于有影像畫面的具體展現,更具有真實的客觀性,是對文學作品強有力的重述方式。可以說,由于空間敘事策略在文學語言與電影語言中的運用,使得影片《昨日當我們盛年》成為了電影重現原著的完美典范,空間敘事策略作為兩種語言的融合者,對于其他小說文本的電影改編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1]趙嵐,王曉英.對話的藝術:《伊恩的救贖》的賦格化敘事[J].外語研究,2015(4):113.
[2]Albert Laffay.L’évocation du monde au cinéma[J].Logique du cinéma,Masson,1964:15-30.
[3][5]約瑟夫?弗蘭克等.現代小說的空間形式[C].秦林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1.
[4][7]安?泰勒.昨日當我們盛年[M].易萃雯,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3:104,81.
[6][8]克里斯蒂安?梅茨.電影的意義[M].劉森堯,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9-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