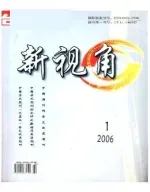稿費
說到稿費,不免無言/顏以對,常有作家向我抱怨,四十年稿費沒漲過!有作家對我說起四十幾年前,拿到一字一元(新臺幣,下同)的稿費,他當時月薪一千多元,一篇一萬多字的小說,稿酬幾乎是一年薪水!聽得我又羨又愧,回答他:“您至少過過那種好日子,我呢?誰不想生在盛唐啊?!”
我說“盛唐”不全然是“比喻”,唐代文人“稿費”之優厚,真的令人咋舌。就從初唐說起吧。據說王勃因為辭采華麗,慕名請求代筆者眾,于是他家里“金帛盈積”。到盛唐有個李邕(李北海),能詩善文工書法,達官貴人、各地寺廟紛紛重金請他寫文章,他寫過數百篇這類“邀稿”而成巨富。杜甫詩曾描寫李邕家的派頭:“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被認為是自古以來因寫文章而獲得最多錢財之人。這樣好的事,怎沒落在杜甫先生頭上呢?
稿費的形式不一定是金錢,古人向文人墨客求取詩詞書畫,或是碑銘志序,除了以金銀酬謝,還可以物易物呢。比如王羲之愛鵝,李白要喝酒,而蘇東坡,據稱送羊肉也可以。
究竟從何時、哪一份刊物開始有了稿費制度?我查閱的書籍文獻都沒有明確記載。早期的副刊或是類似副刊的版面,經常是主編自己寫稿,編者即作者,連徐志摩接編《北平晨報》副刊(1925年10月-1926年10月),據說每星期要寫幾千字應付版面。但也不可能編輯全部自己包了,還是要對外張羅稿源,稿費的制度化,可能就是在副刊形成的過程中,慢慢建立的吧。至于副刊的形成,容后另篇談論。
可以確定的是,報刊稿費的概念,是在有了副刊之后,在此之前,一般的觀念,到報社刊登文字不僅沒有稿費,并且是要付費的。清同治十一年(1872)3月23日創刊的《申報》,創刊號發表《申報館條例》被視為最早的文藝征稿啟事,曰:“如有騷人韻士有愿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竹枝詞及長歌記事之類,概不取值。”“概不取值”的意思,就是不向你收費。
在副刊興起,甚至成為報業競爭主力之后,稿費自然應需求而生,從每篇奉酬雞蛋兩個,到一篇海外通訊稿費50元天價(當時米價5元一擔)皆有之。
今日稿費(臺灣)普遍在每字1元至2元之間,專欄或重量級名家另有標準,詩一般每首以一千字計算,長詩另計。大致如此,與四十年前相去不遠,難怪資深作家經常感慨。我同時是作家也是編輯,比誰都向往過去的好時光。
過度緬懷美好時光,有害身心。今日全球報業媒體的生存困境難以盡述。有一次作家劉克襄見到我,搖了搖頭:“以前我們整天擔心有一天副刊會不見,原來……有一天整個報紙都會不見!”但說到最絕望處,我又沒有那么悲觀了。不僅依舊保有無可救藥的樂觀,遇上一些還沒投稿來,先來電仔仔細細詢問稿費多少錢?怎么計算?如何支付?刊出多久會寄出?不能多一點嗎?甚而有擔心我們竊取他的稿子而要求收到稿件先付費種種的問題、要求時,我刻薄的劣根性立刻壓倒愧疚之心,得非常努力壓抑自己不要迸出這涌上喉頭的話來:“你稿子能用再來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