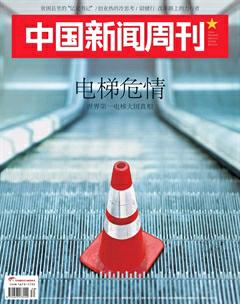北京“遷府”并非“梁陳方案”之意
華新民
傳言北京市政府要搬遷到市中心30公里外的通州潞城鎮,許多人評論這條消息時,都提起1950年梁思成和陳占祥的“梁陳方案”,想說明將市府設立在舊城之外是早已有之的專家建議,只是決策層沒有采納。
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
“梁陳方案”的起源,是梁思成在1949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計劃座談會上提出的建議。當時新政府已打算繼承民國政府1947年的西郊五棵松新都市規劃,政府代表交給與會技術專家討論的議題之一是:“將來發展應注重趨向于建設近郊區或衛星城”,日后西郊新城市功能是行政、居住、商業、輕工業或手工業及游憩。這也是大部分在場專家的共識。但梁思成卻不贊成把五棵松建設成新城市,而是提議規劃成行政中心。
他的考慮有點民族主義色彩:五棵松一帶為二戰時日本人為其僑民建的新城區,他不愿用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和基礎設施發展一座新城,但行政中心尚可接受(不過數月后,梁思成對此仍感不快,綜合其他因素后,又建議遷址三里河)。當時會上所說的行政部門,無論新都市計劃還是行政中心(附帶干部住宅)的提議,都是指中央政府而非北京市政府。
究竟是新都市還是行政中心?會議結束時并無結論。但五棵松一帶的建設年內已開始。為此專門成立有新市區工程處,并在萬壽路為毛澤東、朱德等人建了住所,稱為“新六所”。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會議召開,我祖父華南圭(工程師)作為與會代表,再提西郊新城市方案:在五棵松一帶建一座真正綜合性新城市,并規劃了道路網、工商區、住宅區、文教區、公共建筑、行政機關、公園、劇場和地下車道等。其中的行政機關雖沒點明是中央級別,但因3個月前最高決策層已決定北京市政府設在舊城區,中央機構設于西郊,所以這里的“行政機關”也是指后者。
1949年9月,蘇聯專家到來,提議在舊城中心設立中央行政區。作為回應,1950年初,梁思成和陳占祥提交了“梁陳方案”,其標題是: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梁陳建議,在三里河一帶建行政區和干部住宅區,全文無一字涉及北京市府機構。與此同時,早先的西郊新城市計劃也莫名其妙地淡出了公眾視野。
即便僅涉及行政中心,“梁陳方案”的主旨依然明確:不制造舊城擁擠,保護古都風貌,反對在長安街兩側興建高層辦公樓等。文中還提到:“其實市人民政府所劃的大北京市界內的面積已二十一倍于舊城區,政策方向早已確定。”
蘇聯專家的部分意志終于占了上風。舊城中心開始建中央部委辦公大樓,開了幾條寬馬路,繼而又有大躍進時期的“十大建筑”等。
不過,“梁陳方案”的部分宗旨也得以保留,體現在建筑師張開濟設計的三里河“四部一會”和干部住宅區。并且,直至八九十年代,除上述有政治含義的建設工程外,絕大部分新建設仍是在北京老城區外面進行的,絕大部分胡同也都依然存在。
其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一直在實施新政權成立之初規劃的大北京藍圖,其面積是舊城區的21倍。另一原因是四合院宅地為私有,房主都手持地契,拆房建樓的規劃只能紙上談兵。
真正的轉折點,是1982年以后推動起來的房地產開發。只要盤點一下今日二環內舊城里大多數高層建筑的建筑年代,便一目了然。而幾十年內幾經易稿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也正是在1982年正式提交給高層的。
因此,今天北京種種問題的根本原因,并非若干年前的“規劃之爭”,也非簡單的“大城市病”,深層癥結是30年來對土地利益的追逐。如不找對癥結,開出的藥方也會無濟于事。
回到眼下包括設立行政副中心計劃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其中提到,要把北京中心城區的功能釋放出去,這無疑正確,關鍵是如何執行。
北京市政府的各個管理機構是北京的管家,大小事情都要由它來具體操辦,跑到三十公里外的通州去辦公,可以預見的是:行政效率將被大大消弱,并將伴隨土地資源和時間的浪費,也許還有諸多連鎖后果。另一方面,如一邊計劃遷府,一邊繼續在中心城里施工建大樓,無疑是一手釋放功能一手增加功能,自相矛盾。
那么,我認為,究竟該如何釋放中心城區的功能呢?首先是要停止三環以內的房地產開發,依法解除相關土地出讓合同;然后是謹慎地選擇外遷行政部門,建議就此認真研究一下已有國內外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