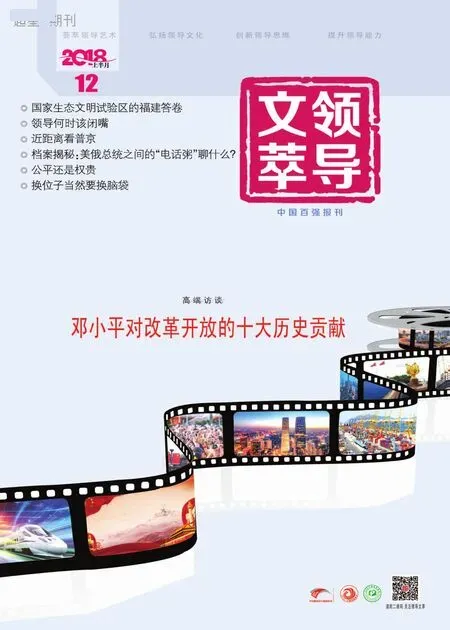在中國創新為什么這么難?
□張維迎
從500年前哥倫布去美洲開始,人類就走向了全球化,人類市場在不斷地擴大,分工不斷地深化,技術不斷地進步,財富不斷地增加。在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業家。市場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場是企業家看到的。所有的市場都是企業家創造的,分工也是企業家創造的。創新更是企業家的一種基本職能,創新帶來經濟增長、財富增加,而財富怎么帶來新的市場,也可以說是企業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產能過剩,意味著中國的企業家沒有進一步將增加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我們還在重復地生產,市場上已經飽和。為什么會是這樣?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企業家本身在最初淘第一桶金也就是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1世紀前些年的時候,仍然是大量市場不均衡的時候。那時候,“低垂的果實”就是生產其他國家已有的產品——我們叫山寨——就可以賺錢,久而久之就不會思考怎么創造新的東西來滿足市場。
另一個原因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泰勒·考恩提到的,我們的社會體制。社會體制使得這個國家的企業家們更愿意去套利而不是創新。相對而言,套利風險不那么大,不確定性也沒有那么大,我們只要敢冒險,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賺錢。而創新卻是完全面臨不確定的世界,看到沒有的東西、誰都看不到的東西。在一個不能夠容忍這種自由、每個人的權益沒有基本的保證、創新的成果沒有確定回報的時候,好多企業家不會真正去創新的。更簡單地說,創新型企業家比套利型的企業家對制度更為敏感,當一個國家沒有很好的法治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業家。一個國家如果法制不健全,游戲規則不透明、隨時在變,一個人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證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企業家不可能真正花時間去進行創新。
如果中國真的從過去的依靠資源配置改進的增長,轉向了創新推動的增長,那么我們的企業家必須從套利型的企業家轉向創新型的企業家。真的出現創新型的企業家,就需要我們現有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進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變革。這里更重要的是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況下,政府的權力受到嚴格的抑制,每個人才能夠在未來有一個預期,企業家才會投入持續的創新。為此,也需要整個社會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教育體制的改革。一個國家的國民,特別是大學生、學者,當他們有一顆自由的心的時候,才真的會有新的想法。我們所有的創新都是從一個想法開始,所謂“新”,就是與眾不同;所謂“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認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中國才可能真正維持未來相對比較高的增長。
其實創新說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亂想,那就會有創新,你不會為了你的想法去冒險的時候,創新是不可能的。希望有一天年輕一代企業家每個人都可以胡思亂想。我們的創新對人類的貢獻,一定要超過我們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問題。一個人坐在那兒是很難創新的,應該是人口規模越大創新的速度越快。中國人口占世界大約20%,但我們為世界貢獻的創新能到多少?我們歷史上有過好多的創新,但在近現代,我們連2%、甚至1%都不到。
最后,筆者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說的話來比喻制度改革為什么這么重要?我們采集了大量低垂的果實,但這個果實是會采摘殆盡的,所以未來還是要依賴我們自己栽樹,讓世界其他人也能從我們種的樹上采摘。所有亞洲國家,不管是日韓還是馬來西亞、印尼、泰國,都不可能像美國那樣一開始推出民主制度的時候就有一個非常強大的中產階級,這不僅是中國面對的挑戰,而是亞洲國家普遍面對的挑戰。
(摘自《青年商旅報》)
——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認為,中產階級的壯大需要創業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