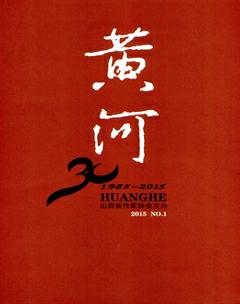問渠那得清如許
朱航滿
錦繡與爛漫
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王元化先生曾提出“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頗得學界的廣泛認同。然則,直到今天,學術界之缺乏思想以及思想界之缺乏學問依然令人嘆息。制造學術垃圾的八股文章以及缺乏學術積淀的胡言亂語,簡直是充斥眼球,也由此可見,能夠真正做到“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可謂難矣。或更由此談到當下的隨筆寫作,我便想借用王先生的這一句式,談談我心目中的隨筆,乃或是有才情的學者之文與有學識的作家之文。學者文章有錦繡綿密之妙,作家文章為天然爛漫之美。一般來說,學者撰寫謹嚴周密的論文,特別是現代學術體系建立以來,嚴格的學術規范使得多數學者的論文邏輯嚴密、論述周全,但面目呆板、缺乏情趣,甚至也壓抑了才情的發揮,但對于真正有才情而又有文體自覺的學者來說,其或者有“另一套筆墨”,也或者能夠使筆下流淌著才識俱佳的好篇章,諸如陳平原所倡導的“大學者寫小文章”,也或者如錢鍾書所撰寫的學術論文,均是有真才情也有真學問的好文章,也是我所喜歡的隨筆佳構。
之所以鐘情有才情的學者之文,乃是能夠較為輕快地了解到研究者的心得體悟,并能從中嗅覺到一種酒香彌漫的氣味。可以說,這樣的文章是論者的才情使熱,同樣還是一種文體上的個性自覺。然則,有這樣文體自覺的學者少之又少,令人遺憾。反倒是一些老派學者,或者是承傳了老派學者遺風的當代學者,才能夠較為自覺地去擺弄自己筆下的文字,諸如我讀學者顧隨的《中國古典詩詞感發》,便能深刻地感受到先生對于中國詩詞的研究已經融化于胸的學問境界,故而能夠以點滴感發的形式漫談中國詩詞的美好與神采;再如我讀學者繆鉞的著作《詩詞散記》,也同樣有類似的感受。繆鉞以隨筆的形式來論說唐詩宋詞,看似傳統實則現代,他是以現代的思維談論古典,令人耳目一新,卻自有一種縝密與細膩。當代以來,諸如錢鍾書的《七錐集》、李澤厚的《美的歷程》、余英時的《中國文化通釋》、田曉菲的《秋水堂論金瓶梅》、馮象的《政法筆記》、李潔非的《典型文壇》等等,是學術論著,但又何嘗不是頗具才情與識見的隨筆佳作呢?我同樣還鐘情有學有識的作家之文。作家是敏銳的觀察者、感受者、發現者和記錄者,但同時還須成為有思考、有識見、有情懷的寫作者。提倡作家學者化,在我看來是不切合實際的,那樣或許會遏制作家的才情,甚至使得作家陷入到論證與考據的溝壑而進退不得,甚至是畏手畏腳,最終難以寫出令人滿意的篇章。學者與作家之間,本無強制性的個人分工,但絕對不是一種思維方式的工作。但我贊同作家要多讀書,多思考,更多一些個人的見地、理性的思考與文化的底蘊,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才耐讀,才有趣,也才能夠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不至于那樣容易地一驚一乍或被炫目的表象所迷惑。但我們也不必要用學者的深度來要求作家,卻可以從作家筆下的觀察與思考中得到更多鮮活的感觸與啟發。有學有識的作家能夠寫出不一樣的文章,諸如孫犁、黃裳、汪曾祺、楊絳、木心,等等,他們筆下的文字有著濃濃的書卷氣,是文化的積淀與修養,是人生的見識與修煉,是精神的超拔與升華,故而令他們筆下的文字有著非同尋常的魅力與氣象。
恰巧在編選2014年的中國隨筆年選時,這幾位我所喜愛的作家,幾乎都有論者談及諸如關于孫犁,學者孫郁便有精彩的文章論及。在《孫犁的魯迅遺風》中,孫郁將孫犁放在“五四”的精神傳統之中予以論述,但同時也讓我們明白了一個因緣,孫犁晚年的文章之所以沉郁老辣,乃正是接續了“五四”特別是魯迅的精神傳統,他暗自以魯迅為標桿,甚至讀魯迅讀過的書,從而完成了文章境界的衰年蛻變;再如汪曾祺,其子汪朗在《“老頭兒”三雜》中談到了汪曾祺的魅力之所在,乃是讀雜書、吃雜食、寫雜文。可以說,汪曾祺的雜覽與雜寫,實際上接續了中國傳統文人的法脈;而對于木心來說,陳丹青在《孤露與晚晴》中,則以深情熱誠的筆觸,追憶了木心浪跡紐約的寫作與生活,也寫了木心的歸來和遠去,以及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文學財富。瑣碎的往事勾勒出一位文學家的個性與情趣,也于不經意中看到了他謎一般的人生經歷、藝術修煉、文學造詣和學識底蘊。顯然,木心是一顆藝術的“孤露”,也是一種人生的“晚晴”。
但遺撼地是,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當代作家,卻是少矣。畢竟孫犁、黃裳、汪曾祺已經遠去,我們只能在不斷重讀他們的舊文中來感受那份卓絕的才情與識見。或許還有邵燕祥、董橋、李長聲、張宗子、止庵這樣的當代作家令我們期待,諸如邵燕祥對于往事的記憶與深思,董橋對于文人和文玩的典雅闡述,李長聲對于日本風物的考證和紹介,止庵對于知堂法脈的研習與追模,張宗子在海外讀雜書寫筆記的那份寂靜與自守,都是值得我們為之流連的。而已愈百歲高齡的楊絳先生,其文章修煉,更是達到了一種大象無形與大音希聲的高妙境界。當然,作家文章中,我也常常被張承志所吸引,他的純粹,他的孤傲,他的追尋,他的思索,雖然對于其關注所在,我個人也時有難以認同之處,但對于他筆下流淌的文字,卻時刻保持著一種敬重的態度。再還有韓少功,我曾為他的眾多充滿思辨與智趣的學術隨筆所驚艷,但他的長篇新作《革命后記》,卻令我失望,這種企圖跨界來論述歷史和討論現實的勇氣值得欽佩,但其間充斥的那種漂浮與狐媚,令我感到驚異。這種感覺,其實早在讀他的那冊為人稱道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已有感觸。
談論學者之文與作家之文,在2014年則有兩篇同題文章值得關注。學者張鳴的隨筆《父親的贖罪》與小說作家胡發云的隨筆《父親的“交代”》,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篇文章均寫道了他們各自的父親,也寫道了父輩的往事和命運,但卻互為補充,展示了一代人在大時代背景下的相似遭遇。他們的父親均曾在1 949年以前為國民黨的低級軍官,一位在革命成功后因為背負了沉重的歷史罪責,從而不斷地試圖通過自我懲罰式的贖罪來減輕那種被認定的罪責,而另一位則在革命成功后不斷通過掩蓋、回避甚至是改寫自己的歷史來試圖逃脫新時代的懲罰。不管他們在易代之前曾有過多少的艱辛與榮耀,也不管是他們在鼎革之后為新社會做出了多么沉重的付出,他們都須用自己的一生來書寫小人物與大時代的錯位。張鳴是歷史學家,有才情也有擔當;胡發云是小說作家,有擔當也有情懷,他們在追尋父輩的人生歷程中,試圖通過小人物的命運來折射時代的荒謬與殘酷,從而以自己的筆觸共同完成了歷史的另一種見證。在此一點上,學者之文與作家之文達到了幾乎一致的深邃與澄澈,我為張鳴的動人才情贊嘆,也為胡發云難得的史家情懷感慨。
張鳴與胡發云的寫作追求,令我想到了捷克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名言:在真實中生活(LIVE IN TRUTH)。在面對2014年的隨筆寫作時,我在更多學者的隨筆寫作中看到了這種堅守道義的追求,諸如謝泳對于陳寅恪有關中國小說的闡發與鉤沉,趙園關于《吳宓日記》中有關舊學人與新時代的錯位悲劇,陳徒手對于陳荒煤命運的細心鉤沉與發微,康正果對于施蟄存的晚年境遇的側面描述,章詒和關于大律師張思之及其新書的深情論述,張霖對于作為青年學人的丈夫張暉不幸早逝的追問,如此等等,都是試圖通過對于知識分子這一個案的深入挖掘,以微小的切口而更多地來展示時代的橫截面。他們在論者的筆下,或被稱為歷史的“被發掘者”,或以“精神知音”論之,讀來常有沉郁頓挫之感。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張霖的隨筆《君子永逝,我懷如何?》,這位失去“君子”張暉的青年學者,以其沉郁動情的筆觸,不僅發出愛人逝去的天問,更嘆息了當代學人在堅守中的安貧樂道,同樣還嘲諷了我們這個時代對于追求真知者的盲視、腐敗與僵化。我從這些微言大義的文章中,既看到了專業的厚實底蘊,也看到了一種精神的升騰氣象。
如果揭示真相是寫作者的一種權利,那么對于自由的追尋,對于革新的探究,對于科學的普及,也同樣應是寫作者的一種權利,在2014年,這些人類共同關注的理念成為學者們筆下奏響的曲調,以不同的方式讓我們得到了一次次精神的洗禮與靈魂的沖擊,盡管它們宛如微星一樣散落天際,卻令我們讀來油然感到溫暖。諸如浦實在《自由之路》這篇長文中,詳實而獨到地寫道了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追求自由的精神地圖,特別是其在度過漫長的監獄歲月中的強大毅力,可以說是人類對于自由的追求與掙扎的一個永恒的情景;王曉漁在隨筆《“獅子要吞噬多少只夜鶯,才能學會歌唱”》一文中,向我們描述了作家奧威爾在追求自由付出的心靈煎熬。王曉漁與浦實兩位筆下的奧威爾與曼德拉,堪稱是人類追求自由的精神領袖,而江弱水與林賢治兩位學者,他們其中一位試圖通過評價一本描述前蘇聯知識分子的著作《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而另一位則試圖評價一本描述捷克歷史的著作《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共同表達了政治極權對于自由的扼殺,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恐懼、壓抑、冷漠和蕭瑟。
人類追求自由的腳步從未停止,而對于自由的贊美、維護、論述乃至爭議,也從沒有停息。同樣,關于改革與革命這一對詞義相近的詞語,也還是一個與我們息息相關卻難以真正說得清楚的話題。2014年同樣如此,在我的閱讀印象中,學者李零的《從燕京學堂想起》則頗有幾分他當年寫出《大學不是養雞場》這樣妙文的回響,可謂嬉笑怒罵,辛辣尖銳,其中一句“錢在賬上不得不花”,可謂是對當前諸多改革的一種特別尖銳的解讀。再如政法學者馮象在文章《國歌賦予自由》中,試圖通過一起工廠的罷工事件來分析其間的法律悖論,妙趣橫生又別有洞見,乃是氣象開闊的論文式隨筆。馮象的這篇文章頗有其當年在《讀書》雜志開設“政法筆記”的遺響,其古雅的語言、專業的視角以及現代的思維,都給人以新的啟發。2014年同樣令我驚喜的,乃是青年學者許知遠發表在網上的專欄文章《2014:中國紀事》,其以觀察者的旁觀視角,冷靜犀利的分析和思考,記錄了作為70后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急劇變革的紛繁現狀,特別是長文《民主的功夫茶》,敘述了南方一起獨立民間選舉的成功與失敗,來寫變革的復雜與困惑,是頗有深度也有才情的隨筆。
諸如李零、馮象等人的文章,在我看來,非有學識、有才情、有關懷的大手筆所難以完成,這也正是我更看中有才情的學者之文的原因所在。正如學者葉嘉瑩在論及古典詩文時談到:大凡真正偉大的作家,在其心中都有一個真正追求和執著的理念。她進而指出,凡是第一等的作家,都有一個最高的理念的層次。那么,在科學的研究與普及上,更是如此,而非一般文采風流者所能完成。她還說,文采再風流,那也不過是第二等。我更看重那些能夠擁有“第二支筆墨”的學者,他們不經意的妙筆卻常有令人喜悅的境界。諸如洗鼎昌和沈致遠兩位,他們都是科學院的院士,可謂學有專長,但他們對于精神的追求,對于藝術的修養,都達到了老爾彌精的地步,從而在更高層次上得到了融通。洗鼎昌院士的文章為《門外談美》,副標題則是“科學和藝術的美學比較”,引經據典,典雅灑脫;沈致遠院士的文章《以簡馭繁》和《文尚思》,則通過科學領域來啟發人文學界,告知簡潔與思想的本真魅力;令我更為歡喜的,還有科學史研究專家江曉原的專欄寫作,諸如他的《<自然>究竟是一本什么雜志》和《<自然>雜志與科幻的不解之緣》,談論大名鼎鼎的頂尖科學雜志《自然》,劍走偏鋒,妙趣橫生,乃是才學并茂的科普佳作。
可以說,有才情的學者之文與有學識的作家之文,皆為我所愛。但在我看來,有才情的學者更多的是造化,多一個則是文章之幸;而有學識的作家更多的是修煉,多一個則是讀者之福。以我所見,近年來的文章佳構,有造化的學者文章多,而有修煉的作家文章少,此不可不令人嘆息。而諸如像錢鍾書先生這樣有兩副筆墨,能夠同時在寫作與研究兩個領域皆有高妙造詣且卓然成家者,則又是少之又少了。為此,我期待能夠有更多學者能夠擁有第二支筆,以大才情寫小文章,也更期待更多的作家能夠寫出妙趣橫生又學識才情具佳的好文章。這兩者似乎都有近年來頗遭詬病的代表,但我以為雖有種種瑕疵,但其學識與才情也均還堪稱優異。前者便是寫出《文化苦旅》的余秋雨,其在戲劇史研究之外寫出大量文化散文隨筆,影響極大;而后者便是臺灣的蔣勛先生,其一系列的解讀中國古典詩詞的隨筆文章也是受眾極多,其間自然不乏博識與見識,更有才情令人艷羨。今年的隨筆年選,我選了蔣勛先生的隨筆《西湖》,看他從杭州西湖談到古人、談到風景、談到藝術,頗有率真爛漫之美,所謂風流灑脫,圓融綿遠,也定是學問之氣象與底蘊。讀蔣勛隨筆,似月下清泉流淌,又如暖春微風拂面,不妨閑來展卷一讀乎。文章似酒如茶深秋之際,與同窗L相約聚談。L在北大中文系讀博士,寫一手好文章,《讀書》雜志連載她的外國文學讀書隨筆,專欄取名“倒視鏡”。我讀了喜歡她文筆的綿密,運思的巧妙,分析的細膩,還有讀書的博雜和多趣。那日,我們縱談白話文章之妙,我說早年最喜歡魯迅,近來則更佩服知堂。前者如酒,后者似茶,都是越品越有滋味的事情。沒想到L與我深有同感,她也是知堂迷,博士論文作了有關知堂的選題,而由知堂,她竟深涉日本文化,也想去東洋留學。因為談性愈濃,她便極力向我推薦了幾位日本作家的作品,讓我一定要好好來讀。后來,我看她新近在報刊上發表的隨筆文章,很多也都與日本作家有關,或談黑石一雄、或談芥川龍之介,或談泉鏡花。L感慨說周作人是最懂得日本文明的真諦的。為此,她寫了一個系列的讀書隨筆,發信給我先睹為快,有許多作家都是我不熟悉的。我覺得她是在向知堂的文章精神致敬。
那日傾談俱歡,記得還提到了錢鍾書。周作人與錢鍾書是我對于中國近世文章的最愛。前者有日本文化的純凈散淡,后者則有英倫文人的博雜風流,而底蘊又皆是中國的精神與氣韻。周作人在《一蕢軒筆記序》中云:“文章的標準本來就簡單,只是要其一有風趣,其二有常識。常識分開來說,不外人情與物理,前者可以說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確的智識,合起來就可稱之曰智慧。”想來讀周作人的文章,恰如明窗飲茶一般的雅興。周氏不但自己喜歡“吃茶”,寫有多篇關于喝茶的美文,而其文章更有茶的甘澀與芬芳。如果說周氏文章如茶,那么魯迅與錢鍾書的文章則也有些似酒了。魯迅文章是烈酒,鐘書文章如紅酒。魯迅文章如酒之陳釀,錢氏文章則若酒之上品;魯迅文章如酒之痛辣,錢氏文章則似酒之甘冽;魯迅文章如酒之醇厚,錢氏文章則有酒之綿遠。魯迅文章多讀使人痛快,知堂文章多讀使人著迷。錢氏文章多讀則使人沉醉。
好文章似酒如茶。其實,這番比擬不過是一種文人的戲談,算不得嚴肅的學術評價,也當不得真的。但因為自從開始接編花城出版社的中國隨筆年選,我常常為了何以入選而頗費愁思。因為若是大而化之,凡是寫就的文章,似都應納入遴選的視野和范圍。但如此以來,豈不是變成滿坑滿谷的雜貨鋪了?說來我更喜歡用“文章”二字,而非“隨筆”這樣的稱呼。實際上,中國人的文章之說,大抵乃是因讀書、看畫、賞景、交游、憶舊、序跋、題記、考證、辨析、答疑等事而記的文字。故隨筆文字,皆應是因故而起,也是言之有物的東西。這或許就是隨筆中“隨”的意味了吧。由此,我對今日諸多所謂新散文頗不喜歡,因許多文字在我看來,乃是造作之氣實在過重,其中雖不乏匠心與才情,但為寫而寫的態度頗令人懷疑。本應是一篇灑脫有趣的文字,可在這些作文者的筆下,卻是如造水泥大廈,層層疊疊,氣勢凌人,實在是毫無情趣的丑陋之物。
而周氏兄弟與錢氏的文字就不這樣。我的書桌旁常有人民文學版的《周作人散文》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錢鍾書的《七綴集》,都是百閱不厭的戔戔小冊。知堂與錢氏作文,雖都喜歡吊書袋,但顯然是胸中筆墨縱橫。雖然引經據典,但前者無論是抄書,還是后者的引用,都是巧妙和自然的。因此,在我看來,好的隨筆文字必須是胸有成竹,能夠對所談之事有個人之見解和態度,對于所敘之事能有取舍之功夫,而不是筆尖隨著對象走,東拉西扯,不成氣候。這些均是火候不到,功力不足的因故。其實,知堂的文章是小品文字,看似隨意,其實卻有成年累月的積淀,字字句句都是功夫,不能輕視;而默存的文字,又是十足的論文,但一點也不似今日學術八股,令人讀來頭疼。都是苦心經營的東西,但卻讀來如美文一般,令人如有行走山陰道上之感。從周氏兄弟到錢鍾書,在這些老一輩文章大家的筆下,我似乎找到了當下中國文章的隱約脈絡。
好文章似酒如茶。翻揀一年年的收獲,卻總是那么不同。年初,在網上讀到南京大學已故學者高華的一篇長文《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后感慨萬千。此文發表于2011年臺灣的《思想》雜志和《領導者》雜志,系為臺灣作家龍應臺女士的著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寫的一篇讀后札記,卻是高華借龍應臺的著作談自己對于歷史的見識與思考,實乃是才情與識見皆佳的論述。此文寫就之際,也是高華疾患癌癥已近晚期之時。去年我編隨筆年選,收入香港中文大學熊景明女士的悼念文章《千山我獨行》,她說高華那時從上海做完手術,肝臟切除了近一半,但回到南京就寫成了這篇長達一萬六千字的文章。熊景明感慨說:“他從來帶著感情走進歷史;懷著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揭示史實真相。”好文章可遇不可求。這是高華的最后一篇文章,卻絲毫沒有哀怨悲憤之氣。我編隨筆年選,頗為這樣一篇上等佳作未曾早日寓目而遺憾,也為高華先生之早歸道山而極感痛時。高華的文章如酒,甘冽醉人,激蕩人心,如陳釀。
如果說高華的這篇是我這一年讀到印象最為難忘的文章,那么,這一年我最喜歡的書籍,則是木心的著作《文學回憶錄》。準確地說,這只是木心的一個半成品著作。在他去世之后,弟子陳丹青根據他當年在紐約為他們這些藝術流浪者們的授課筆記編訂而成。我捧讀此書,頗感木心先生的慧心。《文學回憶錄》闡述他對世界文學殿堂中的諸子百家的認識和體悟,但實際上在我看來卻是藝術家的文學筆記,其最關鍵之處不僅僅在于他對于文學的諸多真知灼見,而更關鍵的還在于木心打通了文學與藝術的壁障,令我讀來十足的驚嘆與欣喜。文學與藝術之間,本就不該分立并列的,而是互通互融才對的。去年我選上海畫家夏葆元先生的懷念文章《木心的遠去與歸來》,今年則選畫家陳丹青為《文學回憶錄》所寫的長篇后記《木心的文學課》,他們都寫到那段坐而論道的日子,令人神往。如果說高華是以史論道,木心則只是借史談藝,但讀他們的文字,不僅是窺見其慧心與才情,而更看到其精神上的獨立和清醒。高華文章似美酒,木心文章如好茶。
如此看來,我遴選2013年的中國隨筆,已有了這般的標準來審視,來欣賞,來體悟,來探究,來斟酌。印象深刻的,諸如筱釹的隨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和《我沒想到我會見到列寧》,雖是游記之作,卻飽含憂思,意境深遠,如飲佳釀;崔衛平的隨筆《收復自己的人性》,系讀書筆記,尖銳沉重,直抵靈魂,乃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楊瀟的隨筆《另一個國度》,氣象開闊,筆意蕭瑟,如紀錄片一樣地沉靜和詩意;還有狄馬的隨筆《梁山是劫富濟貧的嗎?》,乃是另類的讀書文字,其筆端的反諷與幽默,令人讀后會心一笑;再有謝仰光的隨筆《王與法之間》,寫他國的舊人舊事,勾勒史料,闡述精神,筆墨酣暢,飽滿淋漓,對于當下現實乃有燭照之意;再有學人范福潮、陳徒手、王曉漁、羽戈諸君的文章,乃是獨立精神的讀史文字,融個人經驗與公共情懷,傳統趣味與現代精神于一體;還有龍冬的隨筆《致赫拉巴爾》,寫捷克小國的大作家赫拉巴爾,是一個出版者與作家之間的心靈對話,也是兩個命運有著相似國度的寫作者的精神交流,更是對一個在特殊語境中堅持寫作的異國作家的致敬,還是一個中國作家的詩意宣言。此等文章,均似好酒。
好酒難得,好茶珍貴。2013年的好文章,既有令人沉醉的憂思之作,如飲好酒一般;也有讓人細品的絕妙之作,頗似飲茶一樣。楊絳先生的《憶孩時(五則)》,乃是百歲老人的筆觸,散淡之間卻有品不盡的人間滋味。文壇老奶奶的筆觸,既可愛又溫暖,還有許多道不盡的憂傷與蒼茫。香港董橋的文章,雖是談文玩與風雅,背后卻滿是道不盡的滄桑與風流,選錄三篇,也是選了再選,篇篇都難舍的好文字;畫家韓羽的文字《故人書簡札記》,乃是因一組舊友書簡寫成的札記文字,共計十八則,其間卻有識有味,文字也如其畫作一樣,寥寥數筆,滿紙機趣;邵燕祥先生的憶舊之作,溫潤中透著鋒芒,仿佛歷史的尖刃在心間慢慢刻錄,選錄兩篇。均如苦茶夜飲,往事浮上心頭。還有章德寧寫母親,劉新園憶恩師,李章和維舟追悼亦師亦友的當代學人,此等篇章,均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積淀與爆發。說來楊絳都一百零三歲了,邵燕祥八十歲了,韓羽八十二歲了;連筆頭甚健的董橋也已是古稀之齡,今年七十一歲了。老先生們的文字還老辣蒼勁,卻也有著溫潤與活潑。真是太珍貴了?這樣篇章難道不是讀一篇就少了一篇嗎?
文章似酒如茶。有好文章可讀,豈能不如有美酒好茶來相伴?雖嘆息今日文運日衰,其實并非是好文章太少,而是糟糕的東西實在太多,遮擋了我們的視野與眼球,麻痹了我們的大腦與神經,甚至玷染了我們的心靈與思想。那日,我與同窗L談到當世好文章,我說谷林先生的小冊子《書邊雜記》精雅細美,不妨一讀;董橋的文字并非文化快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集子不妨買上幾本抓緊珍藏:我說期待已久的《胡河清文集》即將面世了,馮象的《寬寬信箱與出埃及記》今年再版了,繆哲的《禍棗集》結集后頗受讀書人喜愛,他的譯文集四冊據說也要集中出版了;我說上海的黃裳先生和北京的止庵先生打筆仗,且不去管,可他們的文章都可愛;浙江大學江弱水教授的十年詩學論文集結為一冊《文本的肉身》,讀來綿密又華美,如江南笙綢那么賞心悅目;我說老師陸文虎先生的著作《荷戈顧曲集》也值得一讀再讀,雖是一冊文藝評論集,讀來卻如飲陳釀。陸師研究錢鍾書多年,讀書多,閱世深,文章蒼勁大氣,我揣摩長久,總是萬千滋味。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記得年初春暖,我攜一船隨筆年選的選本拜訪孫郁先生,在先生人民大學文學院的辦公室暢談文章之道。后來,《文藝報》整版刊登大學文學院長的訪談專欄,竟也有先生所談的文章之道,不僅讀后會心一笑。去歲秋深,我編2012年的隨筆年選,在上海的《文景》雜志上偶然讀到胡蘭成的佚作《記南京》,頗愛之。癸巳夏熱,受邀到南方參加一個筆會,遇見詩人龐培,夜談竟均提及此文,堪稱快事也。好文章如價值不菲的礦石,發現的愉悅便是如此。由此,想到孫郁先生為拙作《書與畫像》所寫序言中的一句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五四以來形成的文體,其空間還是那么的大。那長長的路還沒有走完的時候。只是有時彎曲,有時筆直,有時隱秘。好的文章,在我們這個時代不是沒有,只是我們有時沒有看到而已。”孫郁先生研究周氏兄弟多年,又在魯迅博物館浸潤數十年,文章溫潤澄澈,又沉厚開闊,想來乃是見識廣、胸襟大、積淀深的緣故。他的這句話,我幾乎都背熟了,想來是憂思,也更是期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