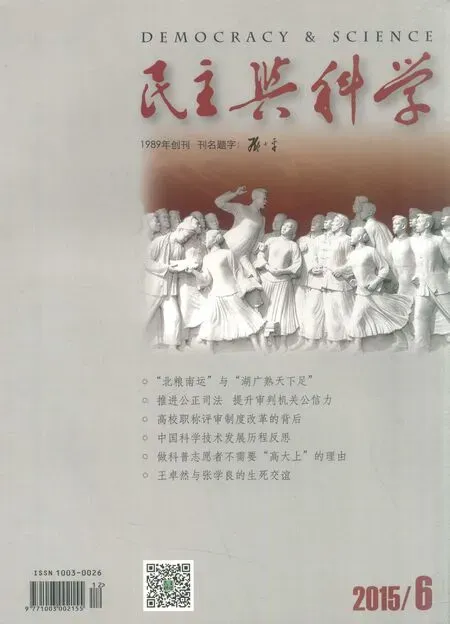大學是干什么的
■ 武際可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大學是干什么的?不同人有不同理解。
曾經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具體實施上,有不同理解。有的當政者提出要培養“奮發有為的馴服工具”,即要把成批大學生培養成“為我所用”的人才;有的則提議要培養“聽話、出活”的人才;還有的把大學定位為“紅色工程師的搖籃”。至于教師和學生則又有不同理解,有的教師為了生存需要發表論文,把研究生當作生產論文的勞力;有的學生把自己當作導師的打工仔。當然,把上大學當作混文憑、裝門面的也不乏其人。還有人因為領導提倡干部要“知識化”,將上大學、混一張學士、碩士、博士文憑作為升官發財的階梯。
大學應起什么作用,辦大學到底為什么,這需要從歷史中考察。
舉世著名的牛津和劍橋大學,有著七八百年光榮歷史,對近代大學發展也有著重要影響。不過,對近代大學發展有著更為重要影響的,要數以下3所大學。
第一所是成立于1794年的巴黎綜合工業學校。這所學校有幾樣革新是以往大學所沒有的。一是對平民招生。這在法國大革命之后,針對以往只對貴族招生無疑是一項重大舉措。二是大規模招生。以往大學招生量很少,大致是一位教師指導若干學生,大規模招生要求成百學生集中上課,于是適合針對大批學生共同學習的教材和教學計劃應運而生。三是厚基礎教學。學生入學頭兩年一律不分專業,一起學習數、理、化等公共基礎課,這些基礎課并不針對學生將來可能的專業,而純粹以提高知識水平為目的,為學生今后各種發展打好基礎,兩年后再根據學生興趣分不同專業。由于巴黎綜合工業學校改革效果很好,后來世界許多理工科大學都照搬它的教學計劃,引用它的教材。有一種說法,認為巴黎綜合工業大學是現代大學之母。
世界上現代工科教育大致也是從巴黎綜合工業學校開始的。特別是1811年出版的泊松兩卷本《理論力學》和1826年出版的納維《力學及其在結構與機械中的應用》對后來工科教育影響很大。后來世界各國的工科基礎課《理論力學》和《材料力學》的基本教學內容就是在這兩本教材基礎上形成的。
由于巴黎綜合工業學校的成功,先后培養了一大批世界一流學術大師,如柯西、拉格朗日、龐加萊、納維、菲涅爾、卡諾、圣維南、泊松、科里奧利、埃菲爾、居里夫婦等。近代力學特別是連續介質力學、數學分析的嚴格化和波動光學的復活等都是從那里開始的。
第二所是成立于1810年的柏林洪堡大學,這所國家資助、男女合校的高等學府是當時普魯士教育大臣、德國著名學者、教育改革家威廉·馮·洪堡(W ilhem von Humboldt)創辦的。
雖然巴黎綜合工業學校主張平民可以入學,但它當初禁止招收女生,而柏林大學則去除這條限制,主張男女合校。巴黎綜合工業學校雖然主張教學厚基礎,但不管是它還是以前各種學校,都或多或少以培養針對社會某種行業需要或就業為其最終教學目的。而柏林大學提出辦學宗旨是以求知和研究為主,大學不為政治、經濟社會利益所左右,要與之保持一定距離,強調大學在管理和學術上的自主性,即教授治校。它包含3層含義,一是大學獨立于政府管理系統,即“獨立于一切國家組織形式”;二是大學獨立于社會經濟生活,科學目的在于探索純粹的學問和真理,而不在于滿足實際的社會需要;三是寂寞是從事學問的重要條件,大學教師和學生應甘于寂寞,不為任何俗務所干擾,完全潛心于科學。這是近代脫離政治和社會俗務的一所真正自由的大學,也是第一所新制的教授治校大學。由于這種辦學精神對于歐洲乃至世界的影響都相當深遠,所以柏林大學被譽為現代大學之父。
高度自治、高度學術自由的氛圍下,培育了德國一代名流——馬克思、恩格斯、愛因斯坦、普朗克、海涅、黑格爾、玻恩、赫茲、費爾巴哈、舒曼、馮·諾依曼,他們都出自柏林大學,出自該大學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有29位。20世紀初這里在科學上成為量子力學與相對論的發源地。
第三所大學是成立于1876年的霍普金斯大學,美國第一所研究型大學,并且是一所世界頂級著名私立大學。柏林大學在世界上首開大學脫離政治和俗務、專心搞研究之風氣,霍普金斯大學一開始便效法柏林大學,專門招收從事研究的研究生,在世界上首開招收研究生的歷史,其招收研究生的辦法后來為世界其他大學普遍采用,對科學和教育發展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由于研究生培養的成功,與霍普金斯大學有關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有36位,此外,該校還培養出一大批美國政界、軍界、企業界名人。
以上3所對世界大學教育影響較大的大學,以及后來以它們為榜樣所開辦的大學,其主要功能是研究學問,即生產、傳播和保留知識。現在一般稱為研究型大學,區別于以職業培訓為主的專科型大學。
我國大學起步較晚,1895年洋務派主將盛宣懷主持創辦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開始建立時只有工程、礦物、機器、律例4門,顯然主旨是為洋務服務,很難說是一所研究型大學。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失敗后留下的唯一成果,其目的是全面向西方學習。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在開學典禮講話中明確提出大學任務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1907年蔡元培40歲的時候,赴德求學4年,深受德國大學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影響。因此,他將大學任務定位為“研究高深學問”,實際就是柏林大學辦學宗旨,要將北大辦成一所研究型大學。
蔡元培還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這正是柏林大學辦學脫離政治和俗務羈絆、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主張。由于蔡元培身體力行對舊北大進行改造,北京大學在一個階段出現了一批對中華民族現代化產生深遠影響的人物。蔡元培為改造北大,費盡心機,雖然成效卓著,但終因處處掣肘而無法徹底實現自己對新教育的理想,1927年辭去北大校長職務。
蔡元培在北大經營11年,他曾經擔任中法大學等校校長,對于中國大學教育產生積極影響,蔡元培之后的胡適和蔣夢麟也是按照蔡元培辦學方針經營北大的。1937年北大與清華、南開成立西南聯大期間,同樣是按照蔡元培辦學理念辦學,實際是按照國際的大學功能理念辦事。所以,盡管在極為艱難的抗戰期間,西南聯大還是集中一批優秀學者,做出世界一流研究成果。如華羅庚在數學、許寶騄在統計、吳大猷在物理、周培源在湍流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蔡元培
2011年,清華大學慶祝建校100周年,列舉了在清華歷史上出現的29位大師級學者,這29位無一例外都是清華大學從1911年到1949年這38年之間聘請或培養的。從1949年到2011年62年間,竟連一位大師也沒有出,所列舉大師都出在100年的前三分之一時期。
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對大學功能不同認識有關,不同辦學方針造成不同結果。前一時期以“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為目標,用梅貽琦的話是“大師之謂也”,以追求培養有學問的大師為己任;而后一時期方針變了,對大學功能理解變了,當然結果不同。
1949年之后,我們喊了60多年“教改”,不斷改來改去。我們的“教改”離國際主流大學辦學理念到底近還是遠了?比一比我們歷次提出的教改口號和改革措施與蔡元培、梅貽琦當年的提法和做法,問題出在什么地方顯而易見。如果再不認真反思,按原來那一套繼續走下去,所謂趕超世界一流大學,不過緣木求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