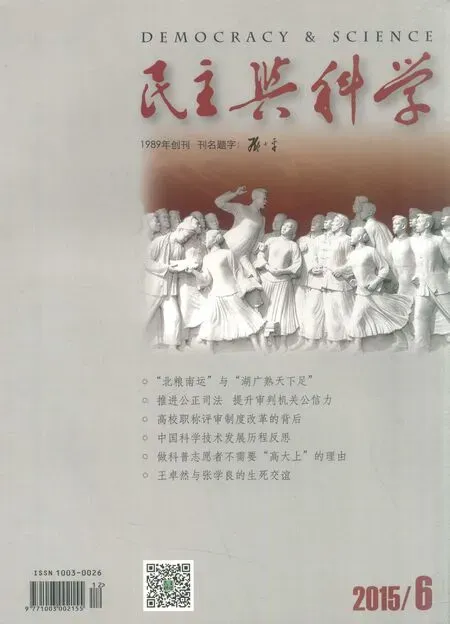兩位中國近代物理學家的不同遭遇和命運
■ 蔣百川
(作者為美國諾瓦東南大學榮譽教授)
每個人的一生都在時空坐標里留下一條軌跡,往往這個人和另一個人的軌跡在某時某地有個交點或有一段重合。過了這個交匯,兩條軌跡又開始各奔東西,造成每個人生的不同精彩和悲哀。中國近代物理學家吳大猷與周同慶就是這一情形。
吳大猷和周同慶都生于1907年,吳大猷9月29日在廣州出生。他的父親是1901年滿清舉人,1909年他全家由粵搬遷至天津,隨后父親去吉林做官,不幸因關外大疫,卒于1911年。其后,舉家重返廣州,吳大猷在廣東念完小學,1921年由其伯父帶去天津入南開中學,1925年考入南開大學礦科,次年因學校停辦礦科,改學理科物理系。1929年,他在南開畢業,遂參加清華大學公費留美考試,未取。那年考取此公費名額的則是剛從清華大學畢業的周同慶。
周同慶12月21日生于江蘇省昆山縣,父親在昆山一所中學任國文教師。周14歲時便獨自一人到南京就讀東南大學附屬中學。此時葉企孫在東南大學任教,在葉的影響下,周同慶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1925年周同慶中學畢業時,葉企孫剛應聘到清華大學創辦物理系,周同慶報考清華大學物理系并成為第一屆本科生。當時一共僅4人,他們是王淦昌、施士元、周同慶和鐘間。1929年畢業,周同慶隨即以物理系第1名考取“庚款”公費,成為該屆學生中最早出國一位。他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讀研究生,師從K.T.康普頓(Com p ton)(現查明因康普頓在1930年便離開普林斯頓,周的導師實為Hen ry D.Sm y th,作者注)。在普林斯頓大學,周同慶取得相當出色的研究成果,先后發表3篇學術論文,《氬放電管中的振動和移動輝紋》(1931)發表在《物理評論》、《二氧化硫的發射和吸收光譜》(1932)收錄在1932年美國《物理學會會刊》、博士論文《二氧化硫的光譜》(1933)也發表在《物理評論》。他因成績優異獲得金鑰匙獎,但他沒有舍得花美元去購買那把金鑰匙,僅僅帶回一紙獎狀。1933年他取道歐洲,途經英國、德國、蘇聯回國。

1931年,吳大猷在饒毓泰和葉企孫推薦下,獲得中華文化基金會乙種研究獎助學金。在多所學校中,吳大猷選了學費低廉的密西根大學。做博士論文時,師從量子力學教授S.A.Goudsm it。當時密西根大學是研究紅外分子光譜的中心。紅外分子光譜在1920年代至30年代上半期是物理研究主流,該校許多教授都是當時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此外,物理系每年都有一個暑期研討會,邀請當時的杰出科學家來演講。吳大猷在學習期間,曾有機會聽到迪拉克(Dirac,1933年諾貝爾獎得主)、費米(Ferm i,1938年諾貝爾獎得主)、海森堡(Heisenberg,1932年諾貝爾獎得主)等學者的講課。1933年春天,吳大猷開始發表論文。1933年6月,以論文《電勢與原子光譜的問題》獲博士學位。同年他再獲中基會研究獎金繼續留校研究。在博士論文中,他提出“鈾元素之后是否有一系列14個化學性質相同的元素”問題,且作理論推斷。因為當時還沒有現代計算機,他主要靠手算完成這項重要成果。1951年,G.T.西博格 (Seaborg) 因發現9種以上的超鈾元素獲諾貝爾化學獎。1989年兩人見面時,西博格對他說:“當年能獲得諾貝爾獎,應歸功于你的論文。”
周同慶回國后,于1933年至1936年間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從事電磁學、分子運動論及熱力學、近代物理及實驗、原子與分子光譜、氣體傳導等多門課程教學工作并進行汞分子光譜研究。在北京大學3年間,周同慶埋頭實驗室,在困難條件下建立起光柵光譜實驗室,帶領一位助教,完成了2篇論文。
吳大猷1934年夏回國,開始在北大物理系從事原子分子光譜研究。當時北大物理系教授只有饒毓泰、朱物華、周同慶、張宗蠡和副教授龍際云。吳大猷積極從事理論及實驗工作,同時教授古典力學、量子力學及理論物理等課程,在3年中陸續于國內、美國、英國期刊上,發表15篇論文。
1936年,周同慶應聘到南京中央大學物理系,并擔任系主任,教授光學課程。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周同慶隨中央大學遷往重慶,仍任物理系主任。到重慶后,除教學工作外,抱著科學救國思想,周同慶帶領李博、林大中2位同事爭取到當時水利部及水工試驗所撥款,受委托研制“聲測水深儀”項目,探測河道水深及水中暗礁。他們設計制造儀器,還坐船到江上實地試驗。經過2年多努力,終于制成《磁伸縮式高頻聲波自動記錄的回聲測聲儀》。有關論文發表在1943年《中央研究院學術匯刊》上。這項研究成果獲得當時教育部嘉獎并移交有關部門使用。1943年秋,周同慶轉到當時也已遷至重慶的交通大學任物理系教授。抗戰時期重慶的大學教授薪水很低,教授也不得不做一些兼差,增加收入,貼補家用。所以他又兼任軍令部技術室物理組長,拿校級軍官待遇。1945年,抗戰勝利復員前,他辭去這一兼職。
1937年吳大猷攜妻費盡周折由天津抵達成都,在國立四川大學任講座教授,1938年初夏飛昆明,歸隊于西南聯合大學。當年秋天,為紀念北大40周年,著手寫作《多原子分子的結構及其振動光譜》(英文)專著,稿成于1939年夏,由老師饒毓泰帶去上海付印。1939年該書獲中央研究院丁文江獎金3000元。該書印出后曾寄國外同行,受到各方稱譽。光譜學家E.U. Condon來信說:“想不到在抗戰那樣艱苦條件下還能寫出這樣的書。”并決定將此書列入由他主編的叢書中,由Prentice-Hall書局出版發行。1943年該書獲教育部科學研究著作一等獎。吳大猷在西南聯大教了8年書,教過的科目有電磁學、近代物理、量子力學及經典力學等。
1943年,周同慶轉交通大學任教,1946年隨校遷回上海。在交通大學期間,周同慶曾任理學院院長并親自講授普通物理及原子物理課程,同時帶領教師建立原子物理實驗室,開展原子物理學方面的科學研究。此實驗室至1948年已初具規模。
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兩地投擲兩枚原子彈,加速日本侵略者投降,同時也喚起中國人制造原子彈的夢想。抗戰勝利后不久,重慶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陳誠邀請數學教授華羅庚、物理學教授吳大猷、化學教授曾昭掄赴重慶商討發展原子武器事宜。3位教授擬訂計劃,遴選優秀青年學者赴美考察。吳大猷挑選朱光亞、李政道;華羅庚推舉孫本旺,到美國后又推舉徐賢修;曾昭掄推薦唐敖慶、王瑞酰。吳大猷9月抵美,隨即向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委員R.F. Bacher探詢有關協助我國建立研究機構的可能性并陸續將建議和報告寄回軍政部即后來的國防部。吳大猷1946年秋返回母校密西根大學任訪問教授,并開始從事核子物理工作。1947至1948年轉哥倫比亞大學做原子、分子束實驗工作并講授原子物理課程。1948年吳大猷被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出國之初,原擬以二三年為期限回國向國防部復命,然此時大陸情勢日變,國防部已無暇國防科技計劃。1949年秋,加拿大國家科學院設300余博士后獎金,廣攬世界各國人才。吳大猷被聘為理論物理組主任,決定暫留海外,候觀局勢再行返國。后來,華羅庚與曾昭掄都返回大陸。
在大陸,周同慶從1949年下半年起,指導助教方俊鑫建立供電子管抽氣用玻璃高真空系統,并抽調中法藥廠玻璃工蔡祖泉到交通大學做玻璃吹制工作。1950年后,進口來源完全斷絕,原子物理實驗室X光管陰極燈絲損壞,所有X射線實驗被迫停頓,更顯迫切需要真空技術。交通大學與東北衛生部合作,開始研制醫用X光管,由電機系試制高頻感應爐,物理系試制電子管,并由周同慶主持正式成立“電子管工作委員會”。1952年底全國院系調整,交通大學物理系部分人員并入復旦大學,周同慶和方俊鑫來到復旦大學,與輕工業部上海精密醫療儀器廠華中一等一起從事X光管研究。1953年3月底成立復旦大學X光管研制實驗室,繼續接受工業部門(此時改為輕工業部上海醫療器械廠)委托,由政府調集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原從事該項工作大部分人員,恢復和發展因院系調整而中斷的研究工作。由周同慶任主任,方俊鑫任副主任,華中一為廠代表。經過一段時間艱苦努力,解決了真空鑄靶、陰極設計、銅與玻璃管狀封接等一系列關鍵技術,并制定了排氣和除氣規范等一系列工藝規程文件,1953年秋試制成功我國第一個醫用封閉式X光管。1954年1月,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技術報告,5月2日在同一刊物上發表《研制X光管工作的新結果》,正式宣布研制成功。1955年,周同慶被聘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學部委員(院士)。1956年周同慶參加“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討論,與王大珩一起,主持物理學規劃光學部分的制訂。同年,周同慶在復旦被評定為一級教授。1957年他邀請各大學光譜學教師到復旦大學,研討我國高等學校光譜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對我國光譜學發展起了推動作用。1956年初,周同慶擔任新成立的光學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有近10位青年教師,都在他指導下工作,共同努力建立光學專門化。
吳大猷1956年應胡適之邀赴臺任教,在臺大和“清大”聯合主辦的研究生班講授古典力學和量子力學,兼及流體力學和核子間的交互作用問題。當時臺灣有物理學博士學位的還不到3位。此后他每年利用寒暑假期回臺工作4至6個月。在美加,他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瑞士洛桑大學、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理工學院、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1957年獲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其研究工作多在原子分子結構及光譜、核子散射、大氣物理、電離體及氣體方程式、統計物理、相對論等方面。1962年他協助在臺灣恢復“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并在1962~1976年間任所長。1965年任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物理與天文系主任。1967年在吳大猷建議下,臺灣成立“國家安全會議”,下設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特命吳大猷為主任委員。1978年吳從紐約大學退休,后長居臺灣,1979年擔任“教育部科學教育委員會”主委。1983~1994年出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一生共發表了120余篇科學論文,15本科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專著,在專著中,7冊為《理論物理》英文著作,是供研究生用的教科書。此外還有7冊《吳大猷文選》,敘述在臺灣20余年工作回顧,也是臺灣科學發展歷史性資料。
1957年,吳大猷建議制定長期發展學術政策,1958年胡適由美返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再請吳大猷擬出具體方案后,始得“教育部長”梅貽琦及“行政院院長”陳誠支持,翌年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此舉打開了政府直接支持學術研究的局面,對臺灣科學發展意義極為重大。
相同期間,大陸經歷了反右運動。1957年夏在復旦大學,在沒有得到周同慶同意之下,他的兩個研究生被下放到農村勞動,回校后直接分配做教師,這種釜底抽薪的方式使他的研究因此中斷。1958年,周同慶受到批判、斗爭。直到1961年,他參加了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摘帽”的廣州會議,情況開始有些好轉。此時,周同慶雖然是學部委員,但得不到充足研究經費資助以及研究人員的配備。他當時只能帶領兩三位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做光譜線輪廓研究,這是一個很小的研究小組。1963年,光學教研室中一位黨員教師提出研制激光器,得到校黨委支持。按照周同慶的學術造詣及在物理學界的地位,理應請他出來主持、指導激光研究。但是,周同慶始終沒有能參加這項工作。筆者記得在1964或1965年一次校慶學術報告會上,周同慶做了一個關于氣體激光的報告。當時我很納悶,他沒有參加系里激光器研制工作,但卻能說得如此深入淺出,明晰易懂。現在看到他的學生所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說:“多年之后,我在協助周同慶先生的子女整理周先生的遺稿時發現,周先生從那時候起讀了許多關于激光的文獻資料,還準備寫有關激光的文章。可見,周同慶先生一開始就對激光研究非常感興趣,只是沒有機會直接參加研究工作而已。”激光是上世紀60年代初光學領域的重大發現,其開創者Char los H. Tow nes為此獲196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作為當時中國光學頂尖教授,居然會被物理系一名助教排斥在激光研制工作之外,可見此事何等荒唐!
1970年以后,周同慶被分派到“理科大批判組”,翻譯科學資料。當時被組織到“大批判組”翻譯資料的有復旦大學理科各系許多老教授,教授們對于“理科大批判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一點也不熱心,但大都不公開表示出來。周同慶卻說:“愛因斯坦的科學理論是以大量實驗為基礎的,如果要批判相對論,就要拿出實驗依據來。”從中可見他的堅持真理,胸懷坦蕩。
周同慶從1970年開始,長期疾病纏身,1989年2月13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2歲。吳大猷1994年在臺灣退休,但仍執教于講壇,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他或許是世界上僅見的一位登壇講學近70年的物理大師,2000年3月4日,他病逝于臺北。回顧這兩位前輩的生活軌跡,感慨萬千。他們都有過的輝煌成就,值得后人敬仰。他們在上世紀50年代之后的極大差別,只能歸結到個人的選擇,以及所遇到的不同政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