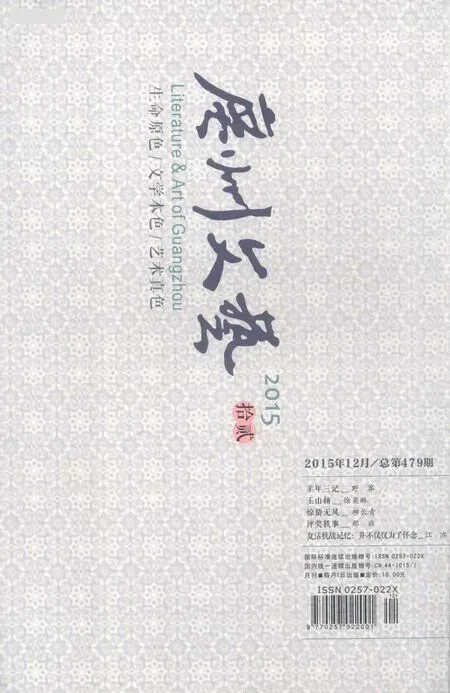錯字別字何其多!
Text_徐暢
天驕藝鑒
錯字別字何其多!
Text_徐暢
(接上期)

圖5-17
“長宜君”朱文古璽(圖5-17)。“君”字“口”旁作一實心點(丁),宜讀作“長宜尹丁”。

圖5-18
“蜀千”朱文古璽(圖5-18),自注:“蜀人”。甲骨文“千”字,從“人”,加一橫分化為“千”。印文的“人”字因“蜀”字的一筆延長到“人”字上,為“人”增添了一橫,印文的“人”字應釋為“千”。
黃子高 《續三十五舉》云:“字為心畫,當先知此字從某從某,于六書之義云何?下筆自然有意。”
劉紹藜 《印文輯略》云:“近來坊本多謬,作者果悉心研稽,一遵古法,義自不失,茍徒于刀法,章法求之,而書法源流昧然罔覺,豈不貽笑!”前賢告誡我們:如不想貽笑大方則要慎重用字,“悉心研稽,一遵古法(六書之義)”。
六、誤用舊釋、誤釋

圖6-1


圖6-2
“含有象謝無私”朱文古璽(圖6-1)。“亡(無)”、“私”兩字的左側加了合文符,屬自造合文,典籍無先例,而且“私”字錯誤,自環為“厶(私)”,此為“曲”字。《說文》:“謝,辭去也。從言,射聲。”戰國文字有2 例(圖6-2)。印文的“謝”字從“言”,“躳”聲,何琳儀疑為“”之繁文,讀“信”。兩字皆誤用。

圖6-3
“公而忘私”朱文古璽(圖6-3)。“厶(私)”在古璽中作空心的倒三角形、半圓形、圓圈形、扁方抹角形、盾牌形。印文右側作凹進一塊的舊釋“厶(私)”字,何琳儀先生改釋“曲”,舊釋“厶(私)鉨”應釋為“曲鉨”,讀“鉤鉨”,《詩·周南·南有樛木》傳引句作曲。《說文》:“句,曲也。”這均可成為其佐證。“鉤為璽印之別稱,以璽鈕如鉤而名。”晉璽“正行亡曲”,讀“正行無曲”,“正”、“曲”對文見義。拙編 《古璽印圖典》中,“鉤鉨”、“正行無曲”即引用何琳儀的說法。印文“私”,因誤用舊釋而誤為“曲”。

圖6-4

圖6-5



圖6-6

圖6-7

圖6-8

圖6-9

圖6-10





圖6-11




圖6-12

圖6-13
“聯五和平”朱文古璽(圖6-4),自注:“聯網和平”。網,甲骨文象漁網之形(圖6-5)。金文或作省減,作部首時網紋只留一個叉,如“”、“羅”等字(圖6-6)。為戰國文字所承襲,如“網”字的繁文“”,用手拉網(圖6-7),會意。《說文》中“網”作雙叉(圖6-8),或體作形聲字,附加聲旁“亡”(圖6-9),云夢古隸的“網”頭仍作一個叉(圖6-10)。印文所引用舊釋的“網”字顯然要比上述引用的一個叉的“網”字少了上面的一橫,故宜隸定為橫書的“五”字。從 《金文編》開始誤釋“五”為“網”(圖6-11),《古文》從之,但 《漢語》、《類編》、《戰編》已注意到這一點,故“網”字條內均未引用這些橫書的“五”字。值得注意的是,《金文編》中“五”字條下的保卣、何尊、宅簋、伯中父簋等上下兩橫皆與叉齊平,不出頭,與“網”字形同(圖6-12),不過,一是橫書,一是豎書罷了。吳王光鑒的“五”字亦與之形同(圖6-13)。所以,橫書的“五”字不應釋為“網”字。橫書在古璽及陶文中有多例可列舉,茲不贅述。

圖6-14




圖6-15




圖6-16
“愛不遉人”朱文古璽(圖6-14),自注“愛不遠人”。“遠”字為舊釋,印文與“遠”字不類。此字從“貞”(圖6-15),《類編》收甲骨文10例,西周到戰國的金文8例。戰國文字9例,茲舉7例,尤以包山牘“貞”字與印文“遉”字所從最似。《戰編》收“遉”字2例(圖6-16),與印文全同,印文應釋“遉”不釋“遠”,顯然為舊釋所誤。“遉”,同“偵”,巡邏偵察之意。“愛不遉人”,與原詞意義迥然有別。
七、用錯字,或釋文有誤

圖7-1




圖7-2

圖7-3
“壺中乍(作)客”白文古璽(圖7-1)。“客”字,《說文》:“客,寄也。從宀,各聲。”大篆“客”字字例甚多,與印文不諧。是釋文的誤釋?印文可能釋為“仙”?但“仙”字大篆、小篆均無字例;在漢碑、漢金文中,“仙”字與“僊”字同時使用(圖7-2),形體與此印文有別。印文用大篆的偏旁拼造新字“仙”是否妥當?實則小篆有“僊”字字形(圖7-3),《說文》:“僊,長生僊去。從人從,亦聲。”段玉裁注:“《聲類》:‘仙,今僊字。’蓋仙行而僊廢矣。”可見“僊”、“仙”為古今字。“僊”字已在戰國古籍中使用,如 《莊子·天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用小篆字形“僊”大篆化是否比用“仙”字更貼切一些呢?何況那時無“仙”字。或者刻秦印用“僊”字,可以省去不少麻煩。

圖7-4







圖7-5
“書者散也”白文古璽(圖7-4)。“聿”,甲骨文從“又”(象手側形),從“筆”之象形(圖7-5),借體象形。《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以后皆作“筆”。“聿”、“筆”為古今字。“聿”,“筆”之初文。一豎是筆桿,下面像筆毛,筆毛向下。印文“聿”字卻筆毛向上,倒毛了,怎么能作筆?
馬衡 《凡將齋金石叢稿》曰:“近來古璽日多,用印及刻印者多喜仿效,宜視其文字恰合者應之,否則寧拒其請求,免貽不識字之譏。”
八、用字不慎,或偏旁錯誤

圖8-1


圖8-2


圖8-3

圖8-4
“慎思敏行”朱文古璽(圖8-1)。“慎”字古文作“昚”,下從“日”(圖8-2),印文卻從“目”,顯然是錯誤的。《說文》:“敏,疾也。從攴,每聲。”大篆“敏”字或從“又”(圖8-3)。古璽“王敏”(圖8-4)中,“敏”之異文,“攴”省作“又”,“又”、“攴”形旁通用,請詳參拙文 《古璽印中的偏旁通用例》。印文“敏”字少了“又”旁(圖8-1),誤為“每”字,又錯一字。

圖8-5



圖8-6

圖8-7


圖8-8

圖8-9

圖8-10
“大方亡隅”白文古璽(圖8-5)。印文“隅”,從“墉”或“郭”的初文(圖8-6)。印文誤為“大方亡(無)墉禺”,或曰“大方無郭禺”五字。“隅”,《漢語》錄有古璽字形(圖8-7),從“阝(阜)”,“禺”聲。左耳同“阜(土山)”,從“阜”旁的字多與山地、山或地形地物有關。“阝”(左耳,讀阜),甲骨文象峭崖有阪級之形(圖8-8),或象三峰立置之形(圖8-9),或省簡作一豎三橫狀(圖8-10),戰國文字承襲商周金文,“阜”與“墉”是兩個不同形不同義的字。此印用字偏旁錯誤。

圖8-11


圖8-12
“徐暘日利長年”朱文漢印(圖8-11)。青年晚輩相贈璽印自當歡喜,卻常常有錯,“暢”誤為“暘”。“暘”,日出。古稱“暘(旸)谷”為日出之處。《說文》:“暘,日出也。《虞書》曰:‘曰暘谷。’”《書·堯典》孔傳:“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畼”(圖8-12)誤為“暘”,偏旁錯誤。
這類印作主要是印作者對文字學的缺失而造成用字的錯誤,編輯也疏于審查把關。周靖 《篆隸考異·凡例》曰:“邊(偏)旁湊合,為筆之害。今文人學士,專騁筆姿,不求根據,遂至魯魚互殽,義理乖舛。”
九、用俗(字),不用正(字)

圖9-1





圖9-2

圖9-3
“修身”朱文古璽(圖9-1)。《說文》:“修,飾也。從彡,攸聲。”“修”的義項很多,“修”同“脩”,“修”是后起字。戰國文字(圖9-2)及小篆(圖9-3)有“脩”,指干肉。《說文》:“脩,脯也。從肉,攸聲。”古藉中“脩”與“修”通。既然有大篆的“脩”字,為什么還要用小篆的“修”再大篆化呢?古璽用“脩”為正字;秦印、圓朱文用“修”為正字。
先秦文字異體叢生,正俗的辨別非常重要。沿著漢字發展主軸的字形是正字,其他的是異體字。如大篆“堂”字,或從“土”或從“立”,“土”、“立”義近,偏旁可以通用,則從“土”的“堂”字是正字,從“立”的“堂”字是異體字、俗字,《說文》稱異體為或體。“壯”字或從“土”或從“立”,從“土”的“壯”字是正字,從“立”的“壯”字是俗字。“粟”字或從“米”或從“禾”,從“米”的“粟”字是正字,從“禾”的“粟”字是俗字。
十、任意支解,使象形字無象可尋

圖10-1

圖10-4


圖10-2


圖10-5


圖10-3

圖10-6
“唯善以爲寶”白文古璽(圖10-1)。“爲”字,甲骨文從“爪”,從“象”,會人手牽象役使其勞作之意(圖10-2),引申有作為之意。印文“爲”字左側的爪應是手的側面形狀(圖10-3),看到的是三只手指,怎么能分開呢?印文卻作一豎彎加兩個點,是一只斷了手指的手,與古文字的“爪”相去甚遠。此印文與舀鼎“爲”字(圖10-4)相近,舀鼎“爲”字“口”形的符號是象頭,頭上豎彎是象鼻,下面是象的背部連著前、后兩腿,再下是象尾。象背連后腿處是豐腴圓渾的臀部,可是印文卻作“橫豎橫”三畫,作者似乎要表現他高超的刀法,卻把圓潤的屁股搞沒了,象形意趣也沒了,其他幾字何嘗不是如此?“唯”,周早召卣銘文為鳥之側形,頭、身、腳爪皆明了(圖10-5)。周晚楚公逆镈銘文中,鳥形的爪訛變為連在一長豎下面的兩短橫(圖10-6)。印文卻把鳥爪離開鳥身寫成“匚”形,象形意味頓失。多么嬌好優美的象形文字被如此拙劣地糟蹋了。“善”,西周金文從“羊”,“誩(言之繁文)”聲。戰國文字承襲金文,多從一“言”。“羊”象羊頭、羊角之形。羊角向下彎曲;牛角向上高挑。印文“善”字,羊角作兩點(丁),“口”聲,皆誤。這玩的是楷書吧?“寶”,從“宀”,從“貝”,從“玉”,會藏“貝”于室內之意,這么多繁文不取,卻用了個簡體,還是個平頂房。

圖10-7


圖10-8






圖10-9





圖10-10




圖10-11
“豪氣沖天”漢印(圖10-7)。豪字從“高”從“豕”(圖10-8),“高”作二橫,未見像印文作兩點的,不僅古隸、小篆如此,漢印也如此(圖10-9)。“氣”作古隸字形,是四字中唯一正確的字。“沖”,大水“沖”了龍王廟,《說文》:“沖,涌搖也。”徐鍇 《說文系傳》:“從水,中聲。”甲骨文、金文、古璽、小篆、古隸、漢代的“沖”字皆從“水”(圖10-10)。“沖”同“沖”。《玉篇》:“沖,俗沖字。”《老子》第四十五章:“大盈若沖,其用無窮。”“沖”為今“衝”字的簡化字。印文“沖”字從“=”(冰),不知出于何典。用簡化字拼造篆書,失之遠矣。“天”字比古隸字形(圖10-11)多了一橫,而且下面變成了“丌(其)”,整字筆畫不相連續,可見輕率任意如此。

圖10-12
“樂且晏口”朱文古璽(圖10-12),自注:“樂且晏如”。“晏”字“女”旁重復使用兩次卻又缺少重文符“=”。“樂”字的“木”旁根須脫離了樹干,為無本之木。“晏”字的“安”旁“宀”(宮室屋頂之側形)符成了“八”字形,無房如何能安?而且字也不規范,中間的兩橫兩邊懸空沒連上。古文字中的象形字和由象形字構成的偏旁,以及由象形字構成的指事字、會意字,其中的象形符號(或稱部件)是絕對不可以支解分離的。此印釋為:囗且囗口。

圖10-13


圖10-14
“李琦”白文古璽(圖10-13)。“李”字“子”旁身首異處,受刎頸之災,一字變成兩字:“杏”和“又”。“琦”字(圖10-14)“奇”旁上從“大”。印文的“大”字卻如“冰”字,況且有現成的例字為何不用,卻要去造字呢?

圖10-15
“陸維釗”漢印(圖10-15)。“釗”,不知出于何典何器。楷書左右結構的字在先秦文字中有作上下結構的,但必定是占一字位置。漢印用字比較規范方整,有一字占兩字位置的,但硬把左右結構的“釗”字作上下結構并占兩字位置,漢印似無先例。
張懷瓘云:“古文篆籀都無節角,蓋欲方而有規,員不失矩,如人露筋骨乃病也。”有一些書者印人對“六書”一竅不通,否則象形字怎么可以任意支解、五馬分尸呢?篆,引也。篆書皆線條構成,象形字及由象形字構成的指事字、會意字的線條是不可以隨意斷開的,結構是不可以隨意分拆的。實心的圓點在戰國齊系文字里多見,或作飾筆,或代以橫畫,皆有法度與規則,不可以胡來。印學家的一些話值得我們深思:
明代朱簡 《印經》說:“今說印法者,多則減,少則增,已開謬妄之門。而曰上字之下,如作下字之頭,右字之左,如作左字之右,是何說也?……”原來隨意增減篆文筆畫、挪動支解偏旁部首的陋習幾百年前已開此風,為印論家所不齒。
《糞翁印存·題記》云:“摹印只須工字體,形容剝蝕要天然,休拌性命論刀法,秦漢何人有技傳。”
袁三俊 《篆刻十三略》云:“結構不精則筆畫散漫,或密實,或疏朗,字體各別。務使血脈貫通,氣象圓轉。”
十一、不倫不類,多體混雜

圖11-1
“申明私印”朱文印(圖11-1)。“申”字為楷書,“印”字為草書。“眀”,同“明”,《石門頌》作此形。“明”字右旁似草書,左旁為楷書,一字竟兩體摻和,不倫不類。“私”字楷書右旁作“幺”,此為何字?不識。楷書、草書兩種書體置于一印之中,甚至一字之中,還有一個錯字,極不協調。

圖11-2

圖11-3
“合十寫真經”朱文印(圖11-2)。五個字不知出于何體,大篆?小篆?繆篆?古隸?四不象故不能斷定璽印的品類。“合”,張著血盆大嘴,是念經呢?還是寫經呢?況且“口”形與篆書“口”形不合,卻與春秋者減鐘的“丁”字相似(圖11-3)。鼻子連著眉毛,一塌糊涂,多處不該連的地方連,該連的地方又不連,如“經”字的絞絲旁,該連不連,使擰成麻花狀的絲緒變成了葫蘆形,象形意義何在?除“十”字外,其余四字皆自抒胸臆,不忍目睹!四個字出于何經何典?篆書的結體?篆體取勢?線條質感?篆書的美感又何在?

圖11-4
圖11-4白文古璽,自注:“尚墨”。“尚”字,只見屋頂(宀)不見“口”旁。或者說這個漏雨的屋頂夸張了些,應該是“尚”字的字頭八字符,但是“口”符卻成了“田”旁。《說文》:“墨,書墨也。從土,黑,黑亦聲。”而印文“墨”字像一堆柴火堆得很高,分不清黑與土。“尚墨”兩字在先秦文字中有許多字例可以引用,但是此印字形怪異,布白奇崛,傳統古璽中未見,是先鋒派,還是印象派、現代派?實在不敢恭維。
前賢的諄諄教導值得深思:
“漢鼎漢鐙又為一體,皆可采取入印,惟須善為配合,不可勉強。但朝代懸隔之文字,不可雜湊一處。”(陳衡恪 《槐堂摹印淺說》)
“篆文須字字有來歷,不可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圓朱文尤以此為重要之條件。”(馬衡 《凡將齋金石叢稿》)
十二、錯字綜合癥,一印多誤

圖12-1


圖12-2


圖12-3




圖12-4

圖12-5



圖12-6
“陽剛之氣”朱文古璽(圖12-1)。“陽”字取周中柳鼎字形。“剛”字取甲骨文字形(圖12-2),《說文》:“剛,彊,斷也。從刀,岡聲。”林義光《文源》以為是“以刀斷網”,會意。印文“刀”旁用朱文,“網”旁用白文,不過外兩豎是朱文,中間網格是白文。雖然戰國古璽有幾方朱白相間印,但這種“陰陽頭”的字在古璽及漢印中尚未見過,實為“創新”。“之”字甲骨文從“止”,從“一”,會足趾所至之意(圖12-3)。《類編》收戰國文字15例,其中僅2例上二或三畫與下橫不連,余皆相連(圖12-4),印文上三筆與下橫畫分離,因此印非楚簡入印,四字又與楚簡風格不類,印文“之”的構形與“璽彙0129”相似,但足趾分離,如何能至?象形文字是不能分解的。
“氣”大篆作“氣”(圖12-5)。小篆、古隸作“氣”(圖12-6),或作“氣”,“氣”應是秦代時增“米”。作者妄加“米”旁,畫蛇添足,還把“米”旁變成了楚簡筆意。

圖12-7
“幸福安康”朱文古璽(圖12-7)。印文“安”字與戰國齊陳純釜“安”字形近。“幸”字從“犬”,與漢金文“幸”字近似。“康”字,甲金文字均從“水”,“庚”聲,“漮”之初文。從殷周到秦漢的文字中都無法找到能印證印文“康”字的字形,尤其是字頭與字腳(四點作火字底)實在怪異。“福”字大誤。“福”,形聲字。《說文》:“福,祐也。從示,畐聲。”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甲骨文)象兩手奉尊于前,或省廾,或并省示(筆者按:即 ‘畐’字),即后世之福字。”印文從“示”,“畕”聲。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說:“畕,從二田,會疆界之意。金文或作畕。或作畺,在上中下各加一橫,劃分疆界之意尤為明顯。”《說文》:“畕,比田也。從二田。”“畕”,“畺”、“疆”之初文。印文從“示”,“畕”聲,為何字?只好請印作者自己回答了。

圖12-8

圖12-9





圖12-10
“看太陽昇起”朱文古璽(圖12-8)。“太”,春秋文字在大字下加分化符號(圖12-9),戰國文字“大”旁之下加一短橫或兩短橫亦為分化符號(圖12-10),卻沒有見過像印文那樣用圓點的。典籍之中“大”、“太”、“泰”三字往往通用;“大”為象形,“太”為分化,“泰”為假借。印文“大”旁之下不加一短橫或兩短橫,卻加“丁”,應讀為“大丁”。“昇”字為后起字,大篆無,小篆有,是新附字。《說文新附》:“昇,日上也。從日,升聲。古只用升。”“古只用升”亦即先秦時期只用“升”,而不用“昇”。亦是畫蛇添足。

圖12-11



圖12-12

圖12-13
“欲窮千里目”朱文古璽(圖12-11)。“欲”字左半“谷”旁是大篆(圖12-12),右半“欠”旁是小篆(圖12-13),“谷”旁“口”符作方塊形,丁字。《說文》:“窮,極也。從穴,躳聲。”“躳”字右旁是兩口,印文卻作一丁一口。“目”是繆篆,“千”、“里”是大篆,“窮”為小篆,用字大雜燴。

圖12-14


圖12-15


圖12-16



圖12-17






圖12-18






圖12-19
“寵辱若驚”白文古璽(圖12-14)。《說文》:“寵,尊居也。從宀,龍聲。”甲骨文(圖12-15)、西周金文(圖12-16)、戰國文字(圖12-17)都有字例。印文“龍”旁卻由“爪”、“屮”、“月”、“丁”組合,與經典字例相差甚遠。有古人使用的文字,為什么要自己去創造或變化呢?
“若”,商承祚 《殷虛文字類編》:“案:卜辭諸若字象人舉手而跽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圖12-18),古 ‘諾’與 ‘若’為一字,故若字訓為順。古金文 ‘若’字與此略同。”何琳儀 《古文》說:“甲骨文 ‘若’,象人跽以雙手順發之形。”
印文“若”字從“艸”,從“又”,即商周文字的“芻”(圖12-19),與“若”字不類。“芻”,甲骨文從“又”,從“艸”,會從手割艸之意。西周 《散盤》同其形。戰國文字“又”旁訛作“彐”字形,“艸”訛變為兩個“×”或兩個“+”,小篆又訛變。所以,許氏誤認為:“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金文編》誤“芻”為“若”,印文可能據此而誤。

圖12-20


圖12-21





圖12-22



圖12-23
“馬大哈”朱文古璽(圖12-20)。印文“馬”字用的是戰國齊系文字(圖12-21),但“馬”字出頭,長了一角。“大”字卻用的是楚系文字(圖12-22),為使協調規整,作了“印化”,卻失去筆意、傾斜度和開張度,與筆畫對稱的“冰”字(圖12-23)形同。“哈”字是楷書才有的字形,拼合造字而成篆書,純屬虛構。這種民間俗語諺語,還有一些政論性的詞語,篆書沒有的字不要自造,可以改用隸書、楷書、行書或草書書刻,以維護祖國古文字的純潔性。
責任編輯梁智強
徐暢/Xu Chang
1941年4月生于成都,1946年移居南京。現為西泠印社理事、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兼職教授、南京藝術學院書法研究生課程班導師、南京曉莊學院教育科學院兼職教授、中國書法函授大學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南京印社副社長、原中國標準草書學社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