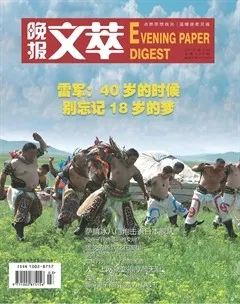人一上網就變得厚顏無恥
網絡是個被文人雅士吹唬得神乎其神的地方,也是個被同樣的文人雅士貶斥得一文不值的地方。至于我個人,對于自己不懂或是不太懂的事物,總是出言謹慎,不敢輕易臧否。去年被人強拉去給網上文學做了一次評委,結果惹得網絡精英們很不高興,說既不上網又不在網上發表文章的人如何能有資格當網上文學的評委?精英們的批評讓我感到口服心服,既不上網又不能在網上發表文章的人的確沒有資格當網上文學的評委,就像既不欣賞音樂又不能創作音樂的人沒資格去給音樂比賽當評委一樣。
自我檢討之后,一種強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90年代不上網,就像70年代不入黨。”這比喻聽起來很順耳,但并不貼切。70年代要入黨,除了自己表現積極,服從領導、團結同志之外,關鍵還要家庭出身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現得再積極也是白搭,弄不好還會給你戴上一頂“偽裝進步”的大帽子。而90年代的上網,只要家里有臺電腦、有根電話線,隨時都可以上,一不要寫申請,二不要什么人批準,更不需積極表現。但我為什么遲遲不上網呢?因為我對涉及到機械、電子之類的東西心懷恐懼,總認為這些東西高深無比。后來我坐出租車,與司機閑談起來。司機說,上網比上床還要容易,上床前你還要洗腳刷牙脫衣服,上網前什么都不需要。他還說,開車比上網還要容易。我問他像我這樣的人用一個月的工夫能不能學會開車?他說:別說是您,把一頭豬綁在駕駛盤前一個月,它也會了。
在這個司機的鼓勵下,我終于上了網。上網之后發現,所謂網上文學跟網下的文學其實也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區別,那就是:網上的文學比網下的文學,更加隨意、更加大膽,換言之,就是更加可以胡說八道。一個能在紙上寫作的人,只要不吝惜電話費和網絡費,完全可以在網上寫作。唱歌跳舞你不會,胡說八道難道還不會嗎?漸漸地我也知道,大多數的網上文學,都是在網下寫了然后貼上去的。因為寫作時就知道了要往網上貼,所以這在網下創作的東西,也就具有了網上文學胡說八道也可以叫做“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素質。有了這些經驗之后,所以當網站讓我開一個專欄時,我稍微猶豫了一下就答應了。今后,我也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我也是個網絡寫作者,我已經取得了給網絡文學當評委的資格了。為了證明網下的寫作與網上的寫作差不多,現在我就把我幾年前為自己的散文、隨筆集《會唱歌的墻》寫的序貼上來: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隨筆集,但我更愿意說這是一盤羊雜碎。
據說寫散文、隨筆要有思想,我沒有思想,有的只是一些粗俗的胡思亂想;據說寫散文、隨筆要有學問,我沒有學問,有的只是一些道聽途說的野語村言;據說寫散文要有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理想,這兩樣東西我都沒有,有的只是草民的念頭和生理性的感受,所以我輕易不敢把這些東西集中起來示眾。那么為什么又把它們收集了起來呢?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版稅,第二個原因嘛,我想既然說百花齊放那就應該讓狗尾巴花也放,既然要百家爭鳴就允許讓烏鴉也鳴。就像我的存在使一直嘲笑我相貌丑陋的那些貌比潘安的男作家更潘安一樣,我的散文、隨筆集的出版,也會使中國的散文、隨筆集們深刻的顯得更深刻,淵博的顯得更淵博,高尚的顯得更高尚,美好的顯得更美好。
這不過是我的夢想而已,其實在這個年代里,多一本書或是少一本書,就像菜市上多一棵白菜還是少一棵白菜一樣,甚至還不如。
前幾年有人批評人家臺灣的三毛,說她的那些關于大沙漠的散文是胡編的。我覺得這些人真是迂腐,誰告訴你散文、隨筆都是真的?你回頭看看幾十年來咱們那些著名的散文、隨筆,有幾篇是真的?大家伙兒都心照不宣地胡編了幾十年了,為什么不許人家三毛胡編?
咱家也坦率地承認,咱家那些散文隨筆基本上也是編的。咱家從來沒去過什么俄羅斯,但咱家硬寫了兩篇長達萬言的俄羅斯散記,咱家寫俄羅斯草原,寫俄羅斯邊城,寫俄羅斯少女,寫俄羅斯奶牛,寫俄羅斯電影院里放映中國的《地道戰》,寫俄羅斯小販在自由市場上倒賣微型原子彈。咱家的經驗是,越是沒影的事,越是容易寫得繪聲繪色。寫時你千萬別心虛,你要想到,越是那些所謂的散文、隨筆大師的作品,越是他娘的胡扯大膽,天下的巧事兒怎么可能都讓他碰到了呢?如果你經常地翻翻那本十分暢銷的《讀者文摘》,你就會明白,那些感人至深的寫親身經歷的文章,其實都是克隆文。
還有那些“訪談錄”“自傳”“傳記”“日記”,我勸大家都把它們當成三流小說來讀,誰如果拿它們當了真,誰就上了作者的當。
短短的上網經驗使我體會到,人一上網,馬上就變得厚顏無恥,馬上就變得膽大包天。我之所以答應在網上開專欄,就是要借助網絡厚顏無恥地吹捧自己,就是要借助網絡膽大包天地批評別人。當然我也知道,下了網后,這些吹捧和批評就會像屁一樣消散——甚至連屁都不如。當然我也知道,上網的人里邊確實也有很多品德高尚、思想健康、表里如一的人,但“歪船野馬偏激文章”,如果此文傷害了誰,就請放開喉嚨罵一聲:呸,這算什么狗屁文章!
(一一摘自《莫言散文新編》,文化藝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