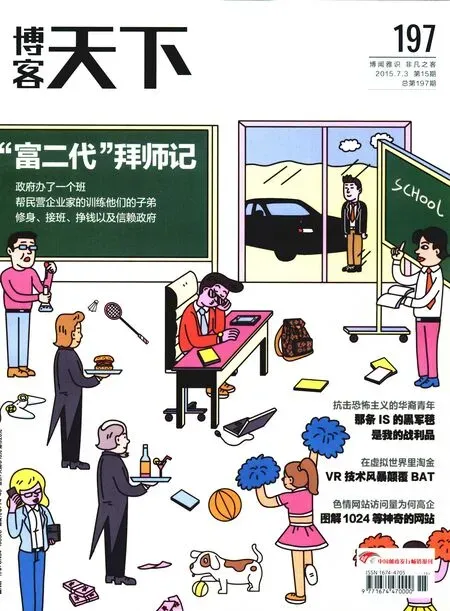蘇陽草一樣歌唱在草野
文 陳雨編輯 王波圖 尹夕遠
蘇陽草一樣歌唱在草野
文 陳雨編輯 王波圖 尹夕遠
民謠歌手蘇陽不愿走捷徑,他仍相信最簡單的邏輯——“靠作品還是保險一點。”

一個農民必須學會工作的過程
歌手老狼覺得,10年前第一次見到的蘇陽和之后不太一樣。
2005年夏天,老狼在銀川做節目,晚上被朋友帶到龍門客棧酒吧見一個“本地歌手”。進門時,一屋子人推杯換盞,興致正高,蘇陽帶著酒態唱起了歌。
“他那天表現得挺痞的,有點小流氓的那種色彩,對,流氓氣質。”老狼對當天的很多細節已記不清,但和《博客天下》說起蘇陽,依然有些興奮。
蘇陽唱的是自己寫的歌,調子用的是寧夏特有的民間山歌“花兒”。音樂一響,“整個酒吧都躁起來了”,老狼聽了一驚。
樂評人耳東曾記錄過類似的經歷。“當時我坐在舞臺對面,蘇陽一張口我就知道錯了,真不該坐他正對面,他一嗓門,‘騎騾子呀嗎上高山呀,上高山呀嗎望平川吶,平川里有那牡丹的花開鮮’,感覺音箱快給唱破了,惡狠狠的音符把我砸個七竅生煙……他其實完全可以不用音箱,就像他祖先們那樣,扯起嗓子就唱,聲音直沖云端。”那天晚上,音樂中西北人特有的豪爽、狡黠,加上生活化的歌詞和搖滾曲風,讓老狼覺得刺激、鮮活,特別地被打動。他直接找蘇陽要了小樣,回京后放給了音樂廠牌十三月的老板盧中強聽。后者毫不猶豫地簽下了蘇陽,為他組建樂隊,成員包括汪峰現在的吉他手伢子、子曰秋野樂隊鼓手陸勛等,1年后制作發行了第一張專輯《賢良》。
2006年是國內民謠的黃金時代,蘇陽、李志、周云蓬、萬曉利等一眾音樂人集中涌現。蘇陽的《賢良》則是他們中的異類。樂評人鄒小櫻說那是當年最有分量的一張華語唱片,“給滿分都不為過。”
“樂隊里的每一個成員都在倍感驕傲地用母語歌唱著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鮮花、愛情、勞動人民。其山藥蛋式的情感使得他們可以突破搖滾的界限,與民族音樂交相輝映。”他曾這樣評價道。
“我們老說民族融合什么的,就是把民歌融入現在的音樂里面,把一些老的所謂的假民歌改成晚會式的編曲之類的,都做得特別生硬,聽起來特別無聊。”但老狼在蘇陽當時唱歌的狀態里,聽到了一個生活在西北的男人“內心的真實流露”。
如今,那個自稱”老漢“的西北人已經搬到北京生活了10年,46歲的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在音樂節、商演和小型巡演中度過。7月26日,蘇陽將第三次登上張北草原音樂節的舞臺。
但到了北京后,蘇陽好像變了一個人。“再見他,他就變成一個特別謹慎,而且特別憨厚、樸實的人。”老狼發現蘇陽錄音和排練時,有些“小心翼翼的”。
“我三十五六歲之前都在寧夏,這個改不掉的,我最重要的表達方式在那個地方形成。”蘇陽向《博客天下》解釋,“以前的環境,在銀川時大家一起玩兒的松弛的感覺,那里面形成的東西更自然。”
然而在北京,要學的東西和需要考慮的問題都越來越多。無論排練還是演出,蘇陽都在為更職業化而進行調整。“你已經從那個環境脫離出來了,很多事都不能拒絕,各有各應該做的。”
坐地鐵時,他經常被警察挑中查身份證,問職業,答說搞音樂的,警察不相信。和樂隊一起去音樂節,蘇陽臨上場被保安攔下,“只有歌手能進,你不能”。第一次去十三月的辦公室時,蘇陽難得穿了件白襯衣,但和西褲、懶漢鞋的搭配還是讓他被誤認成農民工。
音樂方面磨合的過程似乎更不順利。
剛來北京不久的一次演出調音時,話筒嘯叫得厲害,調音師姜北生建議蘇陽在吉他的音孔上蓋個蓋子。這是控制嘯叫的常用手段,但蘇陽說不行,不能改變我的演奏習慣,都得按照我的習慣來。倆人吵了一架。
“現在我的琴上都要加蓋子,但作為在銀川成長起來的樂手,當時很不理解,總覺得別人在壓制你。”蘇陽說。
類似的“水土不服”還發生在《賢良》的制作過程中。專輯的錄音和混音由姜北生負責,錄音時他為蘇陽配備了當時最貴的一支電容話筒,靈敏度、頻響等各方面都優于平時演出時用的動圈話筒。
蘇陽試了試,說太怪了。換成普通話筒后,“聲音反倒對了”。
錄完專輯里的10首歌,像給其他歌手制作唱片時一樣,姜北生花了三四天時間修唱,音修得特別準,節奏特別齊,蘇陽聽完直接否了。理由很簡單,“不能這樣,修成這樣就失去了我的意義,沒有我的味道了。”
姜北生很不理解,但也意識到這畢竟是工作。“我得按照他的要求來,等于之前修過的全白費,錄成什么樣基本最后就是什么樣。”
不過,他現在認為,蘇陽當時的堅持是正確的。之后和萬曉利、李志、逃跑計劃、曲婉婷等音樂人合作時,相比音準和節奏,姜北生將他們錄音時的狀態放到了更優先考慮的位置。
2010年,制作第二張專輯《像草一樣》時,他為蘇陽準備的依然是支普通話筒,沒有精修。
當姜北生逐漸適應音樂上的差異化時,蘇陽則開始學習向規則靠攏,不再像在銀川時那樣隨心所欲。他慢慢理解調音的復雜,漸漸提高對燈光、舞臺設計的要求,也培養起了版權意識。在采訪前一天,蘇陽第一次在排練中使用了節拍器。
進棚錄音時,節拍器必不可少,但排練中為了追求現場感,蘇陽始終不肯打開,而樂隊也習慣于此。
“比如說《賢良》,我一般都是前面唱得慢,后面唱得快,這個在統一的節奏里是不允許的。節拍器只要一打開,從頭到尾只有一個點。所以我就嫌它,我想快怎么辦?”
但新加入的鼓手王洪濤不斷問蘇陽,能不能打開節拍器對一下。“你們一激動,我實在不知道什么時候該快什么時候該慢。”他勸蘇陽,“大家都用,其實這東西不會傷害你,你不要害怕。”
排練結束后,蘇陽覺得的確沒什么,他意識到這只是“需要克服的一個習慣罷了”。
“說得夸張一點,這就是一個農民必須學會工作的過程。”蘇陽說,“其實歌曲這個東西,不管誰唱,最終是你表達什么,科技進步也不會影響的。我不排斥科學。”
但老狼還是覺得有些遺憾。10年前那張小樣中的毛刺和特別粗糙的地方,消失在了專輯中。“后來的錄音方式可能還是太規整、太干凈了,反而失去了特別粗糙的那種‘刺骨的香味’。”
你是一個什么人?
蘇陽在《一席》演講中講過一個故事。在寧夏采風時,他曾經拜訪過西海固唱“花兒”的民間藝人馬生林。老人當時70歲左右,眼睛潮濕,坐在褥子上唱著“尕妹你是牡丹花園長,二阿哥是空中的鳳凰”,用得是“花兒”《割韭菜》的旋律,聲音顫抖、干枯,像從土里傳出來。幾個小孫子吵吵鬧鬧地圍在老人身旁。老人不理他們,一直在唱,唱著唱著抓住了年紀最小、最不聽話的孫子的手,意思是讓他別鬧。小孫子不解,用方言問,“爺,你干啥呢?”老人依舊不理,繼續唱。
蘇陽覺得馬生林就像一棵很老很老的樹,旁邊都是嘰嘰喳喳的小鳥,干凈的院子里有陽光,農具都很安靜地擺在那里。那一刻,蘇陽忽然意識到,這就是西海固人的生活,因為貧瘠,所以他們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
老人唱的那首“花兒”被蘇陽改成了歌曲《鳳凰》,收錄在《賢良》中,歌詞的下一句是“我懸來呢嗎懸去的個沒忘想,吊死到白牡丹的樹啊上”,帶著西北特有的悲傷和蒼涼。
第一張專輯中還有一首類似的歌《賀蘭山下》,歌中唱“路上的人呀,停車問一聲你從哪里來?送走了這個,送走了那個,說死也不分開。你看那流水不回頭,夕陽下了山,不知他們都活在哪里,可再也不回來”。
錄音前,姜北生去看了蘇陽的一次排練,排到《賀蘭山下》時,他感動得差點哭了。
去了一趟賀蘭山后,他明白了當時擊中自己的荒涼感從何而來。“可能好幾天不會有一輛車從那里經過,突然過來一輛車,比如說是修路的,你真的忍不住會聊天、喝水,問‘你從哪里來’。這就是西北人的勁兒。”
在評價蘇陽的音樂時,不止一個人提到了“歸屬感”、“根”。
樂評人耳東曾說:“他的音樂不僅僅只是好聽,還讓我感受到很多失去的東西,或者是從未存在過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哈拉(說大話),除了你腳下正踏著的那一平方土地,那就是你最真實的生活,你應該去歌唱它,蘇陽就是如此做了而已。”
蘇陽出生在浙江溫嶺,7歲半隨母親北上和父親團聚。
16歲在西安上中專時,他第一次接觸吉他,畢業后便加入了上世紀80年代末的“走穴”大潮,在各地的歌舞廳、夜總會演出。
1995年回銀川后,他組建了寧夏第一支原創搖滾樂隊“透明樂隊”。受Guns&Roses、Bon Jovi、恐怖海峽等樂隊和音樂人的影響,他開始模仿著創作了一系列金屬風格的作品。樂隊演出當時在銀川頗受歡迎,但4年后仍以解散收場。
這4年中,蘇陽開始思考一個“返璞歸真”的問題—音樂到底是干什么的。他給自己的答案是,個人的表達方式。
“既然是個人的表達方式,那么你是一個什么人?”
“你是一個成長在銀川這么一個非常小的城市里的非常普通的人,從外地遷徙來,在支援大西北的一對工人家庭里的一個普通孩子。你真實的身份是這些,而不是留著長頭發,千萬人在下面(聽),搖滾的那些。”
這一番思考和自問自答,
讓他厭倦并最終放棄了對歐美搖滾樂的模仿。此后,蘇陽轉向了更本土、看似更傳統的表達方式。2003年春節,初到西北時覺得“黃土高坡一點也不好看”的蘇陽,開始到西北各地走訪還會唱傳統民歌的人。他討厭用“采風”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行為。“我更想看到他們的生活,他們在生活里歌唱的態度,他們怎樣用身體來完成歌唱,而不是用五線譜或者阿拉伯數字來記下它們的旋律。”他曾在專輯文案中寫道。
這種尋找與記錄一直持續到現在,已經變成了蘇陽的習慣。他喜歡和這些民間藝人待在一起,喝著酒,講講奇聞異事,慢慢聊到音樂,想聽聽民歌,他們也不會拒絕,一切都保持著農村的樣子。有時候喝到后半夜唱起來,回頭再聽錄音,甚至聽不太懂都唱了些什么。
“喝一場酒,該知道的都知道,不知道的再找下一個。”12年過去,西北的大部分民歌種類都進入了蘇陽的“資料庫”。他沒有整理過這些錄音,但它們漸漸影響了他的創作。
他不再標著漢語拼音唱英文歌,而是回歸習慣的西北方言,并開始像山歌一樣用比興的修辭方式表達感情。曲調上他開始融入西北的秦腔、小曲、“花兒”等。
蘇陽的樂隊有一名“編外成員”安彪,生前在寧夏秦腔劇團上班,是蘇陽的朋友,包辦了他作品里包括板胡、低胡、嗩吶、管子在內全部的民樂部分。兩次專輯制作時,蘇陽都專程把他從寧夏叫了過來。
“安彪特別厲害,什么都會,而且味道特別對。”姜北生頓了一下,想了想不知該怎么形容,“比如他嗩吶那個勁兒,好像就是西北人才能弄出來。”
安彪和蘇陽是在銀川的歌舞廳認識的。歌舞廳、夜總會是當地夜生活為數不多的去處,也是蘇陽這樣的本地樂手當時主要的謀生場所。

“那種二三線城市,真正的生活場景就是那樣的,娛樂、麻將、歌舞廳、啤酒,來回就是這些。掙錢了就是把這個規模化,上更豪華的歌舞廳,洗更牛逼的腳,然后買更豪華的車,打更大的麻將。”蘇陽說,“其實沒有太多的改變。”
這些熟悉的生活圖景直接進入了他的音樂。在《賢良》中他唱,“一學那賢良的王二姐呀,二學那開磨坊的李三娘……王二姐月光下站街旁呀,李三娘開的是紅磨坊”。在《長在銀川》中,他唱“我的家住在同心路邊上,那里有我的爹和娘”。到了《早操晚操》里,又有了“野蠻女友在蹦迪,昨個頭發紅變綠,今天又是藍盈盈,明天啥東西?”
西北給了蘇陽質樸,也造就了他狡黠的一面。
老狼用狡猾來形容10年前見到的那個蘇陽。“歌里說什么去扒寡婦的墻頭,從門口騙進半條腿,那個感覺,我操,我覺得特別好,特別真實,就是內心有點小騷情,躁動,特別準。”
到北京后,蘇陽不止一次地跟老狼說過自己的不習慣。“他說我在這兒寫不出東西來,很苦悶。”老狼回憶。
在北京生活了5年,蘇陽出了第二張專輯,音響和樂器上的把握都更進了一步。老狼聽出蘇陽在和這座城市的磨合中慢慢適應了新環境,而北京也開闊了他做音樂的眼界。
“但是相比第一張,第二張多了些‘花兒’里面特別深情、特別悲傷的東西。”
張北草原音樂節7年陣容變化


“你覺得是因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我沒有那么細致地去跟他探討內心的這些東西。”老狼說。
靠作品還是保險一點
蘇陽很瘦,總穿一身黑,采訪當天剛把本就不長的板寸理得貼著頭皮,攝影師拍照時,他有些拘謹地自嘲,“理完發是不是看著可壞了”。
打眼看去,蘇陽并不像音樂人,既不時髦也不藝術。
“他真正的魅力還是在草莓音樂節的舞臺上。”張彤說。他是蘇陽的朋友,2011年第一次見面時也犯了以貌取人的錯。后來在音樂節,他目睹了臺下一兩萬人口型完全一致地合唱蘇陽的歌,“你才發現那么多人真是喜歡他”。
蘇陽喜歡音樂節,認為在那里,音樂的好壞、演出的成功與否,遵循的都是簡單的邏輯—唱得好,看的人就多,唱得次,看的人就少。
“這個平臺是公正的、公平的,給每個人的機會都是平等的。”他也因此對2010年張北草原音樂節念念不忘。
“人和人之間不是被一種特定的東西規劃出來的。”蘇陽說,“他們是非常鮮明的不同的人,可能是都市里的白領、可能是縣城里農貿市場上的小老板,可能是個開茶樓的,可能是個賭鬼,然后他們湊到了一個場合里面去看你,這就是音樂的溝通能力,說明你的音樂是有價值的。”
那年張北的草長得很高,搖滾青年、抱孩子的婦女、翻墻進來的老鄉一起,在場地中營造出了一種有些混亂的集市感,讓當時在臺上的蘇陽覺得特別動人。
而每次音樂節演出結束后,蘇陽的專輯總賣得特別快。“我的觀眾其實都是唱回來的,沒有誰是聽說過蘇陽,但沒聽過歌。基本上都是先聽過歌,然后來說,哦,你就是那個唱歌的。”
蘇陽并不善于經營自己。2008年和十三月的合同到期后,他單干過幾年,自己組織樂隊、搞運營,既吃力效果又不好,直到2014年和摩登天空簽約。
“這個其實是很多藝術家的問題。”老狼說,“他沒法像李志那樣當領導,自己去經營,而且蘇陽也不善于在微博上、在網上跟歌迷互動。”他留意到蘇陽在慢慢一點點學習,只是還沒有那么游刃有余。
張彤曾經發過一條朋友圈,說蘇陽的價值遠遠被這個圈子和這個社會低估,所以現在才能非常廉價地消費他,真正有眼光的應該抄他的底了。但什么時候能大漲起來,他也不確定。
“蘇陽的優點是老實,缺點是太老實了。”張彤對蘇陽的固執深有體會—即使有出名的愿望,蘇陽也不愿意采取更為簡單有效的方法。好友、民謠音樂人馬條去參加了《中國好歌曲》,但這樣的選秀節目,并不在蘇陽的考慮范圍之內,他更愛說的是,“靠作品還是保險一點。”
“他有他自己做事的一套規則,這個規則怎么來的,我們也不太清楚。”張彤說。
在老狼眼里,10年間,蘇陽的變化并不大。他重復穿黑色衣服,理最普通的寸頭,自己買菜做飯,和朋友喝酒逗悶子,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每年回西北“采風”,不慌不忙地制作新專輯,寫一本書,參加一場場音樂節,用看上去笨的方法往前走。
姜北生覺得,這種平淡是因為蘇陽的年紀。2005年和十三月簽約時,蘇陽已經36歲,“整個人生的格調基本上有定位了”。
但這似乎更符合西北人的執拗與倔強。就像蘇陽在《像草一樣》中唱的:
“我要帶你去我的家鄉,那里有很多人,活著和你一樣,那里的鮮花呀,開在糞土之上,干枯的身子喲埋在地下喲,像草一樣,像草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