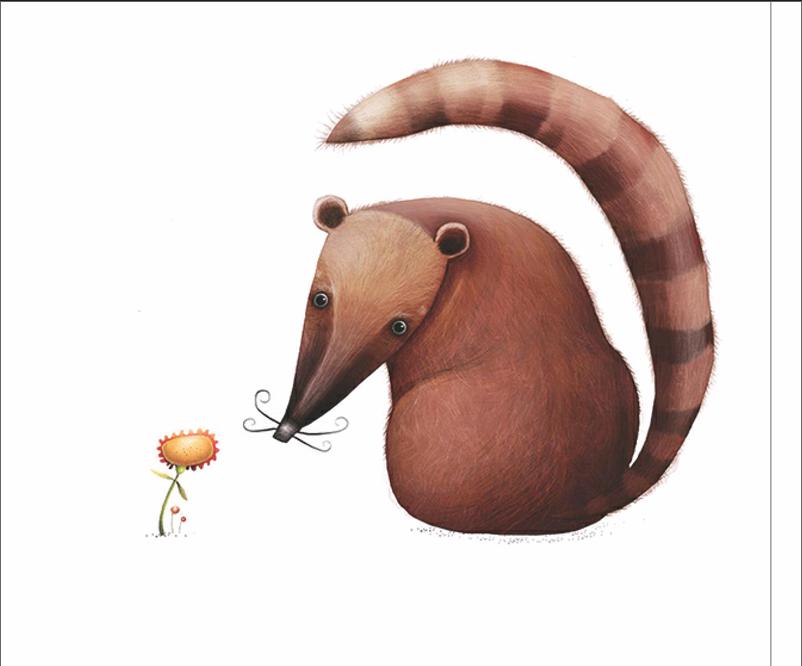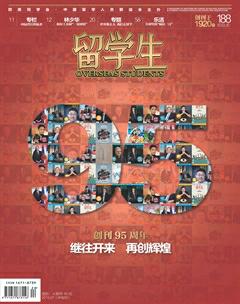兇猛背后的溫柔
胡剛剛
我在無意間看到加拿大野生動物攝影師保羅·尼克蘭(Paul Nicklen)于2013年為國家地理頻道所做的一段演講,講述了他被一只友好的豹斑海豹喂食企鵝的趣事。
人們素來視豹斑海豹為南極食物鏈頂端的神秘殺手,它們行動敏捷,牙齒鋒利,連鯊魚都要對其退避三舍。所以當保羅冒著生命危險用攝像頭對準一只豹斑海豹的時候,心中充滿恐懼。誰知這頭龐然大物看起來十分溫順,一開始,它試圖將一只企鵝不斷驅趕到保羅身邊供他捕獲,當看到他無動于衷時,干脆親自捉住這只企鵝送到他眼前。保羅說:“它不斷地將企鵝往我的相機里塞,似乎認為那就是我的嘴,這真是所有水下攝影師夢寐以求的一幕。”
看到這里,我不禁莞爾。其實動物界的復雜之處恰好在于其不可預測的單純性,而我們對此卻知之甚少。盡管物種之間絕大部分是吃與被吃的關系,但兇險中往往隱藏著觸動心弦的溫馨。
幾年前,我在哥斯達黎加邂逅了一種名叫coati的長鼻浣熊。它們經常成群結隊地在度假村里游蕩,比如當人在棕櫚樹間的吊床上小憩時,身下就會悄無聲息地穿過十幾只長鼻浣熊。度假村里的大喇叭天天播放警告:“千萬不要接近長鼻浣熊,因為它們兇猛異常。”這條警告先用英語播放一遍,再用西班牙語播放一遍,每隔一小時循環一次,令我覺得長鼻浣熊如同洪水猛獸,一看到它們我就像躲避瘟神一樣敬而遠之。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當地工作人員被長鼻浣熊團團包圍卻安然無恙。懷著好奇,我走上前一探究竟,發現它們居然正在向那位工作人員討要白糖。工作人員告訴我,其實動物的兇猛是事出有因的,長鼻浣熊的敵意來自于它們過度膽小的性格,如果你不去侵犯它們,它們絕不會主動進攻。“我與長鼻浣熊打交道好幾十年了,對它們的脾性了如指掌”,他笑著說,“它們像貓咪一樣嘴饞,只要一點點白糖就會令它們服服帖帖。”
于是我放下警戒,仔細觀察起這種奇特的動物來。它們渾身呈棕褐色,耳朵、眼框和前肢點綴著象牙色斑塊,深淺相交的環紋尾巴豎得高高的,與纖瘦的身體保持著靈活而悠雅的平衡。尖尖的鼻子像一個倒扣的漏斗,有些調皮地微微翹起。它們時不時站起身來,用短短的前足作揖討要美味,那可愛的樣子令我心融如蜜。我離它們非常近,甚至可以聽到它們濕潤的舌頭舔舐糖粒時與地面輕微的摩擦聲。當它們聽到我“咔嚓”按下相機快門時,只是抬頭瞅瞅我,動一動鼻尖,再繼續埋頭奮戰,仿佛我只不過是一株會出聲會移動的樹。這令我感到欣喜,一種放下執拗之后未曾期盼的欣喜。
很多時候,我們會對一知半解的事物產生莫明的恐懼,并為此付出莫名的代價,比如長久的偏見和無謂的負擔,這也許代表了成長過程中的一些駐點。雖說戒備之心不可無,但世間溫情總歸有,說不定哪天,當你孤獨無助的時候,就會有一只豹斑海豹將企鵝溫柔地送到你面前:“喏,這是我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