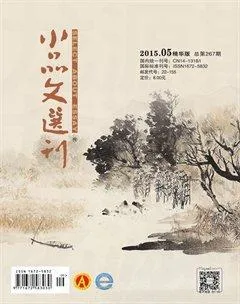一個人的魯迅
林賢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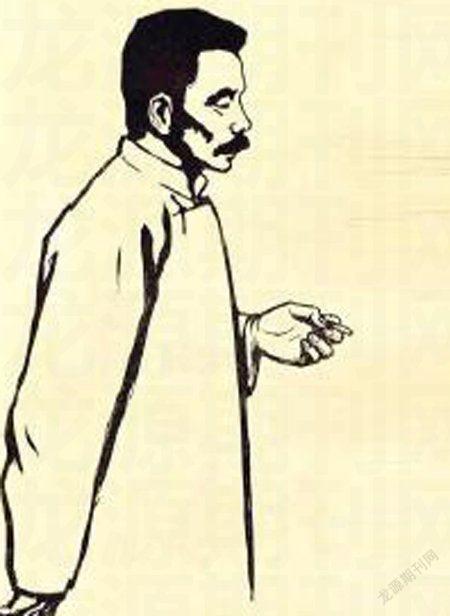
我發現,在魯迅的身上,有一種特異的力量。
在所有已故的和活著的中國人中間,我確乎不曾遇見有哪個人像他一樣令人如此神往。
魯迅生前曾兩次手書明代畫家項圣謨的題畫詩贈人,詩云:“風號大樹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短策且隨時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暮色昏暝,狂風肆虐,當此孤立無援之際,惟見大樹依然傲岸,挺立不移。如此形象,實在可以做魯迅個人的寫照。
魯迅植根于草野,他有書即名《野草》。同為植物,我懷疑“大樹”乃由“野草”變異而來,所以帶“草根性”。魯迅曾經注目于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草葉”是人民的象征。說到魯迅的特點,他的老友許壽裳說第一是“仁愛”:愛人類,愛人民,愛廣大的卑賤者和弱勢者。大樹以寬闊的樹冠成為野草的護衛者,而其枝干伸展向上直刺蒼天,惟在對抗來自上頭的風雨雷暴。
魯迅是哲人,天生的哲學氣質,不是那類經院式哲學家,所以無意于建構體系哲學。相反,他的哲學是反體系的,是問題化、斷片化的。
他的政治哲學,重點在解構權力,權力與社會(群眾)、權力與知識的關系尤為他所關注。他的歷史哲學,基礎是進化論的,但是對于東方歷史有反向的觀察,其間社會的停滯、倒退、羼雜與循環,在他那里有著深刻的揭示。至于他的人生哲學,則頗近于西方的存在哲學,重境遇,重主體性,重自由選擇,卻叫喊“絕望的反抗”。在許多論域中,諸如奴隸與奴隸性、流氓與流氓政治、革命與革命文學,都有獨到的發現,還有“包圍新論”、“隔膜”、“看客”、“中間物”等等,都是自創新詞,極富于個人創造的魅力。超短劇《過客》,可謂魯迅哲學的代表作。
哲學就是思想,在這里是與現實行動直接聯系的思想,戰士的思想。生命、思想、行動(寫作),三位一體。思想與生命的結合,“愛”與“憎”就成了重要的思想范疇。有大愛,必有大憎。憎根于愛。“在現在這個‘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這種憎愛觀貫穿了魯迅的全部哲學。這種哲學也不妨叫復仇的哲學。因為思想與行動的結合,使斗爭變得更明確、更深沉、更持久。是思想給戰士以高度,正如魯迅自己所描述的:“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魯迅一直強調戰士在中國的重要性,對于自己,也曾多次表明作為一個普通戰士———而非“領袖”、“盟主”、“導師”———的身份。說起魯迅,他固然有許多令人敬重且難以追躡的地方,而我最為欣賞的,仍是他的戰士的一面,尤其是自我批判。知識分子以啟蒙者自居,往往有優越感,這樣便把不少污穢的東西隱藏了起來,并因此與社會大眾相隔絕。魯迅說他身上有“可惡思想”,有“毒氣”和“鬼氣”,所以,在解剖別人的同時,要更多更無情面地解剖他自己。所有這些,都不是慣于文過飾非的知識分子容易做到的。
魯迅答復關于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事時,說他不配拿獎,因為世界上還有更多比他好的作家,又說在中國還沒有可得諾獎的人,假如瑞典要格外照顧“黃色臉皮人”,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結果將很壞。對于有人提出為他作傳,他答說自己平凡得很,要是連他也配作傳,中國將有四萬萬本傳記,一時塞破圖書館云。一個有大氣象的人,如此謙卑。這種平民主義的態度和作風,也是我特別欣賞的。
此外是戰士的風度。這種風度表現在對斗爭的熱戀上面。魯迅說他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生命,大半是為了敵人。他說他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就是為了給他們的世界多一點缺陷,直到自己厭倦了要脫掉為止。“但我覺得正人君子這回是可以審問我了:‘你知道苦了吧?你改悔不改悔?’”文中接著寫道,“我可以即刻答復:‘一點不苦,一點不悔,而是還很有趣的。’”他又這樣表示說:“我所憎惡的太多了,應該自己也得到憎惡,這才還有點像活在人間。”———這種風度在哪一位大師級人物中見過呢?
從前寫過一篇文章,說是喜歡看靈魂勝于看風景。郁達夫閱人無數,論及魯迅時,說是讀他有一種讓人明知是毒酒,喝了會死也要喝的況味。魯迅的靈魂,永遠躁動著、掙扎著、叫嘯著;這是一個自由的靈魂,大靈魂。
選自《一個人的魯迅》系列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