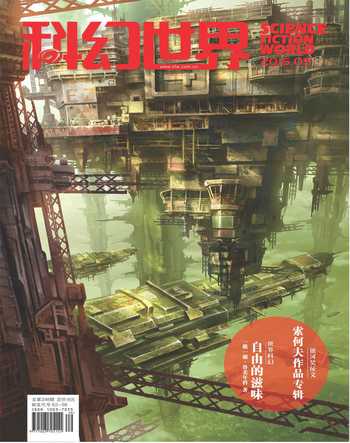創作談
索何夫
科幻世界雜志社的編輯希望我就第一次發表小說專輯寫點創作談,但真到了動筆的時候(好吧,準確地說其實是動鍵盤,除了考試和簽名之外,我已經很久不曾使用這一人類文化史上的偉大發明了),我才意識到這事兒比我預料中的要更有難度:本次專輯刊登的三篇作品《母校》《盲躍》和《斯巴達克斯》都已經完成多日,時間一久,就連我自己都有些記不太清楚具體的創作過程和創作時的想法了(在此衷心地希望讀者們能夠體諒我糟糕的記性)。
雖然我不很清楚其他作者是如何寫作的,但我自己的寫作習慣大致上可以歸納為“收集零散的靈感片段——尋找一個主題——把那些碰巧能夠與主題扯上關系的靈感變成小說”。湊巧的是,《母校》《盲躍》和《斯巴達克斯》都完成于去年的八到十月份,也就是去上海參加銀河獎的前后一段時間,而當時我恰好準備寫一些關于“自我”的小故事,于是,這三篇內容和背景看上去都大相徑庭的小說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算是一個系列——呃,我承認這么說有生拉硬扯的嫌疑,但當時我確實就是這么想的。
首先談談《盲躍》。這篇小說的最初靈感有一小部分來自美國科幻作家羅伯特·里德的《億萬個世界》——設想平行宇宙中的地球因為漫長演化過程中的微小差異而產生的不同生態模式,確實是一種相當有趣的思想實驗,而小說中的“安努”形象(某位網友不無詼諧地為它取了個“超級史萊姆”的形象綽號)在一定程度上則受到了克蘇魯神話的影響。不過從總體上而言,《盲躍》是一個關于人類殖民的寓言:與大多數中國人從歷史書里了解的那個“殖民主義”不同,廣義上的“殖民主義”的產生時間其實相當早——“殖民地”(colony)的詞根可以上溯到愛琴文明時代,而人類事實上的殖民活動甚至從現代智人最后一次走出非洲時就開始了。最早利用海洋進行大規模、有組織殖民活動的古代希臘人曾經為“殖民”下過一個定義:所謂“殖民”,就是在不存在社會以及維持社會存在所必要的秩序的地方將它們建立起來。
在對于“殖民”的所有定義和衍生定義中,我認為這個定義才最貼近“殖民”的原初含義:所謂“殖民”者,遷民于他地而使之繁衍生息也。而這個最原始的“殖民”概念所對應的恰恰是“無主之地”:因為無主,所以沒有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所必須的社會與社會秩序;而要與這片“無序”斗爭并重新建立起適宜人們繁衍生息的“有序”來,殖民者們就不得不動用一切手段與之斗爭——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些在“有序”的社會中人們所不屑的行為,無論是希臘人、維京人、波利尼西亞人還是尼德蘭人,在這一點上都是相同的。而這也正是小說中“安努”的計劃失敗的根本原因:它通過殖民者們攜帶的資料學習到了“有序”人類的行為模式,并想當然地按照這種行為模式制定計策,殊不知只有人類才真正了解人類。當然,由于社會道德的約束,人類對打破“有序”的行為往往是深惡痛絕的——這也是為什么小說中殖民者的真正挑選標準必須作為機密的緣故。
相對而言,《斯巴達克斯》這篇小說則不用多說——它的靈感,哦不,應該說是故事梗概,來自我在高中時代寫的一個關于機甲競技大賽的小故事。不過考慮到機甲這玩意兒隨著網絡小說的大繁榮已經變成了一個爛大街的、甚至足以令某些科幻迷見之反胃的概念,因此我將競賽換成了一場復古的羅馬式角斗。而小說中靠生物技術培育“軀體”的相關內容,則來自于過去和一些動物保護主義者在網上關于動物權益邊界展開的爭論(請不要聯想到《非理性時代》,其爭論的主題是什么樣的動物才應該享有權益)。相比于《盲躍》和《母校》,我個人認為《斯巴達克斯》在題材上與另兩篇小說大相徑庭,但既然勉強算是一個系列,它們之間自然也有一點關系——這一點我會在后面說明。
在全部三篇小說里,《母校》的創作過程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這篇小說源自我在好幾年前從果殼網上看到的一篇關于東亞地區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化的文章。但在小說基本完成時,我的朋友又向我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我以最近發生的流感疫情為題材寫點什么,為此我索性把《母校》整個兒推倒重來,一改再改,最后總算打磨出了一篇兼顧二者的小說。好在從整體上來看,將自然發生的流感疫情作為戲份不多的女主角對社會的報復手段,不但顯得更加自然,而且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人類用技術褻瀆自然,結果遭到了自然的殘酷報復”的深刻意境來(好吧,其實我寫小說的時候壓根兒沒想到這一點)。除此之外,小說中對“繁花之蔭”靠工業化生產手段人為“制造”出沉默寡言、缺少正常人七情六欲的社會精英的描寫,也算是我對未來社會“娛樂至死”傾向的一種回答——當越來越稀少的新生代因為日益豐富的娛樂活動而被磨光銳氣、失去進取心與求知欲后,這種看似不人道的手段或許倒不失為某種意義上的保持人類社會創新能力的可行之策……
呃,我要說的就是這些——等等,好像還少了什么?對了,我還得談談這三篇小說作為一個準系列(雖然彼此之間沒什么直接聯系)的共同點。就像我在前面說的那樣,我習慣于先確定主題,再把平時積累的靈感與點子“變現”,而《盲躍》《斯巴達克斯》和《母校》確實有一個共同的主題——“自我”。在《盲躍》中,擁有近乎無窮無盡的知識、經驗與智慧的超級生命體“安努”雖然在三篇小說的主角(或者準主角)中是最強大的一個,但它作為一個非社會性的生命體,擁有的其實僅僅是最為原始的“自我”:純粹基于生物本能的、僅僅局限于對本體的認知。在小說中,安努其實并不將像它一樣擁有智慧的人類視為與它同等的“他者”(這一點上很有點大清朝當年不承認“敵國”的風范),而只將這些與它截然不同的生物視為可以捕捉、吞噬、利用的資源,這正是其自我意識發育程度低下的體現。相對而言,誕生于偶然之中的“斯巴達克斯”雖然極其幼稚,獨立性相當低下,但因為與使用者共享記憶與知識的關系,反而擁有了高于安努的自我意識:由于不甘受到無償支配而自我毀滅的行為,恰恰意味著他至少意識到了“他者”——也就是那個直接支配著他的用戶——的存在,從這一角度而言,斯巴達克斯事實上更像是一個三到四歲的幼兒:能夠在感性層面下意識地意識到“我”和“他者”的區別,但還不足以進行進一步的理性思考。而《母校》中的“我”則是一個真正的成年人,雖然由于思維方式局限于刻板的模式之中,“我”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事實上是必然的,但這并不排斥“我”擁有成熟的自我意識的事實:因為“我”已經能夠脫離嬰幼兒式的、下意識的“自我”觀念,從理性的角度認識并憎恨那些從“我”還是一個受精卵時起就無處不在地支配著“我”的人和他們的行為,乃至通過理性的思考將憤怒延伸到造成了這些具體行為的社會上。從這種角度上講,這三篇小說的主角和準主角們,代表的正是自我意識的三個發展階段:基于本能,基于感性,基于理性。
啥?你問我這么寫要表達什么中心思想?說明什么宏大主旨?呃……怎么說呢?其實在確定這個主題的時候,就連我自己都不清楚這到底是為了表達什么。不過話說回來,我想表達什么其實也并不那么重要——反正一千個讀者眼里有一千個那啥,文藝作品受眾的觀感才是決定作品意義的關鍵因素。更何況,就算看不出中心思想和宏大主旨,那也無關緊要,畢竟小說首先要看的是故事,至于故事好不好,我只能靜待諸位讀者不吝筆墨(或者說電費和上網費),對我的這三篇小說多作評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