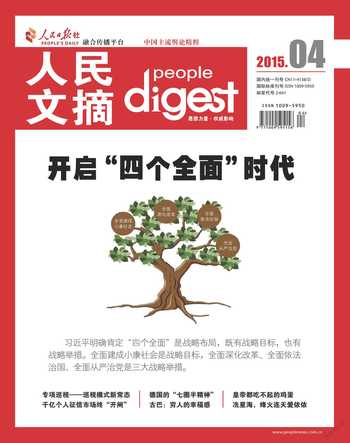澳大利亞站上反恐風口
雷墨


幸運之國不再幸運。澳大利亞雖然自2001年以來一直是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爭的得力干將,但它也是西方國家中少有的十多年來沒有遭到恐怖主義報復的“幸運者”。事實上,澳大利亞上一次本土遭襲還要追溯到1978年悉尼希爾頓酒店的恐怖爆炸。然而,2014年12月15日悉尼鬧市區一家咖啡館發生的人質劫持事件,給這種“幸運”蒙上了陰影。
假作真時真亦假
悉尼人質劫持案到底是刑事案件還是恐怖襲擊,在澳大利亞輿論乃至專業人士中都存在爭議。從曼·莫尼斯的背景看,他與澳大利亞國內以及國際伊斯蘭極端組織并沒有聯系。正因為此,有人認為莫尼斯只是個“山寨版”恐怖分子,他一手策劃并實施的人質劫持事件也不能被定義為恐怖襲擊。
從媒體披露的情況來看,曼·莫尼斯的履歷的確更像是一幅劣跡斑斑的拼圖,而不是一幅典型的恐怖分子標準像。莫尼斯上世紀90年代在伊朗開辦旅行社,之后卷款潛逃,于1996年來到澳大利亞,隨后以曾為伊朗情報部門工作、生命受到威脅為由申請政治避難。在澳期間,他給在阿富汗陣亡的澳大利亞軍人家屬寄恐嚇信。這次劫持人質前,他身背涉嫌殺害前妻、強奸等多項指控。他的“伊斯蘭教教長”頭銜也是自封的,甚至他的律師也稱其精神不正常。雖然莫尼斯劣跡斑斑,但澳司法部門認為他涉嫌的罪行都不帶政治動機,所以準予其假釋。
盡管如此,莫尼斯長期傾向于伊斯蘭極端主義卻是不爭的事實。除了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示支持“伊斯蘭國”,2014年11月他還在其個人網站上寫了一封宣示效忠“伊斯蘭國”的公開信。他也毫不掩飾自己對澳大利亞政府的敵意,曾公開聲明“以筆頭為槍、以文字為彈”與澳大利亞做斗爭。或許正因此,有分析人士將悉尼人質劫持案稱為“帶有政治動機的暴力事件”。
澳大利亞阿拉伯理事會創立者約瑟夫·瓦吉姆說:“他持有槍支,這是人質劫持事件。但他‘豎了旗’,那就是恐怖主義。”人質劫持案發生后,莫尼斯提出了三個要求:用“伊斯蘭國”旗幟交換一名人質;要求媒體報道人質劫持案是“伊斯蘭國”對澳大利亞的襲擊;以5名人質為交換條件與總理阿博特直接通話。莫尼斯沒有得到“伊斯蘭國”旗幟,而是掛出了類似的阿拉伯黑旗。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學者彼得·詹寧斯此前撰文稱,旗幟本質上帶有政治意涵,鑒于“伊斯蘭國”大肆把阿拉伯黑旗作為宣傳工具,莫尼斯掛出類似的黑旗絕不可能是巧合。
山雨欲來風滿樓
2014年12月18日,也就是悉尼人質劫持事件結束兩天后,澳大利亞警方又在悉尼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恐搜查行動,但并未逮捕任何人,澳警方聲稱該行動與悉尼人質劫持案無關。是不是莫尼斯讓澳警方繃緊了反恐神經已不重要,因為澳國內的確有比他更危險的“貨真價實”的恐怖嫌犯:就在悉尼人質劫持案發生前數小時,澳警方在悉尼突擊逮捕了一名25歲的男子,該男子被指控計劃在澳本土實施恐怖襲擊。而2014年9月澳警方在悉尼和布里斯班的突襲行動中抓獲的恐怖嫌犯,則更能說明澳大利亞反恐形勢的嚴峻性。
2014年9月18日,在澳大利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恐搜查行動中,警方逮捕了22歲的恐怖嫌犯奧馬詹·阿扎里。導致阿扎里被抓的是他與目前“伊斯蘭國”重要人物、澳籍恐怖分子阿里·巴亞雷的一番通話。在這段被澳情報部門截獲的電話交談中,巴亞雷指示阿扎里在澳大利亞策劃一起針對平民的“斬首行動”,拍成錄像后傳給“伊斯蘭國”對外發布。雖然恐怖分子的陰謀未能得逞,但阿扎里案件凸顯了澳大利亞反恐形勢的兩個明顯特征:一方面,澳大利亞已成為國際伊斯蘭極端勢力招募“圣戰者”的基地之一,澳國內恐怖分子與國際恐怖勢力呈現聯動態勢;另一方面,澳本土恐怖勢力漸成氣候,并正著手策劃單打獨斗的“獨狼”式恐怖襲擊。
根據澳大利亞安全與情報局的數據,上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赴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加入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澳大利亞人約為30人。敘利亞危機尤其是“伊斯蘭國”崛起后,這一數字快速上升。澳安全與情報局2014年9月12日向國會遞交的報告中顯示,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澳籍武裝分子有約60人,如果算上在其他地方“打圣戰”的澳籍武裝分子,人數多達150人。有媒體統計,以人口比例來衡量,澳大利亞是西方國家中對伊斯蘭極端分子海外軍團“人均貢獻率”最高的國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參戰的澳籍武裝分子中,有一半是巴亞雷招募的。澳情報部門還確認,澳國內約有100人對海外恐怖組織提供支持。阿扎里所受到的指控除了在澳本土策劃恐怖襲擊,還有給海外恐怖組織募集資金。
對于澳大利亞來說,這些國際伊斯蘭極端組織中的澳籍武裝分子,身在海外會影響澳國內本土恐怖分子,回到國內則對澳構成直接安全威脅。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反恐問題專家山姆·穆林斯認為,如同整個西方世界一樣,本土恐怖主義在澳大利亞社會已成為現實,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繼續存在。“作為美國的盟友以及東南亞的關鍵角色,澳大利亞很快就成為合理的攻擊目標。”
澳式反恐及爭議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澳大利亞的反恐都呈現積極主動的特點,甚至在某些領域更甚于歐美國家。在法律層面,有學者統計,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澳大利亞頒布了62部與反恐相關的法律,在數量上超過美國、英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比如,根據澳大利亞法律,前往敘利亞、伊拉克等地參與暴力恐怖活動,最高可判刑25年。從上述地區回國的人,必須“自證清白”,證明自己沒有參與恐怖活動。澳司法部長喬治·布蘭迪斯曾放下狠話,如果某個澳大利亞人不能給出前往這個地區的合法理由,那么這個人就會被假定去與該地區的恐怖組織一道從事敵對活動。
在政策層面,澳政府分別在2004年、2006年、2010年以及2014年發布了有關反恐和國家安全的戰略報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報告強化反恐和安全政策的同時,也在強化國家強力機構的權力。有數據顯示,2001年至2011年,澳國防和安全支出增長59%,但澳安全與情報局、澳聯邦警察局、澳秘密情報局的預算分別增長了655%、161%和236%。去年10月通過的《國家安全法修正案》,賦予了澳情報部門更大的權力,比如不經司法程序羈押、更大范圍的監控等。同月,澳聯邦政府還額外撥款6.3億澳元給情報部門,應對本土恐怖主義以及回國的澳籍伊斯蘭武裝分子。
在國際反恐領域,澳大利亞是西方國家中美國少有的鐵桿兒盟友。阿博特政府是首個表態派軍參與美國領導的打擊“伊斯蘭國”軍事行動的西方國家政府。澳大利亞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堅定支持者,也是北約國家外在阿富汗駐軍最多的國家。澳大利亞反恐形勢演變的原因錯綜復雜,但外交政策無疑也是一個誘因。澳大利亞前工黨領袖馬克·萊瑟姆最近撰文,呼吁阿博特政府重新評估介入中東的政策。他寫道:2014年初通過承諾介入中東又一場徒勞無益的軍事行動,阿博特政府增加了澳大利亞出現像莫尼斯這樣造成公共威脅人物的可能性。“作為一個僅有有限軍事能力的中等國家,澳大利亞沒有必要卷入中東宗教沖突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