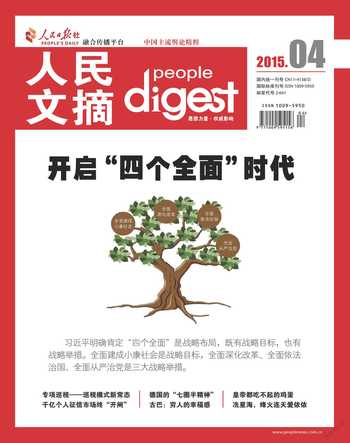南水北調34.5萬移民背影
呂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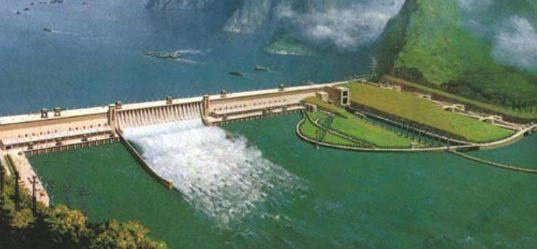

2009年10月25日,隨著汽笛的一聲長鳴,駁船緩離水岸。艾兆春一步跨上駁船高處,連連揮手:“回去吧,回去吧……等安頓好了,接你們下去看看。”船漸行漸遠,艾兆春兩眼噙淚依然不停揮手。
艾兆春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34.5萬移民中的一員。長江最大支流漢江上的丹江口庫區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源地,為了確保工程供水,丹江口大壩壩頂將由原來的162米增加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抬高至170米,風浪線172米,水庫面積由745平方公里增加到1050平方公里。這意味著移民們的家園將葬身水底,他們將別無選擇地惜別故土,踏上異鄉。
移民工程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重要部分,涉及河南、湖北兩省,共34.5萬人,其中約23萬人需要外遷。河南省淅川一個縣需移民16萬余人,湖北省丹江口市、鄖縣、鄖西縣、張灣區、武當山特區5個縣需移民近18萬人。
隨著南水北調工程的進展,湖北、河南兩省開始了有條不紊的庫區移民和干線征遷工作。
兩次離鄉
58歲的葉明成經歷了建國初因修建丹江口水庫和2009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所涉及的兩次移民。
1959年,均縣(后更名為丹江口市)縣城遷至沙陀營,一座水電城市就此興起。均縣縣城周圍的農民被移民安置在襄陽、隨州等地。
14歲那年,葉明成被安置到隨州安居鎮肖店公社。那時的他還不理解父母為何一直掉眼淚。不遠的均州古城一天天被淹沒,在水漲到家門外十幾米時,他和父母鄰居一起上了船。先坐船,再坐火車,輾轉三四天,一家人終于來到隨州。
搬遷到外地的移民面臨著完全陌生的環境,很久無法適應。他沒有像父母一樣天天念叨著想回去,但他也很快意識到,移民身份會使他失去很多機會,比如升學、當兵,甚至招 工。
1979年,他和均縣鎮關門巖村的一個姑娘結婚,把家和戶口從隨州遷回了均縣鎮。后來,他買了條小木船,過上了靠打魚為生的生活。
上世紀80年代前后,移民政策放寬,葉明成的父母也回到 了均縣鎮,一開始沒有住處,只好在水庫邊用芝麻秸搭了座棚子。1984年,葉明成請全生產隊的人吃了頓飯,終于將父母的戶口落入了關門巖村,他們再次成為故鄉的人。第二年,父親去世,老人在臨終前告訴葉明成,死在家鄉,他也沒什么好遺憾的了。
隨著漁民的增多,葉明成開始嘗試網箱養魚。經過二十多年,他已擁有40個網箱,加上十幾畝柑橘園,一年收入可達20萬元。再后來,家中的養魚網箱已有100多個,村里的人都稱他“養魚大王”。
可是,為了南水北調,他再次成為移民。為了確保水庫的水質,家中的100多個養魚網箱也被取締,他提前上岸“退休”。
“這輩子都圍著南水北調轉,終于等到丹江口水庫的清水流進北京。為了調水都不容易,希望北方的人們珍惜用水!”得知漢江水正式進入北京的消息后,老移民葉明成感慨道。
難度最大的移民
南水北調移民工程是繼三峽工程之后,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水庫移民“大遷徙”。
1992年淹沒區實行“禁建令”,原則上停止一切建設,村民生活困難。原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副主任蔣旭光在調研中發現,有些移民群眾房屋破舊,家里沒有像樣的家具物品,交通、環境、衛生、飲水等生活條件都很差。
2009年兩會期間,時任河南省省委書記徐光春、省長郭庚茂“參謀”出了一個思路,針對丹江口庫區移民強力要求盡快搬遷的呼聲和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提出的中線工程2014年實現通水的目標,河南省打算“四年任務,兩年完成”。和“四年任務,兩年完成”相對應,湖北省提出“移民工作四年任務兩年基本完成,三年徹底掃尾”的總體安排。
河南、湖北兩省均已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目標。
丹江口庫區在三年時間里搬遷安置超過30萬人,而且多是跨縣市安置,這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罕見的。
世界著名移民專家、世界銀行原社會政策與社會學高級顧問邁克爾·塞尼評價:“南水北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丹江口庫區移民是一項偉大的工程。”
搬遷工作雖已完成,但在搬遷過程中依然遭遇了各種難題。
為移民提供物質上的資助是必要的。但在眾多人的眼里,不僅要關注移民的物質需求,更要關注人的發展需求和精神等非物質需求,盡量滿足移民的合理要求,移民才能“穩得住”。
在移民搬遷中,對涉及的一處回民村,充分考慮民族習俗,并專門為回民建設了一座清真寺,搬遷時,一些特殊群體都有專車接送。“通過情感關懷和親情操作來補充物質補償的不足。”
南水北調工程的移民采取了相對集中安置的政策,繼續沿用原來的村名,保留原來的基層組織架構,在新村建造一些懷舊的紀念物。蔣旭光說:這種相對集中的安置,為移民適應新環境提供了緩沖的時間,便于溝通和互相照顧。同時,每個家庭都配有聯系人,幫助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實行責任制,三年不撤,以此保證群眾向政府反映訴求的渠道透明、暢通。
搬遷到陌生的環境里,孩子上學又是一大難題。為此,河南省在每個移民新村都建起一所小學,保證11歲以下的孩子就近在村內上學,12歲以上的再出村。湖北在192個外遷安置點都考慮了配建學校,或擴建當地學校。
南水北調工程移民的另一個重要創新是將移民新村建設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將被征遷群眾生產生活安置與當地社會經濟建設相結合,多渠道安排資金,協調地方在供水、供電、交通、通信、醫療、教育等方面出臺扶持政策。國家相關庫區移民政策、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和新農村建設資金,優先傾斜庫區移民,讓移民新村實現一次規劃、一步到位。
在新鄭市多個移民新村,家家戶戶都是白色的二層小樓,村里健身廣場、圖書室等公共設施一應俱全。來自淅川的村民肖靜飛說,自己從沒想過能住上這樣的房子。
在政策的支持下,安置區的很多村子都因地制宜找到了合適的發展模式。和村里很多家庭一樣,肖靜飛把分到的5畝多地承包給了一家農業公司搞生態園,每年有4000余元的承包費收益,自己還受雇于這家公司,每月有上千元收入,丈夫則繼續在老家淅川打工。
移民工作是個大難題。搬遷難,穩定更難。移民真正融入新的環境還需一個很長的過程,搬得出只是第一步,穩得住、能發展、可致富,任重道遠,需要作出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