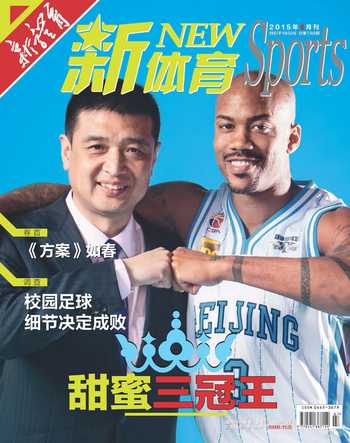孩子要踢球,聽聽家長怎么說
張曉辰 柏強
讓孩子踢球,是為鍛煉身體、培養興趣,還是為日后成為職業球員?不同的家長有不同的考慮。記者走訪了北京市幾所學校,隨機采訪了幾位家長。
張松先生今年41歲,原是八一隊射擊運動員,妻子曾是專業排球運動員,2006年11月有了兒子。兒子7歲時開始接觸足球。“我喜歡看球,也喜歡踢,帶著孩子一起玩主要是讓他喜歡,感興趣”,張先生說。兒子3歲的時候曾測過骨齡,以后能長到1.96米。很多教練說,這孩子身材不錯,跑跳靈活性也不錯,是塊搞體育的料。
由于夫妻倆都有專業體育背景,孩子先天條件也不錯,加之足球作為世界第一運動倍受歡迎,張先生對孩子有所期待:“我是誠心想讓孩子學足球,不像有的家長那樣是為了以后升學走捷徑,所以我給孩子做了認真規劃。”

張先生通過觀察,發現北京市東城體校足球教練動作規范,就經朋友介紹,讓孩子來這里先跟著練。孩子不足10歲,還入不了隊。至今已來這里一年了,“一是培養他的興趣,二是觀察他到底是不是這塊料。如果五六年級時還練不成場上一個位置,就轉別的,比如去學守門,畢竟現在我的孩子身高1.4米左右了。”
談起對兒子未來的規劃,張先生滔滔不絕:“如果孩子硬件條件足夠好,我們想在他12歲以后把他送到國外去學球。我分析過,世界足球的五大聯賽,德國首屈一指,加上德國人作風認真嚴謹,這是我們的最佳選擇。意大利是其次的選擇。如果學出來了,哪怕在比利時、瑞典等國的一二級聯賽上踢上個主力,也算沒白費功夫。如果十七八歲還學不出來,至少語言水平和文化見識提高了,身體也練好了,可以在國外找機會學習或工作,至少生存不會有大問題。”
與張先生不同,另一位家長楊珂女士主張踢球以快樂為主,并沒有望子成龍。楊女士的兒子與張先生的孩子一樣大,在中關村第一小學讀二年級,也十分喜歡踢足球。中關村一小每周一、二、四下午三節課,周二、五兩節,學校在這兩節課后設有足球課,可以按興趣參加。
與中關村一小類似,北京市皇城根小學也開設了課后足球興趣班,相對更專業。據任課教師屈俠介紹,課程內容主要為普及足球知識,講足球規則,進行傳球、接球、停球、腳內側推球、擲界外球、射門等基本動作練習,最后半小時分組比賽。
屈俠說:“我們校長喜歡足球,也支持足球興趣班,從孩子的服裝到球門都由學校添置。學校原來沒有場地,現在新校址有一座跑道不到200米的運動場,內設一塊塑膠五人制足球場。”皇城根小學從今年開始將足球列入校運會項目,先從射門比賽開始。
不過,足球興趣班的孩子一周能來上一次課的居多,兩次以上的很少。這是因為家長為每個孩子報了不少其他興趣班或課外班,孩子上不過來。即使同是踢足球,一些有想法的家長還在北師大等地報了更專業的課外班,帶著孩子去趕場。
楊女士就是這樣趕場的家長之一。她的兒子非常喜歡踢球,學校的足球課節節不落。出于興趣的考慮,她給孩子報了足球俱樂部,每周日上午兩個小時,陪孩子到奧體中心足球場練球,“雖然學校有場地,也很重視,但老師很一般,不怎么教孩子技術,就讓孩子分組踢比賽”。
“我們之所以來這兒,就是看中師資。這里的足球老師多有職業足球背景,有的是北京國安退役隊員或教練,有的是高校足球畢業生,大部分都持有中國足協D級或C級教練員證書,據說在青少年足球教學上經驗豐富,金志揚還是顧問。孩子來這兒能真正學到東西。”
在綠茵場邊,楊女士一邊看著兒子在場上奔跑,一邊跟記者說了她的想法:“我們讓孩子踢球,一來是尊重孩子的喜好,二來足球是一項很好的運動,教育講全面發展,身體是第一位的,踢球能強身健體,現在的小孩體質比我們小時候差太多,多踢球能讓他強壯些。”
楊女士在環境保護部工作,對于學校教育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覺得現在學校的教育太過死板,缺少直觀感受。比如說物理上講的拋物線,數學上講的角度,不用在課堂上說太多,讓孩子在戶外踢場球,一下就能明白。小學生的認知需要直觀感受,這也是讓孩子踢球的一大原因。更多的是出于孩子的興趣,并沒有想著以后讓他以此為飯碗,畢竟尊重孩子的個性最重要。”

然而,不少家長對孩子踢球有所顧慮,擔心影響學習成績,擔心踢球中發生安全事故,擔心孩子的道德品質會受球場不良風氣影響。許多小學甚至在課間十分鐘規定除了上廁所,不讓孩子出教室,更別說課后踢球。校方也是出于安全和學習成績的考慮。
楊女士對此不以為然:“踢足球當然不會影響學習,相反還是一種促進。足球不光能強身健體,在團隊中還能對孩子的心理有所塑造。踢球能讓人的身體、心理和文化形成互動,是一種性格的磨礪。”
現在的孩子如溫室里的花朵,在學校、家長和社會的過度保護之下,受不得一點挫折。楊女士朋友的孩子就讀于北師大附小,因為跳繩比賽中繩子甩到一個孩子的臉上,留了道疤,家長就找到學校。學校為保證意外傷害事故為零,自此之后不再讓孩子參加戶外活動。
楊女士覺得有些家長對安全問題過慮了,“小孩應該多到戶外玩,他們一天到晚都坐在那兒低著頭寫作業,太不利于成長了。我們這么大的時候,都天天在外面跑來跑去,磕了碰了都是正常的”。
踢球有風險,家長擔心是人之常情,但家長過慮會導致孩子參加不了足球運動。為了打消家長的顧慮,北京市皇城根小學采取了兩項措施。“最重要的是嚴防死守,保證孩子不出事。比如分組比賽時,三名任課老師全部上場,分別在前場、中場、后場,與孩子們一起踢球,邊踢邊指導,讓學生不扎堆,減少安全隱患”,屈俠老師說。另一方面,訓練公開化,組織低年級孩子的家長現場觀摩,為的是讓家長放心。“到現在,我們沒有出過大事,至多是兩個孩子絆到一起,摔倒了”。
北京博凱智能全納幼兒園是全市最早開設幼兒足球課的幼兒園,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避免安全事故的發生。據教學園長馬益文介紹,首先會給每個孩子發一條發帶,戴在頭上,磕碰時能起到緩沖作用。幼兒園的草皮較為柔軟,甚至在足球場四周的墻上也貼上了一米多高的草皮,能起到保護作用。最關鍵的是老師的責任心,每次足球課,除了一名足球老師外,會有保育員協助任課老師,負責照看孩子的安全。

張先生鼓勵兒子要硬氣,他認為踢球能讓男孩更像男子漢,“足球是集體項目,現在家中都是一個孩子,獨慣了,踢球就得融入集體,就得與人交流溝通,應對好各種關系。不可否認,踢球時大孩子欺負小孩子很常見,但這不是壞事,孩子在這種情況下就得學會面對和處理。踢足球不光要靠身體素質,還要靠智慧和對足球的理解”。
王飛的孩子今年6歲,每周末也會來到奧體中心足球場。王飛是北京女足的退役隊員,現在的身份是教練。孩子4歲的時候,她就開始教幼兒和小學生踢球,自己的孩子也在隊中。對于足球進校園這件事,既是教練又是家長的她有些矛盾。
作為教練,她很不樂觀,認為開展起來有很多的問題,學校難有更多像她一樣專業的老師,即便有,也難以施教。“獨生子女對家長來說都是寶,老師說不得、訓不得,有動作做錯的或調皮搗蛋的孩子,老師不好管理,不像我踢球那會兒,教練說一不二,擁有很高的自由度和自主權。有時候自己的孩子不認真學動作或者偷懶,我也很生氣”。
作為家長,她又非常支持孩子多踢球,“現在的孩子整天坐在教室看書寫作業,課業壓力那么大,太需要到綠草青天的環境里踢踢球了。玩是小孩的天性,踢球能減少壓力,快樂成長。我每周末都會帶他上我的課,平時也抽出很多時間陪他踢球”。
為滿足孩子的足球興趣,家長可謂煞費苦心,不惜時間、財力、精力。楊女士說周末足球班的費用確實有些高,“一年5800元,是筆不小的開支。但是孩子喜歡踢球,作為家長,我們也舍得花錢”。
張先生說費用和安全對他不是大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時間和精力。為了讓孩子堅持踢球,不惜全家總動員。孩子的學球時間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點到5點半,周六上午半天。學校離體校球場有一段距離,張先生說:“我和愛人每天要輪流開車去學校接剛下課的孩子,再送他火速去球場。我要求孩子用10分鐘的時間在車上換好衣服,然后提著一瓶礦泉水3點10分到場訓練,晚上6點多到家。就這么一個孩子,現在的生活學習和訓練要搭上兩邊4個老人和我們夫婦倆,總共6個人的精力付出。”
小學低年級不應留家庭作業,但孩子現在每天仍有作業。升入五六年級時,作業會多起來,勢必與訓練時間有沖突。孩子在足球方面成才需要十幾年的努力,全家的各種付出可想而知。
和楊女士不同,張先生認為,孩子練球影響學習是難以避免的,“你看這些體校孩子的學習,就那么回事”。上學期為了去廣西冬訓,體校孩子的期末考試去年11月中旬就進行了,而普通學校的孩子是今年1月。張先生不免有些擔憂:“孩子如果練不出來,學習也耽誤了,到高年級時能否轉回來?”
家長能不能支持孩子踢球,不光是從孩子天賦、家庭財力、時間精力等方面考慮,社會環境和足球氛圍也是影響家長做出決策的重要因素。
高遠的父母和楊女士、張先生有著類似的考慮。高遠目前26歲,七八歲時開始接觸足球,談及父母的初衷,他說:“那時國內職業聯賽剛開始,中國隊正沖擊世界杯,足球的環境氛圍好,家長喜歡,我也喜歡,于是就讓我學踢足球。倒不是為了踢職業,一方面有當時足球熱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為上大學創造條件。”

高遠曾是人大附中三高足球俱樂部的隊員,畢業后考入北京體育大學足球專業,大三轉入體育傳媒系公關班,畢業后曾在新浪體育做足球編輯。人大附中三高創辦20年來,王安治、王曉龍等70名學生成為職業球員,在足球人才培養模式上獨樹一幟。
高遠小時速度快,踢邊路,個子長高后,改打中后衛。小學六年級時,他到人大附小訓練,一年后升入人大附中。他說,“入學時既要看足球水平,也要看學習成績,同被選進附中的有七八個同學。我們學習、住宿、訓練在一個基地,沒比賽時,周末才能回家。每天下午第二節課后開始訓練,晚自習到9點。高中畢業時,我們隊20多人中,有兩三個進了專業隊,其余人都上了大學,當然是以特長生的身份。”
他坦言自己身體素質不錯,可以走職業球員道路,但練到十四五歲時,家里在猶豫。“我個子長得晚,高一時還不到1米70,比賽機會也少,搞不清是否有發展前途。后來足球環境不好,國內聯賽也處于低潮,足球不被看好,前景不明。盡管我本來有機會進入國安梯隊,后來的身高達到1米85,但最終家長還是選擇讓我走上大學的道路。”
高遠說他也想過搞職業,但不太堅定,畢竟走職業足球這條路有一定的風險,“我們承受不了那種代價,最終還是同意家長的穩妥選擇”。在他考大學時,足球的熱度大不如前。原來像他一樣的特長生都被保送到人大、北理工等高校。但到他這一屆時,只能各人選校報考,被人挑選。
高遠切身體會到:足球發展得好壞,與整體環境和氛圍有很大關系,“父親和我最初選擇學踢球,最終放棄,都與此相關。從這個角度上說,現在國家提倡從學校開始抓足球教育,是件好事。只是這件事和這種氛圍要能持久,要務實。”
姚明在今年“兩會”上的提案主張專項體育課進校園,這項提案是在“姚之隊”走訪了上海市三家學校后生成的。楊女士說她非常贊同姚明的呼吁:“因為學校開設的體育課大多是擺設,好的老師還教一些田徑動作,不好的老師就讓孩子自由活動了。教跑步跳遠,孩子不喜歡,因為太枯燥。足球對孩子來說很有意思,多數孩子也喜歡玩,可是學校不怎么教。所以足球進校園,學校開設專項體育課是好事。”
據了解,北京市將在2016年把足球作為體育選考項目納入中考,各方對此意見不一。

楊女士認為,足球跟考試掛鉤太沒必要了,“急功近利是很不好的社會風氣。什么科目一說要考試,應試化,就會讓孩子產生厭煩”。
屈俠在北京市皇城根小學任教4年。他剛來當老師的時候,就有教育部和國家體育總局《關于開展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活動的通知》。他認為,中國不是足球強國,基礎薄弱,但大家喜歡,現在提倡從學校開始普及,無疑是件好事。但應當看到這不是一呼就能起的事情,有很長的路,而且要走得扎實。
屈俠說:“德國在世界杯賽奪得冠軍前,有多年的規劃,經歷了臥薪嘗膽。人家足球強國尚且如此,更何況我們。”
足球進校園,尤其是小學,除了頂層設計,“我覺得首先要普及的是足球理念和認知,至少讓學生知道足球是什么。現在不少家長和孩子簡單地認為足球就是踢著玩的,活動一下身體而已,重視程度當然不夠。孩子的問題主要源自家長,畢竟大多數孩子現在的學習還是被動的,興趣的選擇也是被動的。因而,足球教育不能只是孩子的事”,屈俠說。
按中國的國情,如果希望家長重視,最有效的方法是將足球教育列入教學大綱,成為正式課程內容。應試當然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甚至會成為家長和學生的一種負擔,反感應試的內容。屈俠認為,還是要從興趣和觀念上改變人們,特別是家長的認識,足球可以作為考試的選擇項目之一。這種方式還是有效的,盡管開始階段會有一定的困難。
不過,大多數網民對于足球納入考試都持反對意見。虎撲體育足球論壇上的投票調查顯示,共有229人參與投票,只有40票贊成,其余都投了反對,占82%。網民普遍認為足球納入考試容易功利化、應試化,有違體育的初衷。國家之所以重視發展校園足球,主要目的在于發揮足球的育人功能,促進學生文化學習和足球技能的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