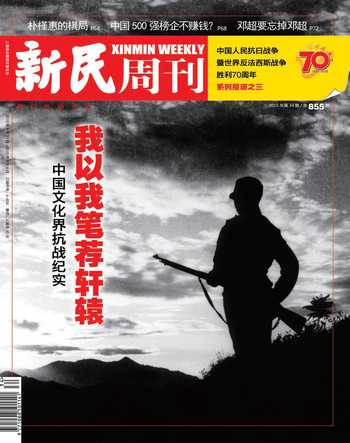丁申陽的“書法傳奇”
張立行
上海東方電影頻道近日舉行年度頒獎活動。現場眾星匯聚,星光燦爛。但是,當主持人在臺上徐徐展示丁申陽草書作品時,引來了比之前任何一位巨星出場都熱烈得多的掌聲甚至歡呼的尖叫聲。
對于電影界來說,丁申陽并非圈外人,他原本就是上海電影集團知名高級美術師,曾在一系列名聞遐邇的影視劇中出任美術師,而書法則是他的“業余愛好”。哪承想,如今在江湖上,丁申陽書法家的名聲早就蓋過了他電影美術師的名頭。
我與丁申陽交往近二十年,其為人行事的風格始終未變,誠懇,低調,散淡。在他的人生詞典中,誠懇待人永遠放在第一位,書法不過被他視作修身養性的“小技而已”。在文人相輕、名利熏心、派系林立的書法圈,他更是少有的沒有爭議受到各方稱譽的藝術家。
我初識丁申陽時,他才三十歲左右。在丁申陽平靜的外表下,人們忽略了他骨子里豪放縱逸、汪洋恣肆、騷動不已的氣質。丁申陽有俠氣,不管是過去做上海青年書法家協會的秘書長,還是現在擔任上海書協副主席分管草書委員會,他都勇于擔當,樂于犧牲個人利益,從不拘泥于一時一事一人一物,而是放眼長遠,抓“大”放“小”,得“意”忘“形”,非常人所能及。因此,他的草書,有法度而無約束,或在靜穆中求飛動,或在飛動中求頓挫,或從常態中超然逸出,縱肆狂舞;或于斷處缺處,追求一脈生命的清流。總之,靜處就是動處,動處即起靜思,動靜變化,含道飛舞,大巧若拙,以達到最暢然的生命呈現,在空白的世界中舞出有意味的線條來。
丁申陽的書法在同輩人中是出類拔萃的,有扎實的基本功,對書法藝術的傳統始終懷有敬畏之心。細品他的書法,可以清晰看出傳統的脈絡。有不少書家,筆墨線條有特色,但短于結構(結體);或書法的結構差強人意,可筆墨線條蒼白無味。丁申陽的書法難得在結構和線條兩方面都比較均衡。書法諸體之中,草書的書寫更講究靈性,光有技巧并不解決問題。不管是書法的結構還是線條,都只是外在表現形式,背后體現出的是書寫者書法之外的“軟實力”:格局、氣息、學養、閱歷、悟性。有些書家讀了幾本書,會謅幾句舊體詩詞,就到處顯擺,唯恐他人不知。丁申陽為人散淡、低調,平時說的是家常話,談的是身邊事,不做作,不擺譜,不故作深奧。但他的中國傳統文化學養,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傳統書畫的理解,要超過許多“二把刀”式的所謂的書畫家和學人。他遍覽歷代碑帖法書,取宏用精;又喜中國古典文學,無數名篇佳詩爛熟于胸。因此,丁申陽書法的筆墨線條是有內容有內涵有意味的。中國人民大學陳傳席教授認為書法的最高境界是散和淡。散是散懷抱,淡是自然自如。這是以藝術家的為人和學養作為基礎的。我覺得拿來評價丁申陽其人其藝真是恰如其分。 丁申陽出了不少書法作品集,但我最喜歡的是那本薄薄的近作《丁申陽草書蘇軾詞卷》。《丁申陽草書蘇軾詞卷》以長卷的方式展示了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和《念奴嬌·赤壁懷古》兩首詞。蘇軾的這兩首豪放詞是丁申陽的情之所鐘,原本就具有歌唱性,而詞句里情緒的起落、節奏的快慢、旋律的高低,都經由丁申陽枯淡、疏密、錯落的筆墨得到準確、傳神的體現。以《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為例,開首“明月幾時有”幾個字,似撥弦三兩聲,筆勢較緩,輕輕起調;“把酒問青天”之后漸行漸快,筆走龍蛇,汪洋恣肆,一瀉千里。及至“高處不勝寒”處,筆頭突然凝滯,幾枚枯點止住了原先明快的升調,沉郁頓挫。全篇一氣呵成,變化多端,似拙實巧,精彩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