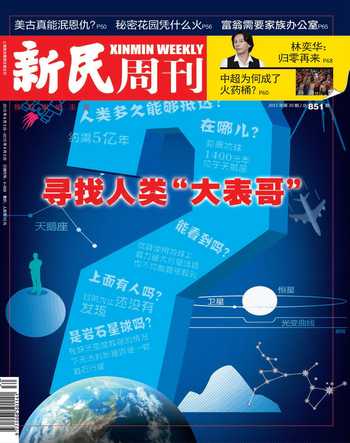“另一個地球”改變了什么?
孫正凡
在前沿科學技術領域,科學研究和科學幻想之間的界限正在越來越模糊。也許再過幾代人,我們真的就會實現《星際迷航》那樣的劇情,我們的某一代子孫將成為宇宙人類。
2014年7月24日,美國航空航天局宣布“開普勒太空望遠鏡”發現一顆距離地球1400光年的類地行星“開普勒452b”,它與地球的相似指數達到了0.98。1400光年對于當前的航天技術來說是遙不可及的,那么為何人類仍花大價錢試圖去尋找這些只能看不能摸的目標?
科學發現改變三觀

開普勒太空望遠鏡這個名字是紀念偉大的天文學家約翰內斯·開普勒,他在17世紀初發現了行星運動三定律,從而證明并發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說”,確定了我們的地球僅僅是太陽系里的一顆普通的行星。幾十年后,牛頓以行星運動三定律為基礎,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解釋決定宇宙運行的基本規律。開普勒的影響不僅僅是在科學領域,也極大地改變了人類思考世界的方式。
在“日心說”被證明以前,在地心說系統里,人們一般認為地球(以及人類)有極其特殊的地位,甚至認為地球和日月五星就構成了整個宇宙,至于恒星,那不過是包裹在“宇宙”外圍的一層球殼。這類想法后來被稱之為“單世界”理論。實際上這個想法又與自古以來人類信奉的宗教和神話觀念有關。在神話時代,這個世界是由神靈創造的(所以并不大),而且特意為人類而創造的。可以說所有的古代宗教和神話,在解釋世界為何如此的回答中,都是以人類為中心,以大地為中心,不管多么厲害的神靈或妖魔鬼怪,都是圍繞著人類的生活為中心。當然,這些時代的科學水平還很低下,不足以抵消這些神話,而神話本身也給人類提供了對“安全感”的需求。
科學革命時代以來,隨著知識的增長和積累,隨著人們逐漸掌握了關于世界運行的科學規律,科學就像一支照亮黑暗的蠟燭,使人類逐漸擺脫了過去對神靈和魔鬼的恐懼,迷信退隱,理性顯現。哥白尼的“日心說”的提出,尤其是開普勒等天文學家的發展,使人們發現了地球在太陽系里的真實地位。17世紀已經有哲學家提出,我們太陽系在這個世界并不是唯一的,每顆恒星都是一個類似太陽系的世界,這就是“多世界理論”。也就是說,早在人類有能力去尋找系外行星之前,早就孕育了不斷向外求索的動力。
1950年代開始的太空時代,帶來的不僅僅是科學技術的飛躍和全新的宇宙觀,也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利益。美國通過阿波羅載人登月工程和太空探索的巨大成就,樹立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科技強國形象,而且通過美國航空航天局與社會企業的協作,推動了一大批科技創新,并且獲得了豐厚的經濟回報。
從“我”出發,理解宇宙

迄今為止,地球仍然是我們所認識到的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球,是我們在茫茫太空中生存繁衍的唯一基地。當我們尋找宇宙中可能供生命存在的系外行星時,也是以人類自身生存為標準的。
包括開普勒太空望遠鏡在內,搜尋系外行星的探索中,最令人感興趣的還是處在“宜居帶”內的類地行星。所謂宜居帶,就按照我們地球的樣板,離其所屬恒星不太近也不太遠,溫度適中,允許液態水存在,從而適宜生命(與地球碳基生命類似)存在的區域。就太陽系來說,宜居帶的范圍基本上是從金星軌道到火星軌道。
當然對于恒星也有要求,它應該是一顆像我們太陽這樣單獨存在的恒星,質量也應該與太陽相差不太多。因為這樣的恒星演化時間足夠長(壽命以十億、百億年計),有足夠的時間允許行星形成,更能滿足生命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的演化過程。類地行星更不用說,海洋是生命的搖籃,陸地是生命壯大并得以自由發展的舞臺;具有類似特征的木衛二、土衛六也成為當前航天探索的熱點對象。當然也有科幻作家,包括像霍金等科學家設想在氣態行星中可能也存在某種形式的生命,但在沒有生物學證據之前,這些還只是幻想。
1980年,行星天文學家卡爾·薩根在參與“伽利略號”項目時,實施了一次“從外太空系統觀測地球”的實驗。“伽利略號”是前往木星的探測器,為了借助引力彈弓效應加速,它會再次飛過地球。當時它離地面只有約1000千米,薩根等天文學家發出指令,調用了“伽利略號”上的儀器瞄準了地球。通過獲取的光譜等資料分析,他們能夠推斷出大氣、水、云、海洋、冰川,以及生命跡象。
當然太陽系外行星的距離比這個只有區區1000千米的距離要遠得多,以目前的觀測技術,還拿不到像“觀測地球”這樣詳細的資料。比如“開普勒太空望遠鏡”觀測到的還只是行星經過母星之前造成的光變,無法獲取行星光譜。下一代搜尋系外行星的望遠鏡,如美國航空航天局和歐洲航天局分別計劃在2020年前后發射的“類地行星搜索者”和“達爾文探測器”,將能夠嘗試分析類地行星的大氣光譜,觀察是否存在氧氣、水汽等能夠支撐生命的物質。也許發現“外星生命”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呢。
為萬世而未雨綢繆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憂患意識是人類從弱小到強大,文明得以壯大的關鍵因素。人類起源于200萬年之前的非洲草原,從采集、游牧進入定居生活才不過1萬年時間。無論從史前時代與野獸搏斗,還是部落、國家之間的殘酷競爭,使人類天生富有憂患意識。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人類的文明史并不長,有詳細的歷史記錄的時間就更短了,也就是說,我們對于長時間的歷史演變是缺乏經驗的,在古人的想象中,也只有通曉天地造化的奇人才能夠“前知一千,后知五百”,我們既往的經驗都是基于幾十年,至多幾百上千年的歷史。天文、地理、生物等科學研究告訴我們,人類、地球和宇宙都存在特征尺度為幾十萬年到上億年的巨大變化。為了人類的集體福祉,必須有人提前考慮萬世之利。
19世紀以來,天文學家對小行星、彗星的研究更表明,地球所處的環境不是絕對安全的。6500萬年前統治地球的恐龍可能是由于一顆直徑10千米的小行星撞擊地球而絕滅,而這樣的小行星在地球軌道附近所在多有。
在遙遠的未來,作為地球光和熱來源的太陽也會成為地球的威脅。近年來太陽物理學研究發現,在數十億年間,太陽將變得比現在大10%,地球上的海洋將被炙熱的太陽蒸發干,生命無法生存。當然我們利用某些手段推動地球向外遷移到新的“宜居帶”位置,但這只是暫緩之計(且不論其成功率如何),當太陽最終死亡時,地球也仍將落入黑暗之中。
近年來哈勃太空望遠鏡已經發現在一些白矮星(這也是太陽的最終命運)周圍發現了可能是類地行星的殘骸,這讓天文學家聯想到了我們地球的未來。從現在起大約55億年內,太陽將在燒盡它核內的氫燃料,開始燃燒外層的氫。在轉變成紅巨星的過程中,太陽內核將收縮,外層迅速膨脹。60億年后,膨脹的紅巨星太陽體積將擴大到現在的256倍,將吞噬地球軌道,把地球燒焦甚至使之灰飛煙滅。無論如何,地球生命(屆時如果還有的話)將難逃劫難。
不過這項研究帶來的好消息是,我們還有大約10億年時間來為地球這次最終的世界末日做準備。拯救地球居民的一種方法是,離開地球前往其他恒星系。不過正如開普勒452b離我們足足有1400光年遠,可以想見未來即使發現“宜居地球”,它的距離也是我們到達那里的巨大障礙,這就需要全新的航天科技才能帶我們到達那里。幸好這一點科學家們也已經想到了。
2012年,美國航空航天局的科學家哈羅德·懷特宣布開始進行“曲率驅動”超光速飛行的實驗。曲率驅動這個詞由于經典的科幻電影《星際迷航》而變得流行,但長期以來只是科學家提出的一種數學模型,難以找到實現它的方法。哈羅德·懷特的想法是,先利用一束強激光來觸發時空在微觀尺度上的扭曲,實現極微小的時空擾動,為進一步的真正的“曲率驅動”實驗鋪路,他們已經在約翰遜空間飛行中心建立了一套被稱作“懷特-朱迪曲率場干涉儀”的裝置。這樣的設想如果最終可以獲得成功,那么未來的宇宙飛船理論上便可以實現在扭曲時空里以10倍光速飛行,而不會打破宇宙對“光速最大”極限的限制。
這些想法雖然看起來匪夷所思、遙不可及,但實際上,近幾百年來,科學技術正呈現跳躍式變化的特征,新的科學技術既是在既往的科學技術基礎之上產生的,又有許多難以置信的突發性創新。這些創新往往是連最頂尖的科學家也難以事先預料的。美國航空航天局推出的關于曲率驅動的研究,無獨有偶,中國航天集團的工程師們也找到了科幻小說《三體》的作者劉慈欣,討論未來可能的航天技術。在前沿科學技術領域,科學研究和科學幻想之間的界限正在越來越模糊。也許再過幾代人,我們真的就會實現《星際迷航》那樣的劇情,我們的某一代子孫將成為宇宙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