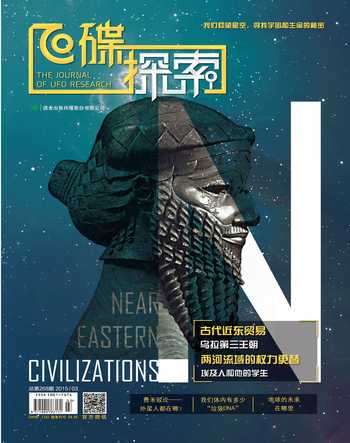人類壽命,真由微生物決定?
田野




與其他動物比起來,人類的年齡結構實屬罕見:幼兒依賴父母的時間之長在自然界中異乎尋常,而年長者在喪失生育能力以后還要生活很多年,這在自然界中也不多見。
那些寄居于人體的小小住客——統稱為微生物,是否在塑造和保持人類這種非同尋常的特性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最早提出這一命題的是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的醫學和微生物學教授馬丁·布雷澤,他得到了來自范登堡大學的生物數學家格萊恩·韋伯的支持,后者用數學模型對該命題進行了證實。兩人聯合發表了一篇名為《寄主死亡是人體內微生物積極作用的結果》的文章,該文早些時候在線發表在美國的《微生物學》雜志上。
科研人員已知,每個物種,無論植物還是動物,都是某種特定微生物群落的寄主。人體內大約有1 0 0萬億個微生物細胞,數量是人體細胞的1 0倍。一直以來,科研人員都認為微生物群落對寄主的影響非常有限,但是,最近的研究發現,微生物對人體的作用遠不止幫助消化和產生氣味,它們還有助于大腦發育、機體生長和預防感染。這項新的研究為完全基因組進化理論提供了有力支撐,認為達爾文自然選擇的對象并非只有單個機體,同時還包括機體內的微生物群落。布雷澤在幽門螺桿菌實驗發現了微生物對人類年齡結構的影響——幽門螺桿菌是一種細菌,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胃里都有這種細菌。
幽門螺桿菌是一種存活于人的胃液中的有益細菌,在人的大半生里與寄主和平相處、共榮共生。1 9 9 6年,布雷澤發現幽門螺桿菌可以調節胃酸水平。但是,幽門螺桿菌也是導致胃癌的常見病因,年齡越大,患胃癌的概率越高。
布雷澤認為,一個真正的共生體就是這樣一種有機體,在你年輕時能讓你保持活力,年老時又可以讓你因此喪命。這對個體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有利于整個族群。
韋伯的專長就是用非線性微分方程來描述動態的生物過程。因此,微生物學家向韋伯求助,看他能否用數學模型對這一想法進行證實。
他們一致同意采取的方法是,建立一個早期狩獵部落人口模型,來觀察微生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為沒有太多資料可供研究,我們無法了解幾千代以前的人類到底發生了什么。”
韋伯說,“但是微分方程體現的是變化,通過對不同變化進行比較,可以掌握當時的更多情況。”
一個基本假設就是,在1 0萬代人的時間里,人類變化并不是很大,尤其是,人類壽命可以高達1 2 0歲——這幾乎是人類壽命的極限了。在現代社會中,由于衛生條件的改善、重體力勞動的減少、糧食供應的增加和現代醫學的發展(比如抗生素的使用),一些高致死率疾病已被廣泛根除,人類壽命得以延長,但人類的平均壽命還是相對較短。
模型將整個人口劃分為三個年齡組:青少年、育齡人群、衰老人群,通過將生育率和死亡率做不同組合來觀察人口的相應變化。在對生育率和死率做出最充分的估測后,科研人員確定了一個基準線,然后根據特定微生物的分布來調整死亡風險。
在一個版本的實驗模型中, 研究人員加入了志賀氏菌——這是在全球范圍內導致瘧疾的主要致病菌。這種疾病的致死人群僅限于兒童,但死亡率越來越高,從而導致人口銳減。
在另一個版本的實驗模型中,研究人員加入的致死因子是幽門螺桿菌,該病菌的致死率隨寄主年齡的增加而增高。這一次,他們發現衰老人群的比例下降,下降部分人口對糧食與資源的需求轉為青少年所用,從而使青少年人口有所增長。最終結果就是,青壯年人口上升,社會系統穩定性也更大。
模型實驗的結果與布雷澤的觀點一致,即進化有可能使人體微生物環境更適合諸如幽門螺桿菌這類以衰老人群為目標的細菌的生存。細菌為保持人口穩定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終將使其受益,因為如果人口的穩定性崩潰的話,細菌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寄主。研究人員決定將生育率加倍,觀察下一步會發生什么。結果是,出現了一個不穩定的社會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伴隨災難(造成人口大量流失的重大事件)而來的,是一個由繁榮和崩潰組成的災難性循環。
在另一次變動中,科研人員增加了狩獵人群中老年人的比例,他們發現,此舉并未造成人口大幅下滑。
除了證實微生物可能塑造了人類年齡結構這一命題外,韋伯還發現,模型實驗揭示了人口增長的一個基本事實:人類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可以恰到好處地支持人類特殊的年齡結構。
“如果你能溯回到三四萬年前,世界人口總共就只有三四萬,而且分散于非洲、歐洲和亞部分地區。”韋伯說,“那么,我們只是比較幸運?還是我們的祖先足夠強壯,可以應付任何環境變化和自然災害,從而使我們有幸存活下來?根據公式計算的結果,答案是,我們的祖先足夠強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