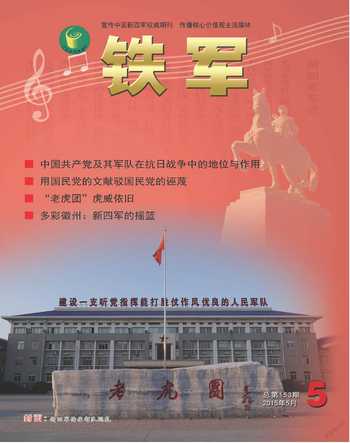懷念我那堅強的老岳父
宋國昌
我岳父是在80虛歲那年,即1997年3月20日傍晚,在與病魔抗爭了兩個多月后,帶著對老伴和兒孫們的深深眷戀撒手塵寰。老人仙逝后,我每每回憶起他那抗日戰爭期間的烽火經歷、面對生活磨難所表現出來的堅強以及對兒孫們的關愛,在無限敬重中由衷地感到欽佩。
岳父名叫徐坤生,1918年8月21日出生在江蘇省宜興縣丁山鎮周墅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里。由于家里窮,他11歲開始給有錢人家喂豬、放牛,17歲后給地主扛長工打短工。抗日戰爭爆發后,岳父的家鄉很快淪陷,日子過得更加艱難。
1944年3月初的一個乍暖還寒的日子,眼看著家里揭不開鍋了,為了謀生岳父就借了點小本錢,在家鄉買些鹽,準備擔到浙江長興一帶去賣,回來時再買些冬筍到家鄉賣,從中掙點苦力錢來養家糊口。但他萬萬沒有料到,途中遭遇鬼子的攔截搶掠,爭奪中還險些丟掉性命。看到鹽被搶走,他怒火中燒,毅然前往長興六都西村,在那里參加了新四軍。
岳父被分配在新四軍十六旅五十二團(7月份改編為四十六團)三營九連當戰士,一參軍就遇上打仗。由于岳父當年已26歲,在家鄉時曾摸過槍打過獵,所以戰斗中不僅作戰勇敢,而且槍法也好,很受首長器重,不久調到營部擔任偵察員、副班長、班長,直至排長。1945年1月3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岳父從1944年3月參加新四軍,到1945年5月一年多時間里,轉戰于江蘇宜興、溧陽、金壇,浙江長興、吳興、臨安、富陽、余杭、武康、天目山,安徽郎溪、廣德等地,參加過20多次戰斗,身上彈痕累累。最慘烈的一次是攻打浙江省臨安縣蟹龍鎮鬼子據點的那次戰斗,激戰中一枚手榴彈在他腹部爆炸,多虧當時因條件艱苦沒能及時換裝而穿著臃腫的棉衣褲,更多虧了腰間扎的皮帶,才使他大難不死,最終成為傷殘軍人。有一塊彈片嵌入肺部無法取出,伴隨了他一生。
全國解放以后岳父第一次回家鄉才聽說,那年他不告而辭參加新四軍后,讓母親在擔驚受怕中遭了不少罪。母親見兒子幾天未歸,怕兒子遭遇不測,愁得吃不下睡不香,她挎著竹籃拄著木棍,獨自一人邁著三寸金蓮,頂風冒雨、餐風宿露,沿途乞討,在江、浙交界的大山里四處尋找。找了十多天沒有結果,一臉憔悴地回到了家,準備養息幾天后再出門尋找。幸運的是,這年4月的一天,岳父所在的部隊在六都村旁邊的廟上與當地群眾舉行聯歡會,恰好岳父同村一位范姓鄰居販豬仔時途經此地,就趕到廟上看熱鬧,無意間看到了岳父在隊伍里忙碌,岳父幾乎在同時也看到了他,兩人目光進行了交流。因岳父家鄉是敵占區,參加新四軍一事若被坐實,會禍及家人。范回到家鄉后,對岳父參加新四軍一事一直守口如瓶。后來看到兩位老人為尋兒子而失魂落魄的模樣,他心中不忍,就私下里對老人說了實情。母親聽說兒子一切安好,這才放下心來。
岳父生前,我曾多次在夏季看到他身上那累累彈痕和猙獰傷疤。因解放后他在政治上受到過挫折,故我平時詢問,他從不愿多談過去的戰斗經歷,只是偶爾酒后興起,才略略透露一些戰斗場景。盡管如此,我仍能窺到他當年在戰場上是如何冒著槍林彈雨沖鋒陷陣的。
老人離休之后原本可以享享清福頤養天年,但操勞一輩子的他一刻也不愿清閑。長年在廚房里忙碌,加之精心琢磨,岳父竟能燒出幾道紅燒肉、排骨、魚、大蝦等上海風味濃郁的好菜,讓孫輩們叫好不絕。
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岳父用左手剁排骨,動作笨拙且費勁,就好奇地問為什么不用右手?岳父微笑一下,輕描淡寫地說:右臂受槍傷,廢了,使不上力。我一聽,心驟然抽緊,勸他不用這么勞累。老人笑著搖搖頭,說我不懂。每當節日全家14口人圍坐飯桌,其樂融融地吃喝談笑,我目睹面帶疲憊、喝著小酒的岳父眼角眉梢都溢滿笑意,才讀懂了老人的心意。
1997年元旦夜晚,操勞一天的岳父難得空閑與子女們打麻將娛樂一會兒,不料在中途上廁所時竟無故摔倒。沒過幾天,老人把兒女們召集到身邊,無奈地傾吐了肺腑之言:“本想春節再操持一次,不想年歲不饒人,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春節你們就在小女兒家過吧?我也該輕松一下了。”
其實,岳父的身體狀態極差已早有征兆。多年來一直咳嗽不止,家人多次勸他到醫院檢查,他總以肺部是老傷而推脫。
1997年元月中旬,岳父突然發覺頸部出現一大硬塊,他誰也沒有告訴就獨自一人到市中心醫院就診,醫生檢查后說已肺癌晚期,病灶轉移!病情很快惡化,住院沒幾天就臥床不起,靠抽痰機幫助抽痰,鼻插氧氣機幫助呼吸。聽妻子講,一次她幫父親腿腳部按摩,父親悄聲對女兒說:“癌癥讓身子骨好疼!”聽后我對岳父的堅強更加敬佩,因為在他飽受病魔折磨之時,我始終看到的是一副平靜安祥的面孔。面對病魔,如此坦然,岳父不愧是從槍林彈雨的戰場上闖出來的新四軍老戰士啊!
岳父盡管離開人世已經18年了,但他那不同尋常的人格、風范、情懷、氣節,永駐我心間,激勵我退休賦閑在家仍每天讀寫不輟。
(責任編輯 李贊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