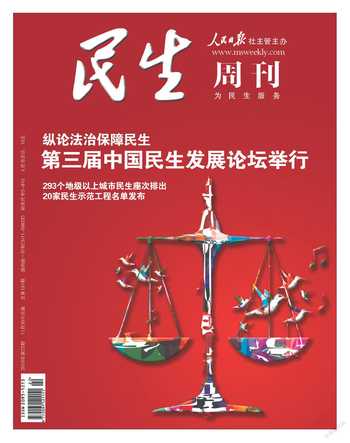“供給側改革”是場革命
賀鏗
會議聯系人給我出了兩個話題:第一是如何看GDP破7。第二是法治如何引領經濟增長。這兩個問題非常難以解答,但我盡量談一談看法。
GDP破7對民生影響不大
先談第一個話題。GDP增長破7,即6.9%,與民生關系究竟有多大?
過去我們的GDP是10%、11%、12%的增長速度,民生問題當然好解決。現在已經降到了7%以下的增長速度,究竟對民生有多大的影響?說完全沒有影響,不大可能。但是影響不會太大。民生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收入增長問題。目前,我們的就業狀況還是比較好的。從公布的城鎮就業率看,比過去沒有降低,而且有一定的提高。但不包含在登記失業率之外的農民工,失業情況確實有增加。從這個角度講,對民生是有一定影響的。
另外,服務業擴大,居民收入從平均數量看,增長還是可以的。與過去比沒有降低,而且出現了很好的情況,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超過經濟增長,這對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良性的、好的變化。
目前的物價比較穩定。雖然沒有出現一些經濟學家判斷的通貨緊縮的狀況,但物價還是比較平穩的。相信這些在大家的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從就業、產業結構的改善以及物價的穩定等方面講,在破7之后,居民生活、民生問題沒有太大的影響。特別是各級政府這幾年更加重視民生問題,各個方面采取的措施都有利于改善民生。
最終消費率大降必致經濟下行
再談第二個話題。法治如何引領經濟增長。我在法律上是外行。但在這方面我還是想講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經濟為什么下滑?我們的經濟增長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進入下滑通道,為什么下滑?我覺得我們的經濟學家,甚至管理層對這個問題沒有認真地、深入地去研究,因此我們在宏觀調控措施方面就不是很準確。當經濟下滑,我們還是一味采取擴大投資,這個辦法對于經濟增長的穩定、對于促進經濟健康發展不會起好的作用。因為我們的經濟下滑,就是因為過度投資所引起的。
1998年因為亞洲金融危機,提出了積極財政政策。長期實行這個措施,導致我們在 GDP的分配結構上出了問題。
我們創造出來的財富怎么分配是有客觀規律的,有它的客觀比例關系。
GDP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最終消費,一部分是資本形成。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最終消費率應該保持較高的比例。資本形成是為了擴大再生產,是為了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有所改善,應該有一個適當的比例關系。
那么究竟怎樣的比例關系才是合理的呢?從世界182個國家和地區的平均值看,最終消費率是65%,資本形成率是35%。有的國家高一些,有的國家低一些。最高的是美國,最終消費率達到70%。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前,我們的最終消費率是62.9%,比65%這個平均數略低一點,應該說是在合理的范圍內。因此,居民的收入增長、居民的消費增長,都能夠保持一個較為適當的關系。
由于較長時期持續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結果是我們的最終消費率每年減少一個多百分點,到2015年,我們的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9.5%,造成內需嚴重不足。盡管居民收入增長在全世界是比較高的,達到7%~8%。這樣的高增長,一方面極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民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長嚴重低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11%左右,居民收入增長7%~8%,比經濟增長低了3到4個百分點,改變了我們GDP的分配比例關系,使最終消費率降到了45.5%。
供給側改革:應放棄凱恩斯主義
二是如何解決當前經濟運行中面臨的問題?
居民的收入低于經濟增長,長期下去,經濟發展當然是不可持續的,當然要進入下行通道的。今年以來,中央領導層已經看到了問題的本質。因此提出了兩個基本觀念:
一個基本觀念是:在制定“十三五”規劃中,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其中最后一個是共享發展。
另一個基本觀念是:最近,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提出,在繼續關注增加需求的同時,要著重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提法。遺憾的是,這個觀點已經提出來十幾天了,媒體好像關注不夠,經濟學家似乎還無動于衷。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個什么概念?
在我們的經濟工作中,推行凱恩斯主義思想,已經有很長時間了。1998年開始,就執行了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引領我們的宏觀調控、政府管理。提出供給側的改革,就是要擺脫凱恩斯的思想,吸收供給學派的思想來改革我們經濟的宏觀調控。
供給學派的思想是什么呢?歸結起來是三點。
一是供給創造需求。要把企業扶植好,怎么扶植企業呢?第二就是減稅,減輕企業的負擔。三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這三條,我覺得特別是第二條和第三條,必須要有法律做保證,不是在口頭上提一提就行了。怎么減稅?稅法要改。政府干預經濟要限制,怎么限制?怎么減少?要通過法律來限制。說政府要改革,要怎么樣怎么樣,已經說了好幾年了。光說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對供給側的改革應該高度重視。關于這個問題,我談一談美國的情況。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出現了所謂滯脹。有人說我們現在不是滯脹,我個人認為應該差不多是滯脹。美國十多年的滯脹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因為從羅斯福起,長期執行凱恩斯政策造成的。到了里根時期,認識到了問題,里根對他的經濟顧問班子進行了徹底的改組,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趕出去了,請進了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經濟學家,實行了所謂里根經濟學。
里根經濟學可以概括為五點。一是削減財政開支;二是大規模減稅;三是放松政府對市場和企業的控制;四是嚴格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長;五是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市場化改革。
這五個方面的政策實施下來,當里根在任的時候,經濟開始好轉,但好轉不明顯。因為政策總是有滯后效應的。但美國經濟在這一改革下,在克林頓時代出現健康的發展。克林頓的8年是美國戰后經濟發展最好的8年,之所以最好,并不是克林頓本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從里根開始的一系列的改革,促進了經濟的健康發展。所以,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
里根經濟改革這五個方面,我們在深化改革思路當中都涉及到了。但是,我們還應該在兩個方面深入研究和探討。一個是國有企業改革,怎么進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二是財政、稅收制度怎么改?我們要敢于改革,但是究竟怎么改革,要研究。
在財政制度、稅收制度、國企的改革方面,美國的經驗都是有法律做支撐的。沒有法律做支撐,改革不了,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國企私有化,我們不可能,但是市場化改革是可以的。市場化是管理權轉讓,私有化是所有權轉讓。無論是所有權轉讓還是管理權轉讓,都需要法律保證。立法必須跟經濟學家結合起來研究,否則的話,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可能流失。改了以后可能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所以在國有企業的改革方面,我認為經濟學家要研究,法學家也要研究,要提出怎么改的辦法來。
美國經濟改革從里根開始,到現在還有一部分仍在進行。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探索、慢慢改。財政貨幣政策,特別是工資政策,都需要改革。
我們經濟中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十三五”期間,是我們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收官時期,這五年中,怎么解決現在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大的問題,是擺在各級領導面前的大問題。我們不能在全面小康社會的時候,還是個平均數。必須要做到發展的均衡、收入比較合理。
因此供給側的改革,它的核心問題,我認為就是要用怎樣的宏觀政策和法律保障,將我們的生產要素引向需要發展的地方去,使生產要素合理流通、科學組合。
生產要素流動要有法律保障
關于生產要素,傳統的經濟學只說是三大要素:勞動、土地、資本。從現代的眼光來看,生產要素還應該包括企業家、技術、信息等內容。這些內容要合理流通,就必須有法律保障。
比如我們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
西部大開發一定要有這些生產要素到那兒去。作為一個企業家,我的資本、我掌握的技術、人才,肯定要到最好的地方、對我有利的地方去。而我們的企業稅是一刀切的,所以企業不愿意動。到需要發展的西部地方,如果企業稅比人家低,我就會去了。你的工資比別的地方高,人才才肯去,技術才肯去。我們稅收上一刀切,工資上卻相反。
我在許多場合講過,我們現在的工資政策和導向,和我大學畢業(上世紀60年代——編者注)時比,完全反過來了。我大學畢業時,到大西北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轉正以后,烏魯木齊工資是每月78元,在北京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轉正以后是每月56元。相差二十來塊錢,這可不是一個小數字。拿今天來說,兩萬塊錢都不止。
所以大西北才留得住人才。現在在北京,如果大學生能找到職業的話,我估計應該是不少于5000元。而在烏魯木齊,大學生找到職業,不會超過3000元。所以,孔雀紛紛東南飛。因此,西部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工資政策要做大的改革。
我也多次舉過美國阿拉斯加發展的經驗。美國阿拉斯加是沙皇俄國的土地,以每平方公里3美元賣給了美國。那里氣候條件非常惡劣,怎么發展?做法是企業稅比本土低很多,工資政策是大學生、研究生到那里就業比本土高很多,這樣,生產要素就到阿拉斯加去了。阿拉斯加現在建設得很美麗。
我們對西部要進行大開發,要對老工業基地進行扶植發展,就要有真正管用的宏觀政策,引導生產要素合理流通,科學組合,只有這樣才能讓經濟發展比較均衡,讓個人收入差距逐漸縮小。
法律上,應該盡快進行個人所得稅改革,房地產稅以及遺產稅的出臺,都要法律先行,讓法律來調節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真正的全面小康社會,收入分配應該是橄欖形的,兩頭小,中間大,特別窮的人少,不可能沒有,特別富的人應該有,也不可能太多。應該是這樣一個情況,我們才是真正的全面小康社會。我們的民生問題才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我們的社會才可以更加的和諧,我們的社會發展才會更加健康。
(本刊記者崔靖芳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