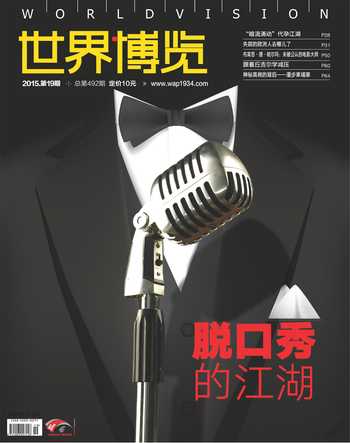藝 ? 境
蔣成龍
鄭根浩(???),1969年出生于韓國忠南燕岐,1991年又石大學(Woosuk University)東洋畫系畢業,2004年獲中國中央美院中國畫系碩士學位,如今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成為了國際關系專家金燦榮先生的博士生。現任中國浙江大學教授、浙江紹興文理學院美術學院客座教授、韓國藝苑藝術大學客座教授、韓國美術協會會員、韓國環境美術協會會員、大田廣域市特邀作家、韓國孝文化節根節日宣傳大使、百濟文化節宣傳大使、地上軍慶典宣傳大使等職務。(文字塊)
鄭根浩曾多次獲得韓國和中國各地的美術相關獎項,舉辦過超過40次個人畫展,作品被中央美院美術館、北京LG大廈、韓國現代畫廊和韓國陸軍本部等單位所收藏。
說起鄭教授給人的印象,恐怕很難讓初次接觸的人聯想到他的職業和工作。沒有外交家的一本正經,沒有藝術家的狂放不羈,平時的他完全是一副憨態可掬,彬彬有禮的學者風度。幾年前在一次中國收藏家協會組織的活動中,筆者經朋友介紹與他相識。操著一口流利但多少有些“洋腔怪調”的中文,鄭教授的話語中透露著對繪畫藝術的熱情,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國際文化、藝術交流的看法。
繪畫專業科班出身的他并非出自藝術世家,父親在韓國的法院系統工作,母親則是傳統的全職媽媽。東洋畫專業畢業后,他一心尋求藝術上的突破,希望能夠從東方傳統文化和歷史中尋求突破。為此,他在1997年只身一人來到中國,開始了進一步的求學之路。
文化尋根與藝術探源
來到中國求學對于鄭教授來說可謂順理成章的選擇,無論從歷史、文化的久遠性,還是藝術形式、風格的多樣性,都深刻影響了包括韓國在內的絕大多數亞洲文明。在韓國學習期間,鄭教授主要以山水類題材的水墨作品為主,融合了眾多東、西方藝術創作技法格,嘗試了大量傳統與創新的結合,最終形成了自己的獨有風格。然而他認為,除了創新之外,自我探索和藝術根源的探尋才是當時遇到的最大困難和不足。
“韓國相比中國開放的較早,所以我很早就接觸過大量西方文化和藝術,覺得暫時夠用了,反而是傳統層面欠缺太多。東方文化在之前的教育中并不充分,所以需要來中國‘補課’,否則無法融會貫通。”
為此,鄭教授1997年便來到中國,在中央美院進修的同時努力學習中文,隨后成功被錄取為研究生,攻讀碩士學位。在他印象里,那時的中國還未全面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各方面都更加傳統。無論是藝術專業還是百姓生活,甚至就連老北京的大院、胡同文化,在他看來都是如此迷人。
碩士在讀期間,他主要以抽象水墨畫和材料學為研究方向。而水墨畫的用色方式、材料特性和構圖方法都與西方抽象大為不同,這使他對藝術和技巧的認知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我的抽象畫是‘東方的抽象’,和西方人不一樣。不同于具象作品表達事物本身的特性,抽象作品需要畫家融入更多思考和想象空間,這與作者和觀賞者的文化背景有很大關系。”鄭教授繼續說道:“在韓國的時候,我的老師非常注重寫生的重要性。那個時候我還年輕,每天走幾十公里路,翻山越嶺去感受生活,這對我的提高非常有幫助。來到中國,我開始從日常生活中尋找靈感,畢竟這里的事情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不同的,值得觀察和思考的。”
來到中國后,除了日常的學習和交往,鄭教授也一直活躍在藝術創作的前沿陣地,期間在中央美院美術館、北京當代美術館、炎黃藝術館、保利大廈等地舉辦了多達40余場的人畫展,最多的時候一年就辦了八場。
當筆者詢問鄭教授作為一名藝術家,是否有經紀人和固定客戶的時候,他憨憨地抓了抓頭,說道:“我沒有經紀人啊,也不知道為什么沒有人找我。客戶也不固定,中國韓國都有,還有一位法國人買過我很多作品。韓國的客戶很多是醫生,很巧合,可能在韓國的醫生比較有錢吧?”說罷我倆都笑了起來。
藝術為媒的文化交流
來到中國十幾年,鄭根浩教授除了虛心求學,努力在藝術造詣上日漸精進之外,也一直在積極努力地探索藝術發展的空間,以及中、韓兩國文化交流的遠大前景。
“2004年畢業后,我在北京炎黃藝術館對外聯絡部工作,從事中韓文化交流工作將近十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并不懂怎么去搞。當時只能向老師和朋友們學習,從中國國際青年交流中心的中日交流項目中借鑒了很多成功經驗。但是我發現自己還有很多理論知識需要補充,很多專業知識需要掌握,所以就到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開始學習外交專業。”鄭教授如此描述當年選擇前往人大求學的初衷。
確實,對于文化交流來說,藝術確實可以稱得上是舉世公認的最好媒介。但跨國交流活動牽扯到諸多外交、公共關系領專業層面的知識、技巧和資源,絕非易事。而從事外交工作的專家之中又鮮有藝術專業出身,缺乏具有藝術家身份的“跨界”人才。
鄭教授認為,隨著中韓兩國的快速發展,人民的經濟水平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與此同時對精神層面的追求會愈發強烈。目前,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主要依靠經濟往來和娛樂行業的推動。這些對于尋常百姓來說固然至關重要,但畢竟只是表層。要想讓人民相互理解,必須從藝術、歷史、文化角度進行更深入的挖掘與互動。
“兩國之間最大的問題是互相‘不了解’,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政府的運作方式,經濟環境和商業氛圍的區別,甚至人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習慣等。這些都和電視劇里演的不一樣,而且這些區別的產生是有歷史、文化等各方面深層原因的。”鄭教授繼續解釋道,隨著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來越久,他開始從更深層面了解這個偉大的文明古國。這不僅對他的藝術造詣提升起到了關鍵作用,也讓他更加清晰地意識到了兩國人民的不同。如果想要拉近百姓之間的距離,就需要讓他們親自參與到交流之中,切身感受這些區別和差異,從而才能認識到如何互補、提升和發展。
對于所謂的“不了解”,鄭教授舉了幾個例子:比如,韓國的行政管理基本是以市為單位,相對松散,藝術領域行業協會在全國范圍內的影響力也呈現“碎片化”的狀態。這在操作大型文化交流項目的時候會產生諸多不便;再者,韓國本地行業協會、藝術機構的數量和規模上也無法和中國相比。根據我國發布的官方統計數字,目前全國范圍內的收藏愛好者大約在7000萬人左右。鄭教授開玩笑地說,整個韓國都沒這么多人口。
“很多韓國游客和藝術家,甚至各層領導們來到中國后都感到非常吃驚。太多藝術和文化層面的東西是他們沒見過沒聽過的。開始他們也不理解我為什么如此執著于兩國交流的事業,但真正來過后,他們都會改變看法的。同樣,當中國藝術家和收藏家前往韓國考察時,也會為整個韓國的藝術行業帶來諸多契機。”
鄭教授繼續說道:“為了能夠讓交流的內容更加豐富,門類更加廣泛,近年來除了藝術相關的專業組織外,也開始和中國收藏家協會進行更多的合作。協會中有各類專業委員會,也有很多水平極高的收藏家,藏品類別也是包羅萬象。這種多元化的藝術品組合更加符合尋常百姓對于文化交流的需求。”
不過與此同時,鄭教授也表示自己努力作為兩國藝術和文化溝通的橋梁,這份差事責任重大,并不輕松。這些年來,他頻繁往返于中、韓之間,協調各方關系,動用一切力量促使各個活動順利開展,可以說是嘔心瀝血。不過,他最終用“苦盡甘來”這句成語說明了自己的決心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當筆者問道他將來的計劃時,鄭教授居然冒出“農村包圍城市”這么個概念,頗讓筆者感到意外。他笑著解釋道,由于自己的能力有限,目前還只能做到局部區域性的小規模交流活動,但這也是兩國之間逐漸互相加深了解的必須過程。他希望今后時機成熟后能夠將交流活動普及到北京、上海、首爾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中,提高藝術交流的影響力,讓更多的百姓領略兩國文化的精髓,進而在各個層面促成更加深入地交流。
“我來到中國都快20年了,絕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我熱愛這里的人,喜歡這里的美食美酒,習慣了中國的生活環境。可以說,我是韓國人,但我的家在中國。”——鄭根浩
(作者為中國收藏家協會學術研究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