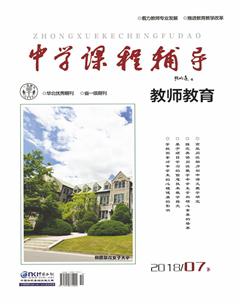學校因素對中學生的心理健康的影響
李常志 遲永剛
摘 要:中學時期是學生心理、生理發(fā)育關鍵時期,也是發(fā)生心理沖突和健康問題的高危期,作為教師,只有準確把握影響中學生心理發(fā)展的學校環(huán)境、教師、同學等學校因素,才能幫助學生安然度過心理沖突期,形成健康人格。
關鍵詞:心理健康;德育為本;學高為師;正能量;融洽
中圖分類號:G63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992-7711(2018)14-043-01
中學時期是學生心理、生理發(fā)育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學生心理沖突和心理健康問題發(fā)生的高危期。中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受多種因素影響,而學校因素則因其特殊地位顯得尤為突出。學校因素主要包括學校宏觀環(huán)境、教師、同學等參與者。下面,我將側重從以上三方面闡述它們對中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
一、學校宏觀環(huán)境是影響中學生心理健康的深遠因素
在中學生心理發(fā)展軌道中,學校因素中的學校宏觀環(huán)境,對學生心理健康發(fā)展起著至關重要的航向引領性作用。而學校宏觀環(huán)境,主要包括學校環(huán)境和學校教育思想。
(一)學校環(huán)境
學校環(huán)境可以分為物質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兩大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硬環(huán)境和軟環(huán)境。這兩種環(huán)境對中學生心理發(fā)展都起重要的熏陶作用。從物質環(huán)境來說,良好的學校環(huán)境就是一個潤物無聲的德育場,能給學生的校園生活帶來愉悅,使學生在緊張的學習之余,放松身心。同時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審美觀。
人文環(huán)境包括校風班風以及校園文化建設。良好的校風班風和校園文化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學生置身其中能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二)學校教育思想
學校教育思想決定了一所學校的校風,要培養(yǎng)出心理健康的學生,首先要在學校教育思想上下工夫,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把“立德樹人”作為學校發(fā)展的根本思路,只有抓住這個根本,才能制定出最科學、最人性化的教育思想,才能把學生作為真正的“人”來培育,關注學生的身心健康成長。
但是,多年來,很多學校還難以走出應試教育的怪圈。沒有實現(xiàn)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根本轉變。在辦學思想上,教學方法上,存在較大的偏差。有些學校為追求升學率,不顧學生生理和心理的發(fā)展需求,隨意加重課業(yè)負擔。加重學生的精神壓力。使學生的心理健康受到很大影響。
二、教師是影響中學生心理健康發(fā)展的基礎性因素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些名言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教師在學生身心發(fā)展中的重要性。毫無疑問,在學校教育中,教師因素已經(jīng)成為學生心理健康發(fā)展的最基礎性因素。我們說的教師因素,主要包括教師素質和教師教育方法。
(一)教師因素
教師是學生心目中的權威,是學生除了父母以外能接觸的最多的長者。教師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學生模仿,學習的對象。所以教師的個性,能力特點,以及教育,教學風格等都對中學生心理的發(fā)展有著極大的影響。陶行知先生說過:“只有學而不厭的老師才能教出學而不厭的學生。”同樣,只有心理健康的老師才能教出心理健康的學生。好的老師無論是班主任還是任課老師,都應以建設和營造有利于學生心理健康的環(huán)境為己任,利用心理學的原理對學生進行恰當?shù)膽土P和鼓勵。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進行精確的教育、培養(yǎng)。好的老師要能和學生交朋友,成為學生可信賴、可親近的人。教師要接納學生的行為,尊重學生的人格;進入學生的內心世界,理解學生的喜怒哀樂,分享學生的情感體驗。
(二)教師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包括直接指向教學內容的教學方法和直接指向學生良好品德形成的育人方法。教育工作既艱巨又復雜,教師要熱愛學生,用真摯的愛去滋潤學生的心靈。去感染學生的情緒,要如涓涓細流,深入細致,循循善誘。決不可急于求成簡單粗暴。學生由于生活環(huán)境,地域特點,智力條件和性格差異等原因,導致他們在思想品德水平,文化知識,學習狀況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面對這些差異,教師不能漠視,不能聽之任之,放任自流。但一定要注意教育方法,要做到循循善誘,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有的教師教育方式簡單、偏激常常用“為學生好”來掩蓋自己的過失。他們對違紀學生缺乏耐心的說服教育,施用體罰和變相體罰的手段,致使學生畏懼逃學,產(chǎn)生師生對立情緒,甚至出現(xiàn)教師學生互相傷害的惡劣事件;有的教師則對學生缺乏公正性,一個班集體由于各種原因,總有一些成績較差的學生,個別教師在學生出現(xiàn)問題時總是偏袒學習好的學生,對成績差的學生橫加指責,惡語相向,導致學生產(chǎn)生自卑心理自暴自棄,放縱自我,心理健康出現(xiàn)重大問題。
三、人際關系是影響中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據(jù)有關科學研究表明,良好的人際關系,可使工作成功率和幸福指數(shù)提高85%以上。對于中學生群體也不例外,在學校環(huán)境中,中學生心理健康,受到校園環(huán)境中特殊人際關系的最直接影響。這里的人際關系,包括師生關系、同伴關系等。
(一)師生關系
師生關系是學生人際關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良好的師生關系不僅能促進學生更好的成長,同時也向學生提供了一種人際關系的榜樣。在充滿愛的師生關系影響下,學生會形成愛祖國,愛家鄉(xiāng)、愛班集體,愛同學的良好心理素質;良好的師生關系可有效調節(jié)學生的行為。
(二)同伴關系
中學生的同伴就是朝夕相處的同學,同學關系的好壞會直接影響中學生的心理健康,有研究表明:經(jīng)常遭到同學孤立,拒絕的學生,在青少年期都表現(xiàn)出了反社會的行為。因此,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同伴關系非常重要,老師尤其是班主任老師要做到:創(chuàng)立一個充滿正能量的班集體,讓每一個學生都有歸宿感;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發(fā)現(xiàn)每個學生身上的閃光點,及時表揚;對個別同學交往能力差的學生進行單獨輔導。
學校因素對中學心理健康影響看似簡單,實則紛繁復雜,可謂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作為教育者,我們應該真正做到“以人為本”,關注學生心理發(fā)展,把各種影響其心理健康發(fā)展的因素加以重視,真正為學生身心健康成長,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