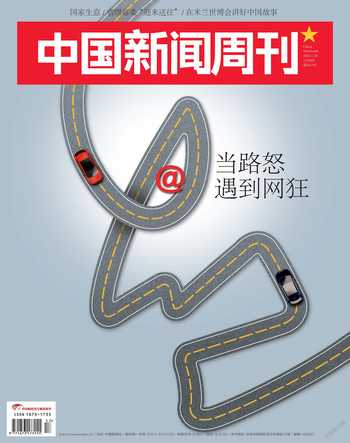南車十年“非洲探路”
閔杰
對于正躊躇滿志準備出海遠航的中國軌道交通行業來說,2014年3月17日是個值得記住的日子。
這一天,中國南車集團和中國北車集團與南非國家運輸集團(TRANSNET,下稱“南非國運”)分別簽署495臺電力機車和232臺內燃機車整車銷售合同,總合同金額超過28億美元,是目前為止中國高端軌道交通裝備出口的最大訂單。
中國南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車株機)海外市場營銷中心副總監王攀至今還記得簽約時有趣的一幕。按當地法律規定,和南非公司簽約的必須是南車株機在南非成立的南非有限公司的法人,也就是王攀本人。但按中國的慣例,上臺簽合同的顯然應該是從湖南總部千里迢迢遠赴南非的中國南車株機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周清和。一位律師給出了解決問題的建議:由王攀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效率的授權書,授權自己的上級周清和上臺簽字。“員工授權上級上臺簽合同”,這個橋段至今還是同事之間調侃王攀的段子。
對于南車株機海外團隊來說,這份訂單意義特殊。從2004年上網查資料了解南非開始,到2014年簽訂國內軌道交通裝備最大出口訂單。10年悲欣交集,這份合同是最好的慰藉。
小城株洲,位于湖南中部,湘江從這里穿城北上。從近代開始,這里就因為地處粵漢、浙贛、湘黔三條鐵路干線的交匯點,奠定了鐵路樞紐的地位。
1936年,粵漢鐵路總機廠在株洲成立,它是南車株機公司的前身。1978年,株機廠被鐵道部確定成為中國第一家專業制造電力機車的工廠,被譽為“中國電力機車的搖籃”。
周清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踏入2000年,隨著國企主輔分離、輔業改制的浪潮,中國機車車輛工業與原鐵道部脫鉤,中國鐵路機車車輛工業總公司重組分為中國南車、北車兩大集團公司,株洲電力機車廠劃歸為中國南車集團,成為旗下的核心子公司。和南非的接觸也從這個時候開始。2000年后,南非幾乎每年都有人到中國來考察電力機車和內燃機車的技術和生產能力。
“當時偶爾會接待一兩個團來參觀一下,但沒有什么明確的意圖。”南車株機分管海外業務的副總經理張旻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2004年開始,公司開始成立海外營銷部,對全球市場按區域進行劃分,公司從這個時候就安排王攀專門負責跟蹤非洲市場。
1998年建交后,中國與南非在2000年通過《比勒陀利亞宣言》確定兩國伙伴關系。此后,外交關系不斷升級。
王攀接手非洲市場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網查找資料,形成非洲市場調研報告。從這時發現,南非早在2000年左右就出臺了比較宏偉的鐵路復興規劃。
南非是世界上較早運營鐵路的國家,在英國殖民地時期修建了比較發達完善的鐵路網,現有的鐵路網和機車車輛量規模都很大。但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因為常年缺乏必要投資和維護,設備陳舊,鐵路老化。“他們一直有更新改造的需求,但一直沒落實。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從2004年開始就一直跟進。”王攀說,從2005年開始,他和南非負責機車采購的人取得了直接溝通。
2006年,收到南非方面邀請后,南車株機的商務團隊第一次踏上南非的土地。
一個星期考察談判后,南非的考慮是,首先拿出30臺機車作為試驗訂單,交給南車株機進行研究和報價,但時間要快,要在一星期之內完成。“按照規定,大項目要進行全球招標,但他們不愿意花很長時間走這些程序,由于一直在跟我們溝通,就希望以議標的方式拿給我們。”王攀說,對方的條件是,價格必須有競爭力,交貨時間要最短,這樣才能說服董事會,接下來也才有可能有更大訂單。“其實這也說明他們對中國產品缺乏信心。”
南非從19世紀開始運營鐵路,也是全世界僅有的幾個擁有萬噸牽引機車的國家之一,對自己的鐵路系統技術一直有優越感,“談判的時候,我們說可以滿足要求,他們總會懷疑,你們怎么可能滿足呢?”王攀說,事后了解到,他們希望以這30臺機車作為試驗,如果試驗失敗,中國產品可能很難再進入南非市場。
不過,在簽訂備忘錄、推進時間表和工作進程都詳盡提交給對方后,想象中的第一批訂單最終無果而終,事后了解到,在“南非國運”集團董事會中出現了反對聲音,“日本公司當時在南非實力比較強,連續做過2個項目,提供過100多臺機車,他們在南非國家運輸集團董事會中進行了游說”。
第一次接近訂單的機會,轉瞬即逝。
直到2011年,新的機會才再一次出現。

中國南車株機公司向南非出口的電力機車。圖/受訪者提供
南非國家運輸集團發出了向全球招標95臺電力機車的項目信息。在等待了四年之后,王攀和南車株機商務團隊再次踏上南非,“期間也沒有完全放棄過,因為上次考察的時候發現,大批車停在那里,用不了,等待維修,這個市場肯定存在,我們就一直在不停跟進。”
與上一次相比,大環境有了一些變化。2010年,在祖馬首次以總統身份訪華時,中國邀請南非加入了金磚國家,兩國經貿關系進一步深化。這些變化也體現在這次談判中,南非方面對中國新興公司的認識和信任度已有所加深,歡迎中國企業參與競爭投標。
“在了解當地配件供應商的過程中,發現有私營企業,也有國有企業,就是國家運輸集團下屬的一個事業部。”王攀說,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一個策略也許起了幫助作用,“我們的想法是,招標方下屬的事業部有這個生產能力,勢必優選下面的子公司。”而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國外訂單都是私營公司進行合作和承接,從來沒有一個國外公司和這個事業部合作。“我們考慮,如果我們進行合作,勢必會增加中標的可能性。”
張旻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南車株機對技術、價格和交貨期,非常有信心。南車株機公司機車年生產能力超過1000臺。而90余臺車幾個月就能完成,能夠迎合南非方面交貨期短的需求。從甄選本地供應商,到測算本地化成本,同時籌劃設立南車電力機車項目公司。這家有南非黑人參股的本地公司,投標技術文件與商務文件準備等項目投標工作進展順利。
整個評標過程持續了半年,但期間國家運輸公司對中國制造能力的將信將疑持續始終。“很多技術項點,我們的標書中寫的是完全響應,他們就會問怎么滿足,要拿出證據。我們說有實驗設施,他們會追問,你們的實驗設施是什么樣的,各種問題無窮無盡。”王攀苦笑說,有些是概念設計,還沒細化到工程設計階段,“但他們說懷疑,那怎么行呢。合同給了你,滿足不了你怎么辦?”
這一輪參加競標的有7家公司,包括西門子、阿爾斯通、龐巴迪、南車、北車、東芝在內的全球知名公司都參與競標。南車株機進入到了最后一輪,競爭對手是加拿大的龐巴迪公司。
在走完了所有程序后,2012年9月,南車株機被告知,再等待兩個星期,如果有消息,就說明有希望進一步談合作。“兩個星期之后,我們沒收到消息,打電話去問,他們說內部還在研究,雖沒有說中止,也沒說繼續往前走。”王攀說,一直到9月底,突然接到國家運輸集團的來函,說集團公司CEO要帶隊來株洲考察。
接到消息的南車株機開始認真準備,為考察團準備了詳盡的行程安排。最先到來的是一個四五個人組成的技術團隊。“我印象很深,那天是周五,在中午接待吃飯的時候,帶隊的技術總工看到行程安排后當場提問,‘你們是不是誤解了我們來這里的意思’?”王攀說,技術總工特別嚴肅地重申,“我是來工作,是來發現和識別風險的,是看你們是不是能滿足我們的技術要求。如果不能,我們就會回去打報告,說風險很大,項目不能給你們。”
兩天以后,南非國運集團CEO帶領技術和商務團隊來到株洲,僅僅參觀了半天,并聽取了先行抵達的技術團隊匯報。當天下午雙方座談時,CEO說,“經過我們的評估,我們很放心,下周到南非去簽合同吧”。
對于南車株機公司來說,驚喜來得太突然,“等了一個月沒有消息,來看了半天就說簽合同”。
考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集團的首席采購官告訴他們,“通過與全球其他企業的對比,你們是最好的,我們以前低估了你們的能力。”直到現在,集團內部在對中國制造有一些爭議的時候,來過中國考察的人會在內部解釋,“你們沒去過中國,去過就知道,這些根本不存在問題。”
和南非的第一個訂單終于塵埃落定。2012年10月南車株機公司與南非簽訂了設計、生產、試驗和供應95臺電力機車的合同。但合同簽署,挑戰才剛剛開始。此次訂單交貨期很短,16個月內要交付首臺車,而國際上一般需要20~24個月。技術難度也非常高,需要滿足25千伏交流和3千伏直流雙流制供電,并且在供電網絡上無間隔無縫切換。同時,南非根據自身鐵路系統特色,提出一些定制要求。
在中國電力機車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劉友梅的帶領下,南車株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術難點。10個月不到的時間內,首臺機車正式下線,開創了中國軌道交通裝備出口最短的交貨時間。
第一臺車機車順利交出,并不意味著此后的路就是一片坦途,更大的挑戰在后面。根據雙方協議,該項目95臺中的其余85臺機車在南非國有運輸集團下屬的科都斯珀特工廠生產。
中國南車株機公司南非項目部總經理蘭雄對此感受頗深,“一年多當地化生產工作中所受的苦和累,幾乎相當于在國內參加工作以來20余年的總和。”
開始時,由于經驗不足、溝通不暢、管理體系對接不上,本地化機車制造的的月產量只有區區的2臺車,照這樣下去,一年的產量頂多也就20多臺機車。
隨著時間的流逝,對于合作雙方來說,心情從開始的喜悅轉變為困惑、失望、恐慌,甚至幾近絕望。到2014年11月初,距最后一臺機車交付僅剩3個月,如要按時履約,在剩下的3個月多時間內,意味著每個月必須完成20~22臺機車的制造。
而當地的合作伙伴既承擔機車當地制造的分包任務,同時也是業主的一個下屬事業部。他們認為,項目已經不可能按時履約,為此他們多次主動提出修改合同交貨期,甚至承諾由其出面與業主協商。不過,蘭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作為在南非市場的開頭炮,中國南車株機公司無論如何也承受不起交貨期違約的代價,因此多次謝絕了當地合作伙伴主動提出的調整合同交貨期的意見。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南車株機選擇了堅持。周清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南車株機公司最多時派出了100余人的龐大技術、物流、項目管理、工藝、生產等團隊趕赴南非。同時,在南非當地的供應商無法滿足零部件供應時,中國南車株機公司不惜代價從國內空運大量的高質量零部件到達南非。
然而,當大量的零部件堆積在機場貨運站時,尚不具備現代化物流管理經驗的南非合作方忙亂得手足無措,南車株機再次出手援助。此后, 2臺、5臺、10臺、20臺,機車產量迅速提升。
“中國企業走出去,在目標市場落地,最需要解決的難題很多,而‘跨文化溝通’與‘跨文化管理’是我們的必修課。”張旻宇感嘆,作為技術援助方,如果被援助的一方限于困境時,作為“教練”既要看到問題所在,還要教會你的“學生”,更要能引導你的學生抱團一道共同解決問題。
與其他海外市場相比,南非項目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在南非大型國企和國家項目中,除了價格外,還有很重要的因素,如黑人經濟振興法案(BEE)、本地化要求、本地供應商開發(SD)等社會經濟因素。王攀解釋,為了提高南非國家鐵路車輛的制造和維保技術能力,并推動相關配套產業鏈的快速發展,南非貿工部對國家采購項目往往提出了很高的本地化要求,有的甚至要求本地成分達到60%。
南車株機公司內部也出現了不同聲音,認為其他海外市場都沒有這么多附加條件,為什么唯獨南非有?隨著項目推開,不僅要在南非成立有黑人參股的公司,還要了解本地化成本,選擇合作生產商,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比在國內直接生產麻煩很多,費時費事。
但隨著王攀對這片市場的深入開拓和理解,他認為所有的這些硬性要求,必須盡可能滿足,“這就是游戲規則,只能去遵守。不僅要在外把項目做好,還要在國內進行產業鏈的分工調整。”
在張旻宇看來,選擇南非國有運輸集團下屬事業部作為當地分包商合作,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不僅有利于拿到項目,在合作過程中,還強化了一個意識,我們要密切協作成為利益共同體,不是做一錘子買賣,而是共同推動當地軌道交通裝備的更新換代與產業升級。”
獲得信任后,新的項目果然緊隨其后。2013年,南非政府向全球發出更大規模的項目招標,共1064臺機車,其中包括599臺電力機車和465臺內燃機車。
直到現在回憶起來,中國南車株機的海外營銷南非項目團隊仍然沉浸在驚心動魄的商務談判場景里。
2014年大年三十,團隊接到電話通知去南非進行最后一輪談判。大年初三,談判團隊飛赴南非約翰內斯堡。去了之后發現,入圍最后一輪談判的有四家公司,南車和龐巴迪競爭電力機車項目,北車和GE競爭內燃機車項目。
“談判過程有太多的艱辛,一個多月的合同談判,最終不僅要鎖定合同條款、合同價格與分包合同,還要博弈合同份額;幾乎場場會談都是驚心動魄,都挑戰談判各方的經驗與智慧的極限。”張旻宇回憶,談判從早上8點開始,四家公司輪流進去;從下午3點開始,又再來新的一輪。“當時的情形是,任何一方談崩了,輕則丟失合同份額,重則直接買機票回國。”
在最后的合同份額競爭中,南車株機和加拿大龐巴迪公司再一次“短兵相接”。在2012年的95臺機車項目談判中,龐巴迪就是南車最后的競爭對手,但最后被南車擊敗。此前,在南非的幾個大項目上,龐巴迪也都頻頻失手,因此這次志在必得。王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聽說龐巴迪全球總裁在談判過程中專程飛到南非,與南非國家運輸集團總裁會面,最后拿下了40%的份額。
2014年3月17日,談判完成的第二天,簽約儀式在南非舉行。中國南車簽署了出口459臺電力機車,價值21億美元的合同,中國北車簽署了出口232臺內燃機車的合同,共同創造了目前高端軌道交通裝備整車出口的最大訂單。
“2014年12月4日,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南非總統祖馬的共同見證下,我們與南非國有運輸集團CEO布萊恩·默勒費代表雙方簽署了軌道交通裝備合作協議備忘錄。”周清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南車株機公司將與南非國有運輸集團在南非成立合資企業,制造、供應并維護南非和非洲其他地區主要的鐵路設備部件。
回望南車株機探路非洲的10年,周清和總結說,對于一個市場,從陌生到進入到成長;對于一個項目,從不可能到可能;對于市場游戲規則,從不熟悉到融身其中,“雙方從貿易合作關系,到文化融合利益共享,終極目標應該是形成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