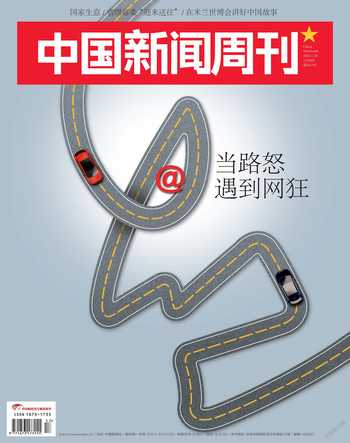一種名叫懷孕的“病”
錢煒
“懷孕給醫學界提供的動力日益增強。在德國,產前檢查在過去20年間漲了5倍。從統計上來看,高危險妊娠已屬于正常現象,準媽媽們有一半以上被歸為高危險妊娠群。但數十年來,懷孕婦女的健康狀況絕對沒有變差,風險劇增主要歸咎于醫生的熱情,他們對懷孕這個自然事件設下的標準越來越苛刻。”
這段話出自德國《明鏡》周刊醫療記者耶爾格·布勒希所寫的《疾病發明者》一書。上述現象被他稱之為“名叫懷孕的病”。中國眼下發生的一幕,與布勒希書中的描述十分相似。無數正準備懷孕或已經懷孕的女性,正在被動接受或主動尋求不必要的檢查與治療。在國內缺乏互信的醫患關系以及準父母們過度重視懷孕的雙重因素驅動下,懷孕已然成為一種需要“嚴陣以待”的“病”。
北京的白領女性陳儀(化名)與丈夫一直忙于各自的工作,到30歲這年,在雙方父母催問之下,才驚覺已經到了完成繁衍后代這件人生大事的時候。自詡為新一代知識女性的陳儀,不聽老一輩的那套中醫理論,打定主意要科學備孕,拉著丈夫一起去醫院做了個孕前檢查。這家大型三甲醫院的婦產科醫生給她開了一個長長的檢查單子,檢查名目之繁多超乎她的預想,光血就抽了好幾管。
過了幾天,她去醫院拿驗血結果,醫生告訴她一個不算太壞的壞消息:其他檢查結果都正常,但甲狀腺功能指標有一項TSH(促甲狀腺激素)超標兩倍多,屬于亞臨床甲狀腺功能減退(俗稱“亞甲減”)。醫生一臉嚴肅地說,亞甲減會造成女性不孕癥,即使懷孕了,也會影響胎兒智力發育并容易流產。“如果懷孕了,早孕期間,TSH數值不僅要在正常范圍的最高限4.9以內,而且要嚴格控制在2.5以下才好。你現在這么高,必須先治療,最好把指標降到2.5以下再懷孕。”
聽了醫生這番話,陳儀連聲諾諾,心想幸好做了孕前檢查,果然及時發現了問題。事后,她和朋友們一交流,才發現身邊很多女性都有這個“病”。
北京協和醫院原婦產科醫生龔曉明如今正在投身醫生創業的熱潮,在北京建外SOHO的一家金融家咖啡館里,這位向來以敢言而著稱的醫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六七年前,孕婦從來不需要在醫院檢查甲狀腺功能。不知從何時起,全國的婦產科醫生開始向每一位前來建檔的孕婦積極推薦甲功篩查。不過,現在,我們終于可以對國內如火如荼開展的孕期甲狀腺功能篩查說一聲No了!”
甲狀腺功能亢進(俗稱甲亢)或者甲狀腺功能低減(俗稱甲減),都屬于內分泌系統的疾病。甲減患者的TSH偏低,游離T4偏高,主要表現為乏力、便秘、怕冷、肌肉痙攣、浮腫、皮膚干燥、脫發。甲減患者若是未經治療直接懷孕,會增加流產、胎兒神經發育異常的發生率。而如果只有TSH升高,而游離T4正常,則達不到甲減的診斷標準,這種情況在醫學上被列為“亞臨床甲減”。
中華內分泌學會完成的《中國十城市甲狀腺疾病和碘營養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有5.32%的育齡婦女有亞臨床甲減,在孕20周前的孕婦中,有5.27%的亞臨床甲減。據估算,如果僅針對高危人群進行篩查,將會有80%的甲狀腺疾病被漏診。
基于上述依據,最近幾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大醫院已經開始在全孕婦人群中推行甲功檢查,并將此項加入了孕前檢查套餐。記者采訪了一位懷孕5個月多的吳女士。她是在北京回龍觀地區的一家三甲醫院分院做的孕檢。她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孕檢里有甲功這一項,在記者的詢問下,她翻閱了檢查單才發現自己確實做過這項檢查,結果是正常。
支持對孕婦亞甲減進行治療的證據是1999年的兩個觀察性研究。這兩項研究發現,亞臨床甲減患者生出的新生兒智力較正常甲狀腺功能母親生育的新生兒要低。然而,這都屬于觀察性質的研究結論,證據級別在2和3級,可靠性不那么高。與此相反,在2012年一個最新隨機對照研究中發現,亞臨床甲減的患者補充或不補充甲狀腺激素,對孩子出生后發育至3歲時的認知功能并無差異。這一結論的證據級別是1級。據此,美國婦產科醫生協會在2015年4月最新發布的臨床指南中,已經不推薦在全妊娠人群中進行甲狀腺功能的篩查和治療。
對此,龔曉明強調說,其實,在舊版的美國婦產科醫師協會臨床指南里,也沒有對所有孕婦推薦進行甲功篩查,而只是說這一問題存在爭議,沒有定論。新的指南則基于最新研究給出了明確結論,這就意味著,那些有亞甲減的孕婦可以停止吃藥了。他補充說,有人也許會認為中國人群因為飲食結構不同,得出的結論會不同,但在沒有充分研究否定掉這個1類證據之前,還是應當遵循這一指南。
然而,此前,國內醫生卻無視國際上對這一問題的爭議,而是一直對亞甲減與妊娠不良的關系持篤定態度。龔曉明說,“也許是他們不愿意知道或假裝不知道這些爭議。”治療亞甲減的藥物并不算貴,一盒優甲樂大約賣幾十塊錢,而“大頭”在檢查費用:甲功篩查在不同醫院的價格是200元~500元不等。一位被判有亞甲減的女性,在整個懷孕期間至少要做3次甲功的檢查。這對于醫院和生產檢查試劑的藥廠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生意。

陳儀的朋友小唐也是亞甲減,最近剛剛生了孩子。懷孕期間,為保證腹中胎兒的健康,小唐每個月都要去醫院抽血監測甲功,以及時調整用藥量,她表示,“相比孩子健康,能花錢解決的都是小事。”當已經吃了好幾個月藥的陳儀知道亞甲減不影響懷孕這一消息之后,卻仍半信半疑,“既然是亞甲減,總歸不是健康狀態吧?吃點藥把指標控制在正常狀態,不是更有利于懷孕嗎?”
陳儀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生活水平的提高讓孕婦及其家庭對懷孕的過程有著神經質般的完美欲,而醫療技術的發展和商業利益驅動也為滿足這種完美欲提供了更多的“說法”和“療法”。
每天,在廣州暨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產科,都有剛剛懷孕的準媽媽來找主任醫師李瑋璟,詢問能否開點黃體酮保胎。在母嬰網站上,還有人發帖說,“這個月監測排卵同房之后就開始吃黃體酮了,姐妹們祝福我這次一定要懷上啊!”李瑋璟說,每每和國外同行提起中國醫生如此鐘愛黃體酮,中國孕婦如此大量使用黃體酮,都會看到一雙困惑和迷茫的眼睛,然后就聽到“why?”
為說明黃體酮濫用的程度,李瑋璟舉了一個最最常見的例子:一位女性在多年等待后終于懷孕,就去醫院查黃體酮,然后住院,每天打針吃藥保胎。李瑋璟問這名孕婦為什么要保胎,回答說怕流產。再問:有流產表現嗎? 答:沒有,只是黃體酮低,醫生說等到出血再保就來不及了。聽了這番話,李瑋璟對這位無知的母親與無德的醫生感到無奈,只好告訴她,“好的胚胎不用保胎,不好的保了也好不了。”后來,在孕中期篩查時,李瑋璟發現胎兒有雙側腎積水,她知道,這和使用保胎藥不無關系。

龔曉明 曾就職于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
長年在產科工作,李瑋璟還處理過更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案例:有孕婦早孕期陰道出血不止,口服和注射黃體酮都不管用,結果到她那里一檢查,發現是宮頸息肉,或者是泌尿系統感染等別的因素引起的癥狀。
對于黃體酮濫用現象,龔曉明也深惡痛絕。他在博客上不客氣地對自己的同行說,“我想給婦產科醫生們做一個科普:在懷孕頭三個月的早孕期間,對所有的孕婦進行β-HCG(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的檢查是沒有必要的。”他解釋說,對于那些有早孕期不規則陰道出血的孕婦,檢查β-HCG、孕酮具有鑒別診斷和判斷妊娠預后的幫助,但對每一個孕婦都進行檢測,就有過度之嫌。然而,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這兩項檢查已經成了國內普遍開展的孕檢項目。
開展普查之后,很多孕婦都被診斷為“孕酮偏低”,繼而開始口服孕激素,打黃體酮“保胎”,這樣的醫療措施聽起來合乎道理,但實際上毫無醫學根據。對此,龔曉明解釋說,大部分的早期流產,都是胎兒的基因有問題,由此可能導致體內某種酶缺失了,或者重要臟器出了問題。這樣的胚胎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在母體內無法繼續發育下去,以死亡表現出來,在母體就表現為陰道出血,甚至組織物排出,導致流產。因此,孕酮低只是流產的一種結果,不是導致流產的原因。
龔曉明說,從停經開始算4~8周之間,是發生陰道出血的高危時期。如果有出血,并檢查出孕酮值在5納克/毫升以下,那么胎兒發生流產的機會很大;若大于25納克/毫升,是正常宮內孕,而介于5~25納克/毫升之間,則屬于需要進一步觀察的情況,但此時也不需要使用黃體酮,觀察變化即可。也就是說,不管孕酮有多低,絕大多數孕婦都不需要用黃體酮來保胎。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僅支持對有3次以上流產病史的孕婦進行黃體酮治療。
在這種情況下,為何婦產科醫生依然熱衷于給孕婦開黃體酮?對此,李瑋璟說,作為安慰劑,給予孕婦黃體酮治療是最簡單也是最安全的的辦法。如果不開藥,流產后孕婦會因為醫生沒有給她保胎而找對方算賬。然而,如果大劑量的使用外源性激素保胎,結果本該流產的胚胎存活下來,其結局可想而知:過量的孕激素會導致很多男性胎兒出現腎盂擴張,甚至腎積水、生殖器發育異常;女性胎兒則可能在青春期后出現生殖器官腫瘤,過量的HCG 還會影響妊娠期的唐氏篩查結果,使原本真的高風險變成假的低風險。
過度醫療在醫療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對于婦產科來說,出于孕產婦對母子健康“絕對安全”的強烈心理需求,過度醫療更是醫患雙方的一種“愿打愿挨”式互動的結果。
既然孕婦有需求,醫生又何樂而不為呢?龔曉明說,一名自然分娩的孕婦在公立醫院生一個孩子才兩三千元,而一個心臟支架動輒好幾萬,一枚骨釘也要好幾千至上萬。相比財大氣粗的心臟外科、骨科等,婦產科在醫院里屬于不掙錢的科室,這迫使婦產科醫生只能想方設法地多開展一些檢查和治療賺錢。
以抗生素濫用這個被業界和媒體常常提及的老問題為例,李瑋璟說,眼下對于圍產期的抗生素使用,普遍存在著過量趨勢。不少人以為,抗生素使用時間越長,預防術后感染就越保險。但已有研究表明,抗生素使用時間過長是不科學和不合理的。
有臨床研究表明,對于包括會陰切開在內的自然分娩,使不使用抗生素進行預防式治療,對產婦的實際感染率沒有區別。中南大學附屬湘雅醫院的一項研究也表明,對于剖腹產,需用抗生素預防手術感染的危險期一般不超過24 小時,其關鍵時間是手術切口切開至縫合關閉的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產婦體中應持續足夠的抗生素濃度來抵御可能污染的細菌。因此,合理的預防用藥方法應是術前半小時至1小時或麻醉開始時給藥,而在臨床實踐中,產婦在術后則被常規性地使用抗生素3至5天。
澳大利亞著名醫療記者雷·莫尼漢在其著作《販賣疾病》一書中揭露了世界頂級醫藥公司為了獲取高額利潤,違背治病救人的醫學理念,重新定義疾病,擴大疾病范圍,使得更多的民眾需要依靠藥物來緩解日常“癥狀”。
耶爾格·布勒希則在《疾病發明者》一書中也表示:廠商和利益團體把正常的生命過程扭曲成醫學問題,讓我們過上了“醫療化的生活”。
在此背景下,懷孕成為一種“病”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