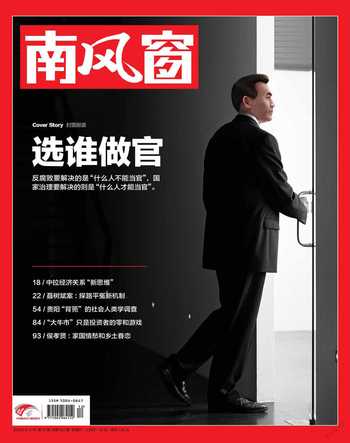高壓反腐更要“打碎權力”
李惠斌
《南風窗》第11期封面報道提到全國各地官員出現了在反腐的高壓下,或者出于“不做不錯”的想法,或者出于做了也“無油水可撈”的心理,從而消極怠工的普遍現象。這一方面暴露了各級地方官員們抓引資、上項目曾經的風風火火背后隱藏著的私利驅動;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傳統動員型發展模式的局限性。腐敗正是這種動員式發展機制中的潤滑劑,一旦阻斷了這種潤滑劑的供應,整個機器的運轉就會出問題。解決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像有人所言,重新注入這種潤滑劑,放下反腐的鞭子;另一個是改變傳統權力動員型的發展模式,用馬克思的話說,叫作“打碎權力”,建立法治政府,把自由和權利還給企業和社會。既然權力對有些人來說已成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為什么不把它還給企業、社會和大眾。推動還權于民,現在可能正當其時。
我們已經習慣了集權統治。改革開放之前是計劃經濟,權力自然集中在各級黨委和政府,最后集中在一把手個人身上。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一再的放權,企業和社會有了一定的自主權,但是,傳統的動員式的開發模式卻一直是我國的主要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確實曾經一度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曾被人們充分地肯定。但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種發展模式的代價是十分巨大的。干部腐敗和社會道德滑坡,是這種發展模式揮之不去的伴生物。各種形式的設租、尋租和推之不去(主動或被動)的權錢交易,無疑是有些官員像打了雞血一樣忙碌的背后動力。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的財富突然間仿佛像中了魔力一樣,從地下冒了出來。而最大的財富是與市場競爭之外的審批權相聯系的。這種審批權著實令我們的一些官員興奮了一陣子。許多人在一夜之間就被巨額財富和女人吸引了。所謂“塌方式腐敗”,一方面說明了腐敗的多發,一方面也反映了反腐的力度。山西如此,別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比山西要好。在反腐高壓的態勢下,中槍的自不必說,沒有中槍的某些干部也已經成為驚弓之鳥,不知道哪一天紀委會找到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干部的積極性自然會落下來,發展的速度自然會慢下來。這時候如果不改變現有的權力動員式發展模式,就有可能給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嚴重的損失,甚至會喪失發展的機會。
十八屆三中全會引入了先進的治理概念,提出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等重要理念。強調要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從統治到治理,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統治是官對民的管控,治理是政府與社會共治和公民自治的結合。統治是集權,治理是權力下移,是分權,或者如馬克思所說是“打碎權力”。這就要求我們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則應該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應該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對政府官員則需要進一步加大問責制的實施力度,真正使每一個官員自覺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既授權必須為”,否則就要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問責。
從統治到治理,大政方針已定,真正做到位,還需要各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