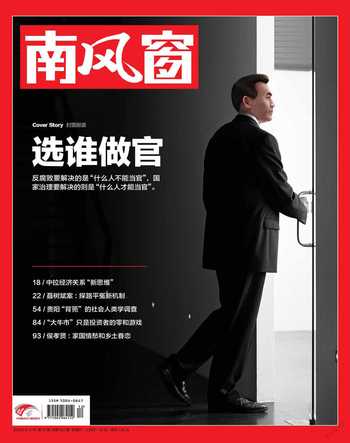中國變身“資本凈輸出國”
雷墨

從中國在國際經濟領域的角色來看,2015年將是一個具有節點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中國的對外投資額很可能首次超過吸引外資的數量,轉身為資本凈輸出國。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力始于2005年,10年間的絕大多數年份增幅都保持在兩位數以上。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160億美元,只比同期中國吸引外資量少35.6億美元。
李克強總理剛剛結束的拉美四國行,再次凸顯了中國在對外投資方面的強勢作為。就拿中國與巴西簽署的總額達533億美元的35個投資協定來說,無論投資金額還是項目數量都算得上大手筆,一舉將中印一年來首腦互訪的經濟成果和中國對巴基斯坦460億美元的投資計劃甩在身后。
關于中國對外投資的快速增長,“逆市增長”總是被強調的一個特點。比如全球咨詢機構安永今年4月發布的報告提到,2011年至2014年,全球直接投資年縮減8%,但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增長達16%。

事實上,“逆市增長”的特點并非中國獨有。中國對外投資的增勢與全球直接投資格局的變遷基本契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3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的占比上,新興市場經濟體從1980年的6.2%上升到2012年的30%。而2012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對外投資中,來自金磚國家的數量占比超過60%。印度儲備銀行去年公布的數據顯示,2003年至2013年,印度對外投資增長了35倍,其中70%的投資額發生在2008年至2013年之間。
從國內背景來看,中國對外投資增長始于2001年提出的“走出去”戰略。不過,最初的“走出去”著力點主要在拓展貿易方面,2005年中國對外投資才開始呈快速上升勢頭。當年中國對外投資額為123億美元,與2004年(55億美元)相比劇增124%!
2012年,中國對外投資額達878億美元,成為繼美國、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韓國又松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迪利普·達斯認為,中國政府在對外投資擴張中扮演了決定性角色,自提出“走出去”戰略之后,中國對外投資在質和量上都發生了明顯變化。他提到,中國對外投資井噴式增長得益于一些特定的因素,比如中國有意識地融入地區和全球經濟、參與全球價值鏈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等。
在中國對外投資歷程中,政府“有形之手”發揮的作用毋庸置疑。經合組織曾在一份評估中國對外投資的報告中表示,中國政府的政策和戰略,在解釋中國對外投資發展上,一直是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不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經濟問題學者丹尼爾·羅森認為,中國的對外投資政策不能不根植于中國經濟的現實,“事實上,中國對外投資的快速增長,正是中國經濟需求的結果”。比利時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鄧肯·弗里曼表示,制度的確在中國對外投資發展中很重要,但制度的角色更為復雜,遠非限制或促進對外投資那么簡單,“不只是政策影響投資,投資者的行為也影響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對外投資大發展,是政府政策與經濟活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李克強總理訪問拉美四國的成果清單,預示著拉美地區將是中國對外投資的一個重點。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增幅,拉美地區是132.7%,遠超大洋洲(51.6%)、非洲(33.9%)和亞洲(16.7%)。而同期對歐洲的投資則下滑15.4%,對北美投資小幅增長0.4%。但2014年,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直接投資分別增長23.9%和1.7倍,增幅遠高于對發展中國家,也高于當年對外投資總體增幅(14%)。中國對外投資態勢的大幅變動,有著復雜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原因,但也體現了中國對外投資行為的強勢特征。美國魯比肯戰略集團董事本杰明·肖伯特,曾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國對外投資描述為“追趕型”。這也是中國對外投資動態變化的原因之一。
從存量看,中國近年來對外投資流量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美國傳統基金會與美國企業研究所共同推出的“中國全球投資追蹤”系列報告,都提到這樣一個趨勢,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美國、澳大利亞以及歐盟等發達經濟體,海外工程建設則主要分布在發展中國家。2014年度的報告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排名前五的分別是: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和英國。韓國學者迪利普·達斯注意到,中國投資發達經濟體意在獲取高科技,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努力,進一步刺激了中國的對外投資。”用本杰明·肖伯特的話說,中國企業利用隨時可獲得的資金,來彌補技術和服務上的短板。
5月16日,國務院公布《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明確以發展中國家作為重點國別,并積極開拓發達國家市場。在訪問拉美期間,李克強總理也提到“國際產能合作”,提議把中國的裝備制造能力與拉美的基建需求結合起來。“中國全球投資追蹤”2014年的報告顯示,過去10年在海外工程建設對象國上,排名前五的分別是尼日利亞、沙特、委內瑞拉、巴基斯坦和阿爾及利亞。從目前情況看,拉美未來的份額很可能會增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投資項目主管卡爾·索文特認為,對于國家經濟來說,拓展投資的范圍和布局,意味著諸如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促進經濟融合這樣的經濟重構有了更多選擇,資源配置也得到了優化。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去年中國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6128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全年累計投資額為1160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的海外利益已幾乎遍布全球。
中國對外投資的另一面是,截至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存量為6463億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1位,與中國經濟總量的世界排序存在明顯落差。但這一現實并未影響中國對外投資行為被過度“關注”。無論是吵吵嚷嚷一個多世紀都沒走下紙面的克拉地峽運河,還是已經動工小半年的尼加拉瓜運河,都由于中國公司的介入而被外界用有色眼鏡聚焦。中國向來突出對外投資的“經濟屬性”,合作對象也希望能得到經濟好處,但中國的“政治動機”總被有意無意地指摘出來。
美國若不重視中國的投資,就不會與中國談“雙邊投資協定”問題。但美國對中國企業的警惕也有目共睹。根據2007年的《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有權對任何事關“國家安全”的投資和并購展開調查。可該法案并未對“國家安全”下明確定義,也就是說美方有幾乎無限的干預權。該委員會2013年審查的97件投資并購案中,針對中國企業的最多(21件)。2013年中海油收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后不久,加拿大政府通過《2013經濟行動計劃法案》,提高了外國國企在加投資門檻。而且該法案把國企的定義修改為:外國政府擁有、控制或者直接或間接受其影響的企業。根據這一定義,加政府幾乎可以把任何一家中國的大型企業定義為國企。
目前歐盟還沒有類似的限制性法案,但政界也出現了中國是“拯救者”還是“掠奪者”的討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索菲·默尼耶認為,中國投資的爆炸式增長給歐洲的決策者造成了兩難:一方面,中國的并購可能會挽救瀕臨破產的歐洲企業,有利于就業和地區經濟;另一方面,中國投資也可能帶來國家安全擔憂,導致無法確保能獲得上述利益。這種獨特的政經邏輯,在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行為中也時有體現。悉尼大學教授詹姆斯·萊利在題為《中國的經濟謀略:將財富轉化為實力》的文章中稱,政治影響力會隨著經濟關系的不對稱性增加而上升,鑒于中國的經濟體量,在貿易、援助或投資上的微小變動,都可能對較小、更具依賴性的經濟體產生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