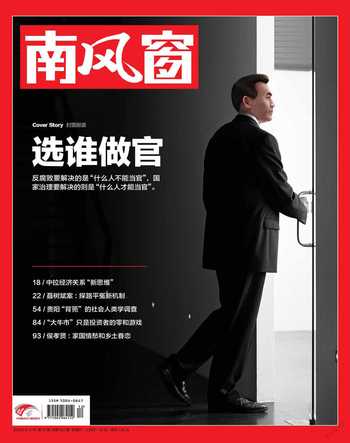美國作為新生大國轉型的啟示
儲昭根

“19世紀80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美國國內引發了一場政權建設運動,權力從各州轉移到聯邦政府,從立法部門轉移到行政部門,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體制開始形成,從而推動美國外交走向國際主義的‘范式轉移’。”著名媒體人法里德·扎卡里亞在其《從財富到權力:美國世界角色的不凡起源》一書中這樣寫道。
從美利堅成長史看,從1877年南方重建結束到進步主義運動(1897~1920)這段時期,正是美國作為新生大國的轉型期。這期間,美國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責任、富人的義務及公民監督與參與的權利,重建了政府的合法性,保證官僚機構的廉潔,有效地解決了諸如生產安全、消費安全、社會福利等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消解了許多潛在的社會運動對政權的威脅,維護了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基本價值觀,并獲得了巨大成功。所有這些,均對中國當前的改革與轉型有著正面、積極的啟示或借鑒意義。
美國從內戰后南方重建到工業化時期,原來的政黨分肥制(the spoils system)已是難以維系,中央行政權力在與立法權的斗爭中一度處于下風,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維護多數人的自由權利,這些都對政府提出了新的需求,也直接導致行政學的誕生。

在美國建國初期,政府運行依靠的是“紳士政治”,即任命文官的主要標準是個人的品德、才能,并兼顧地區分布。華盛頓、約翰·亞當斯和杰斐遜政府,基本上都奉行基于“合適原則”的任命制。隨著投票人口的增加及政黨政治的發展,轉向了分肥制—1829年杰克遜任總統后,將任命制改為分肥式的輪流任職制,起用了大批同黨人士充任官員,約撤換了30%的聯邦公職。政黨分肥制為杰克遜以后的兩黨各屆政府所采用,盛行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政治學家古德諾認為分肥制有兩大缺陷:一是嚴重損害了行政效率;二是除了維持政黨組織的必要性之外也找不出它存在的理論依據。第18屆總統格蘭特,因分贓賣官的問題,險遭國會彈劾下臺,第20屆總統加菲爾德更因為支持者求職未果而遭槍殺,改革政黨分肥制由此提上日程。
與政黨分肥制一樣不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還有南方重建過程中形成的國會至上的“國會政體”。美國內戰結束后,由共和黨主導的國會在與總統爭奪南方重建的領導權的過程中,憑借憲法賦予的立法權,通過自身內部力量的整合,不斷打壓總統行使權力的空間,甚至差一票就能彈劫一位總統。
這之后美國政府的職能擴張,與熱絡的工商發展、西部開發與壟斷的形成有著邏輯關聯。早在美國重建之時,不健全的民主制便給特殊利益集團造成可乘之機,而自由放縱的經濟競爭更是導致他們不擇手段地拉攏政治代理人;為因應西部開發,需要建立州際鐵路及交通網絡,聯邦政府和各州立法機構幾乎都與鐵路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團聯系密切,政治腐敗已成為全國性的社會現象。為了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美國政府的職能擴張成為必要。
此外,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殖民列強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特別是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外交、安全和防務等問題在美國的政策架構上日顯突出,這在客觀上要求擴大總統行政部門的自主權力,以應不時之需。同時總統的權力意識也日漸增強,常常主動出擊,并設立只受其約束的總統辦事機構。
從理論準備來看,在大工業和城市迅猛發展的沖擊下,堅持古典自由主義傳統、鼓吹社會進化論思想的人們遇到了許多新問題。針對議會的腐敗,“新民主運動”對于早期的民主主義要求進行了反思和修正,不再強調權力的分散,反而希望政府、行政力量應該站出來,成為匡扶社會和經濟進步的工具。而包括實用主義、動態社會學、美國新經濟學派、制度學派、行政學等等,這些思潮都為美國進步主義運動與行政擴權及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為擺脫大國轉型期出現的“壟斷資本俘獲政府”的危機,美國統治精英加快了行政改革及行政擴權的步伐。
一、美國文官制度改革。1871年美國政府成立統一的文官事務委員會,1876年海斯總統指令海關、稅務、內政等機構試行公開競考選用文官,這些改革措施在政黨分肥制盛行之際并未收到明顯效果,但改革文官制度的步伐并未停止。隨著共和黨總統加菲爾德1881年被一名求職未遂者刺殺,以及次年共和黨中期選舉嚴重受挫,為了防止可能上臺的民主黨利用分肥制削弱共和黨勢力,共和黨轉而支持民主黨議員的改革提案。于是,美國國會1883年通過《彭德爾頓文官法》,用以遏止封官賣爵的歪風。
二、建立大批隸屬于總統、專業與強大的行政機構。從當時最能體現政府功能擴張的對鐵路公司的管制改革開始,到19世紀末政府掌管了電信郵務、交通建設、工商業管理等業務。1901年總統威廉·麥金萊被無政府主義者刺殺身亡,西奧多·羅斯福繼任總統后,增設了商務與勞動部,隨后又連續設置了幾個重要的職能委員會:聯邦儲備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會、聯邦農業委員會、美國海運委員會、鐵路勞工委員會和預算局。老羅斯福開創了通過建立大批行政機構來擴大總統權力的先河,此后的幾屆政府都對建立行政機構樂此不疲,從而使得權力加速向總統集中。
三、總統立法權的擴大。從西奧多·羅斯福開始,總統通過向國會頻繁提交國情咨文的方式,積極參與國會的立法過程。在威爾遜執政期間,他打破約翰·亞當斯以來把國情咨文轉交給國會的傳統,在就職的第二個月就親自到國會宣讀咨文并提出立法的要求。威爾遜的舉動,不僅贏得國會的好感,還推動國會迅速通過自己所希望的立法,同時作為一種輿論手段,也起到了阻止院外活動集團對國會施加影響的作用。自此以后,總統提交的國情咨文實際上成為一種立法綱領,而此前,立法權力一直是單獨控制在國會手中的。
四、反托拉斯運動。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規定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托拉斯問題。不過,反托拉斯法運行至西奧多·羅斯福時期才有明確的成果。在1890至1901年間,聯邦政府提出的反托拉斯訴訟中,竟然沒有一件獲得勝訴。老羅斯福通過法律增加司法部的編制,提高其反壟斷的起訴能力。他根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提出了43起案件,限制或解散了許多壟斷企業,因此被人送外號“托拉斯馴獸師”。在塔夫脫時期,聯邦政府起訴的大企業比老羅斯福8年中起訴的大企業還要多。一些改革派人士認為,保護性關稅是“托拉斯之母”,威爾遜執政之后,立即敦促國會通過了《安德伍德-西蒙斯關稅法案》,將平均稅率由40%以上降到27%,大大減少了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關稅。
五、強化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西奧多·羅斯福授權州際貿易委員會設置鐵路運費上限,并對食品、養畜和肉類加工企業進行稽查和實施強制衛生標準,以及加入了當時剛剛興起的自然資源保護運動。老羅斯福離任之前還推出了美國聯邦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經濟社會規劃,其中包括征收所得稅和遺產稅,制定《雇主義務法》來保護受傷工人等。塔夫脫1908年當選美國總統,他擴大了政府管制鐵路公司的權力,第一次將電話與電報公司納入政府管制,還支持工廠安全生產立法,建立了美國兒童局。伍德羅·威爾遜上任后,繼續深化羅斯福的改革措施,開征了個人所得稅,重組了國家銀行系統—1913年推動建立了公眾控制的聯邦儲蓄委員會,履行中央銀行的功能;一戰期間建立了戰時工業委員會,對全國經濟進行強制管理。對外,威爾遜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以武力的方式把美國利益推進到世界范圍、把美國理念帶入國際政治,并期望以美國價值觀統帥全球意志的美國總統。
六、預算改革。伴隨著政府的支出規模越來越大,要求徹底改革政府財務和預算管理制度,以消除腐敗、提高效率和落實政府責任的訴求也越來越強烈。1905年,一批人設立了旨在推動紐約市預算改革的“紐約市政研究所”,今天大名鼎鼎的“布魯金斯研究所”便是由它演化而來的。預算改革者指出,沒有預算的政府是“看不見的政府”,也必然是“不負責任的政府”。這場以行政預算為目標的全國性預算改革運動,從精力充沛的老羅斯福總統向國會奪取創制權開始,經過塔夫脫總統贏得制訂并向國會提交預算的權力,直到1921年哈定總統簽署《預算與會計法》,才算是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并且也促進了美國現代總統制的形成。
從美國南方重建結束到1921年美國《預算法》出臺期間,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全面完成給美國社會和生活帶來時代巨變。城市化引起了大規模社會變遷與轉型,美國從一個鄉村型社會,變成城市為主的工業型社會。外交上,美國從區域強國邁向全球,作為一個新興大國崛起,為二戰后平穩過渡為世界霸主奠定了根基。
梳理美國作為新生大國的內部轉型,可以發現有幾點思路對今天的中國改革教益尤多。
首先,改革以效率為目標,從體制運行機制入手,通過制度創新“化危機為轉機”。美國政府通過改革官僚制度,使“政黨分肥制”徹底失去存在的基礎;以科層制、功績制加以培訓和管理的職業官僚,轉變了“政府被俘獲”的頹勢,提高了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干預的程度,進而增強了政府能力;通過提升行政效率,承擔越來越多的職能,政府嘗試滿足越來越多的社會需求,直到碰到它擴張的邊界。政府作為制度變遷中最關鍵的主體,其行為目標對轉型或治理的方向有著決定性影響,怎樣合理發揮政府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值得思考。
其次,正確認識市場、私有財產保護等問題。古典自由主義中保障個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權力,啟蒙運動的自然法學說所倡導的“有限政府”或“最小政府”的思想,都是美國立國的精神淵源。但是,美國進步主義確定了政治討論的用語“托拉斯”和“特殊利益”威脅著“民主政體”和“個人自由”;放任主義的政府無法重視“競爭”,也不能帶來工業主義允諾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市場原教旨主義宣稱市場可以自動回復平衡,但是市場卻沒有被設計得可以用于維護公共利益。由此,政府要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守夜人”,轉變為對國民經濟進行主動干預的積極角色,包括開征個人所得稅,對貧富分化進行有效調節等等。
再次,現代社會對監管的需求是無限的,我們應該看到,美國這一時期在行政權急劇擴張的同時并沒有打破原來的權力制衡。相反,美國行政權的擴大恰恰是議會種種方案,甚至是憲法修正案所授予的,是在憲政框架范圍內,原有的監督、制約依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包括這期間國會基于現實的需要給予總統的“任意性權力”,也在1892年的“菲爾德訴克拉克案”的判決中,得到了聯邦最高法院的支持。也就是說,美國進步主義運動之所以獲得巨大成功在于兩個“強化”—強化政府對經濟-社會的監督與調節;強化國會、司法對行政的監督與授權。強化監管貫徹整個時代的始終,才保證了效率與公平。
最后,美國預算改革從整體上為美國人重構了一種全新的國家治理模式。公共預算其實是各種利益集團在政治領域尋求自身利益的有效工具,其重要性不亞于選舉制度。而且,公共財政改革是低調的,不會過分提高人們的期望值;它是具體的,比抽象談論“政治民主”更容易操作;它是務實的,可以在不太長的時間里產生看得見的變化。一句話,美國預算改革不僅讓民眾參與到政治中來,更為關鍵的是讓抽象民主過程、盲目的政治參與,演變成與具體、實實在在的自身利益結合起來,更是賦予公民及社會無限制的監督權利。
總之,研究美國1877~1920年的行政擴權及改革,對于中國分析自己當前面臨的相似問題,并且從現代公共行政學出發打造全面監管下的“效率政府”,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