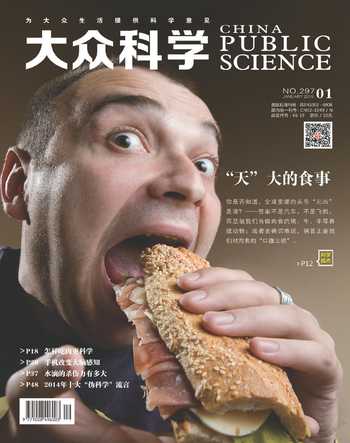隱姓埋名28年的氫彈元勛
近日,201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最受關注的國家最高科技獎授予了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于敏。
作為“兩彈一星”元勛之一,于敏是我國自主培養的杰出核物理學家,也是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曾經為了我國的核武器研究而“隱身”近30年。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從小他就愛問為什么,對于新知,總喜歡探究其所以然。讀高中時,他就以門門功課第一的成績聞名全校。
1944年,于敏考進北京大學工學院機電系。1946年,出于對理論研究的熱愛,于敏轉到理學院物理系,并將專業方向定為理論物理。當時,他的學習成績總是名列榜首。
不久,于敏被慧眼識才的錢三強、彭桓武調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1年,他在錢三強任所長的近代物理所開始了科研生涯。他與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結構模型,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
在研制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于敏幾乎是唯一一個未曾留過學的人,但這并沒有妨礙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巔峰。彭桓武院士說:“于敏的工作完全靠自己,沒有老師,因為國內當時沒人熟悉原子核理論,他是開創性的。”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獲諾貝爾物理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訪華代表團來華訪問,于敏的才華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回國后,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國產土專家一號”。
1961年1月12日,正當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時,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他談話,秘密交給他氫彈理論探索的任務,于敏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分配。
從那一天起,于敏開始了長達28年隱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連于敏妻子孫玉芹都說:“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的。”于敏自己說:“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國的強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國際上,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都是指氫彈,但氫彈設計遠比原子彈復雜。一方面原子彈和氫彈技術原理不相同,另一方面,國際上核大國對氫彈的研究絕對保密,沒有任何公開資料,這意味著氫彈理論探索要從零開始。
1965年,于敏被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9月,他帶領小分隊趕往華東計算機研究所。當時,我國僅有一臺每秒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但其95%的時間被分配給了原子彈計算,只有5%的時間能留給氫彈設計。于敏領導的工作組只能人手一把計算尺,廢寢忘食地計算。
100多個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頭于堆積如山的計算機紙帶,然后做密集的報告,終于率領大家發現了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路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1966年12月28日,中國進行氫彈原理試驗。5個多月后,1967年6月17日,我國西北羅布泊上空,蔚藍色的天空驟然升起一團熾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幾百個太陽還要亮的光芒,急劇翻滾的烈焰騰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云,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圓滿成功!
中國人從此擁有了氫彈,當量330萬噸級,于敏這個名字從此也與中國氫彈技術緊緊連在了一起,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核武器分冊中,“于敏”的條目下赫然寫著:“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
目前,全世界只有兩種氫彈構型——美國的T-U構型和中國的于敏構型。諾貝爾獎得主、核物理學家玻爾稱于敏是“中國的氫彈之父”。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軍委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于敏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他在代表獲表彰科學家發言時總結說:“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3個月,前蘇聯用了6年3個月,英國用了4年7個月,法國用了8年6個月,中國人只用了2年8個月,中國創造了研制氫彈的世界紀錄。”
第一顆氫彈只是試驗裝置,還不能用作導彈運載的核彈頭,屬于第一代核武器。要與運載裝置導彈適配,必須提高核裝置威力并將其小型化,發展第二代核武器。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于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全面負責領導突破二代初級和次級原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不但在初級小型化和中子彈原理試驗方面取得了圓滿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實現重大決定性進展,而且次級小型化技術途徑已明確,核武器事業躋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但于敏沒有盲目樂觀,他將視線投向全球。當時美國仍在不斷做地下核試驗,于敏分析,美國核戰斗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為保持美國的核優勢,限制別人發展,美國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促成國際上簽署全面核禁試條約。
如果必須做的核試驗沒有做,該拿到的數據沒有拿到,豈不是要“功虧一簣”?于敏心急如焚。他顧不上當時鄧稼先已身患重病,就直奔醫院談了自己的想法,鄧稼先亦有同感。幾經思考,鄧稼先和于敏給中央打報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進程的建議。正是這封建議書提前規劃了我國核試驗的部署,黨中央做出果斷決策,我國才爭取了寶貴的十年熱核試驗時間,完成了必須做的核試驗。
相比美蘇上千次、法國200多次的核試驗次數,我國的核試驗次數僅為45次,不及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
于敏選擇的是既有發展前途、又踏實穩妥的途徑,大多時間花在用計算機做模擬試驗上,集思廣益,保證了技術路線幾乎沒有走過彎路。
禁止核試驗后,如何保持我國核武器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綢繆。他提出,一定要把經驗的東西上升到科學的高度,用計算機模擬等新方式開展深入研究,確保庫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該建議被采納并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重要支柱,至今它仍是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如今,89歲高齡的于敏仍然擔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以平生所學繼續為祖國的核物理事業提供咨詢和建議。(來源:綜合《科技日報》、《四川日報》、《南方都市報》 責任編輯/和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