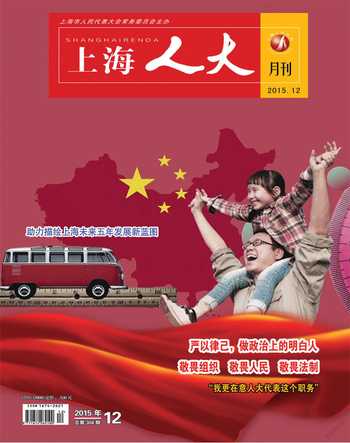鐵路服務中的柔性管理
丁冬
近日,浙江大學大二學生小陳因“二次購票”起訴昆明鐵路局并獲準立案受理的消息引起廣泛關注。事情很簡單,小陳在登車時發現自己的車票不慎遺失。在出示了購票短信、紙質火車票照片和二代身份證后,列車長仍要求小陳補票并交納了手續費。到站后,小陳試圖退票也被拒絕。百度一下,筆者發現,因為車票遺失,而導致“乘一趟火車,交兩次車費”的事例并不鮮見。2014年4月,長沙旅客何奎乘坐武廣高鐵時遺失車票,在出站時被要求全額補票。事后,他將廣鐵集團告上了法庭,要求廣鐵集團退還164.5元票款、2元補票手續費,賠償1元錢損失。同年10月,法院一審判決廣鐵集團向何奎退還補票票款。2014年12月30日,因消費者對此類事件的多次投訴,浙江消保委一紙訴狀以公益訴訟的名義,將上海鐵路局告上法院。
從法律關系的角度看,旅客與鐵路運輸企業之間形成的是鐵路運輸合同關系。鐵路法第14條、合同法294條都明確規定:旅客乘車應當持有效車票,對出現無票乘車等情形的,應當補收票款,承運人還可按照規定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承運人可以拒絕運輸。原鐵道部1997年制定的鐵路旅客運輸規程第43條規定:“旅客丟失車票應另行購票。在列車上應自丟失站起(不能判明時從列車始發站起)補收票價,核收手續費。”上述法律以及鐵路部門制定的內部規程是鐵路運輸部門要求遺失車票的旅客另行購票并加收手續費的主要依據。而旅客在另購車票后,退票的前提條件運輸規程也作了限定:“……又找到原票時,列車長應編制客運記錄交旅客,作為在到站出站前向到站要求退還后補票價的依據。”
旅客應當持有效車票乘車自不待言,在實名制之后鐵路部門除了查驗車票還同時查驗身份證,做到票證同一。鐵道部的運輸規程載明:車票是鐵路旅客運輸合同的基本憑證。但我們必須看到,上述法律和運輸規程的制定實施都是在鐵路購票實名制實施之前,彼時既沒有電子購票的方式,也沒有實名制的約束。彼時,車票可以說是能夠證明鐵路運輸部門與旅客之間建立了運輸合同關系的唯一憑證。彼時,鐵路運輸部門因此將旅客在乘車時是否持有車票作為判斷旅客是否是“持有效票乘車”和是否需要另行購票的唯一依據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在實行實名制購票和電子化購票的“互聯網+”時代,紙質化車票并不再是證明旅客“是否持有效車票乘車”的唯一依據,在旅客出具了購票成功短信、電子郵件或者登錄購票賬戶展示購票信息等證據的情況下,鐵路運輸部門仍然要求另行購票,無疑有利用優勢地位加重他人負擔或削減他人權利之嫌。此外,利用旅客的身份信息或者電子購票信息核查旅客是否購買了所乘車次的車票,從技術角度而言似乎也并沒有什么大的障礙。
退一步講,即使在車輛行駛過程中,不具備當場核查的技術條件。那么在旅客另行購票后并抵達目的地后,憑借原始購買的電子數據和訂單號等證明也應享有要求退還原始車票款項的權利,而不是如運輸規程所設定的“找到原票時”才可以退票這樣的顯失公平的格式條款。在旅客提供證據證明自己因車票遺失導致二次購票的情況下,鐵路運輸部門不同意退票的行為,明顯已經構成了不當得利。車票丟失,雖然是旅客本身的過錯所導致的,但這并非鐵路運輸部門強制要求旅客補票并設定苛刻條件限制旅客退票的理由。特別是在電子化購票、憑借身份證就可以刷卡進站的購票實名制背景下,從公平合理的角度出發,鐵路運輸部門應該尊重和接受旅客以電子購票數據等進行自證的權利。只有在旅客不能證明自己已經購買車票的情況下,鐵路運輸部門才能要求旅客補辦車票。在技術手段不成為障礙的情況下,通過電子數據核查旅客的車票信息也應是鐵路運輸部門應承擔的必要責任。
2013年,國務院撤銷鐵道部,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改革初衷是推進鐵路政企分開,為社會提供更高效、優質服務。踐行初衷有時候很簡單,就是從主動適應購票實名制、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的鐵路服務新形勢開始,變強制補票為柔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