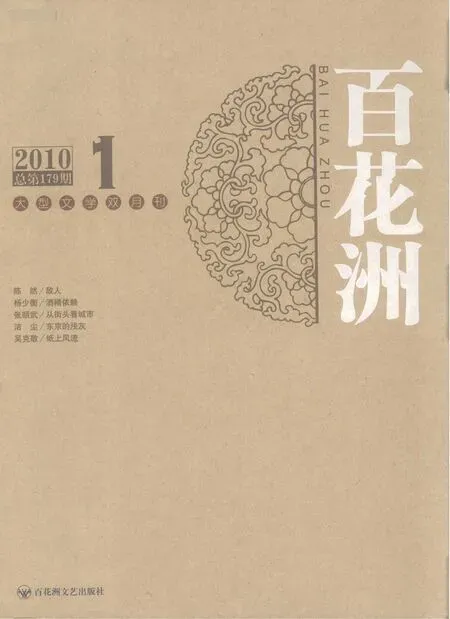飄過國界的哈達
飄過國界的哈達
在西藏,凡是接待來自他鄉的客人,主人都要為他們獻上潔白的哈達。
這是一種藏傳佛教的風俗,也是一種美好吉祥的祝福。
去年7月中旬,因為前往日喀則地區的聶拉木縣樟木鎮進行專項調研,動身的時候,當地的群眾照例熱情地為我們每人系上了一條哈達。
車輪飛轉,哈達伴行。我們沿著中尼公路向樟木前進。
中尼公路是西藏目前唯一的一條國際公路,修建于20世紀60年代,起點是拉薩市,越過喜馬拉雅山,最終到達尼泊爾的首都加德滿都,而樟木就在中尼邊境的中國一側。
在此之前,由于我們所到的西藏其他地方,都是雪域高原,所以預想中的樟木也肯定是這番模樣。但是在過了聶拉木縣城進入喜馬拉雅山南邊的一條大峽谷之后,隨著海拔的降低,兩旁的景色也像電影的鏡頭一樣不斷變幻和切換出新的畫面。先是在鐵青色的光山禿嶺上疊印出綠茵茵的草地,接著草地又漸漸地幻化成翠生生的灌木林,而后灌木林又在不經意間切換成了郁郁蔥蔥的大森林。一些不知名的樹木,從刀劈斧削般石壁的縫隙里斜生出來,用虬干曲枝懸空撐起了一把把巨傘,繪成了一幅不畏艱險頑強不屈的綠色生命圖景。峽谷中間,一條小溪歡快地奔流著,不時被水中的石塊激起白色的浪花。嘩嘩的水聲伴著沁人的綠意,把我們帶進了一個童話般的仙境。
這是缺氧貧瘠的西藏么?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概是看見我們臉上的驚異表情,隨同的藏族同胞告之說,因為這里地處喜馬拉雅山的南坡,經常受印度洋暖濕氣流的影響,所以氣候溫和,雨量充沛,非常適合樹木的生長。其實在西藏,這樣的地方很多,西藏不僅是世界的屋脊,而且是全國最大的林區,其中不少地方還是人跡未至的原始森林。
真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西藏,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西藏,一個生態優美生機盎然的西藏。
峽谷很長很深,一眼望不到頭。兩邊的山峰相峙而立,就像兩扇聳入云霄的巨大綠色屏風,把天空夾成了一條云的河。公路是沿著一邊的峭壁開鑿的,上是望不到頂的懸崖,下是見不到底的深淵。人坐在車上,不免有些膽戰心寒。偏偏這時前方又出現了滑坡,本來就剛好可以會車的路面向下坍塌了一大半,臨時用木頭撐搭起來的路面顯得十分的單薄。我們的心被嚇得猛地蹦到了嗓子眼,幸好司機是常年在崇山峻嶺中駕車的藏胞高手,只見他小心翼翼地把車子緊靠里邊慢慢行駛,車子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顛簸了幾下就安全地通過了。大家懸著的心也一下子放了下來。然而沒過多久,又是一陣云霧奔涌而來,霎時間,樹林、公路和整個峽谷都隱藏在了一片茫茫的白色中。我們的車子也宛若在天上的云海里緩緩飄駛,只有谷底的流水聲提醒大家這是在人間。也許是因為濃重的云霧遮蓋了視線,我們原本覺得很危險的公路也不覺得那么危險了。人類有時就是這樣奇怪,只要眼睛沒有看見,許多平時不敢涉足的危險也能毫無畏懼地闖過去。
山間的氣候說變就變,剛剛還是云霧繚繞,現在卻是細雨霏霏。飄飄灑灑的雨絲好似無數輕盈柔軟的手指,把山中的那每一片樹葉、每一塊巖石化作了精美的琴鍵,彈奏出一曲又一曲天籟般的原生態小調,如夢如幻,奇妙極了。雨不知什么時候停了,整個山林青翠欲滴、流光泛亮,像浸透了的碧玉,又像水靈的翡翠。特別是那些瀑布,不是十幾條,而是上百條,依次懸掛在綠色山崖上,好似無數條白色的哈達在飄舞。我們不由得感嘆西藏山水的神秘與神奇,連瀑布都充滿了這么濃郁的藏味。
越往下走,山越來越陡,路越來越險。這與一般的山脈越到高處越陡險不太一樣,喜馬拉雅山的南坡在山腰以下幾乎都是懸崖峭壁,不少地方簡直就是垂直狀態。反倒是到了5000米左右的高處顯得相對平緩,而在快要臨近峰頂的地方又重新變得險峻。這也在無形中對應了人生及其事業的一個規律。大凡有非常成就的人,在他事業的起步階段都是異常艱難的,橫亙在其面前的,不僅有陡峭的山崖,而且有數不清的險阻,這時他只有敢于冒險勇于攀登,才能登臨到一個比較平緩的事業高度,然后再以此為新的平臺繼續向上攀登,從而最終到達人生事業的輝煌頂點。
也不知向下拐了多少道彎,在海拔2300米的前方坡谷綠蔭中,隱隱約約地現出了一方方五顏六色的屋頂,有灰色的,有黛色的,有白色的,有紅色的,原來是樟木鎮到了。這是一座典型的山城。街道沿著之字形的盤山公路而建,兩邊都是兩三層磚木結構的精致藏式小樓,其中也夾雜著一些六七層的現代建筑。各種各樣的商店一間接著一間,有賣尼泊爾商品的,有賣印度商品的,有賣瑞士名表、國外戒指和玉器等高檔商品的,但更多的是賣當地的木制、牛羊毛和絲織等工藝品的,還有不少的賓館和飯店,特別是那些特色風味的小吃店,從里面不斷飄溢出來的牛羊肉香味,讓人聞了直吞口水。街上人流如織,車水馬龍,使本來因為街路合一就很狹窄的街道顯得更為擁擠。一些中青年婦女在街邊的自來水龍頭下沖洗著長長的頭發。一些老人和小孩三三兩兩地坐在街旁,那悠閑自在的神態,仿佛在向過往的行人詮釋著幸福的真諦。
從鎮中心再往下約三公里,便是我國的邊境口岸。這里不僅有莊嚴的海關,而且還有初具規模的邊貿市場。每天,一輛輛滿載貨物的中尼兩國卡車不時從這里進出,一批批中尼兩國的邊民和商人在這里做買賣。中國的電子產品和日用產品從這里源源不斷地輸往尼泊爾各地,而尼泊爾的大量精美手工制品也從這里源源不斷地輸往中國的西藏和內地。同時這里還是中尼兩國旅游的主要出入通道,每年都有數以萬計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人士來此觀光旅游。據說在高峰時期,邊貿和旅游的日均人流量都在五六千人以上。在從事邊境貿易和旅游業的中國人中,有全國各地的商人,也有本地的邊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夏爾巴人。這個原本居住在喜馬拉雅山南部深山老林中的原始部落,是藏民族的一個分支,過去從不知“生意”二字為何物,但自十幾年前搬到樟木鎮后,如今已成了闖蕩市場的生力軍。300多戶人家不僅都做起了邊貿生意,而且還辦起了為旅游服務的各種店鋪,尤其是2009年興辦的夏爾巴民俗文化度假村,獨特的民族風情和奇異的自然山水讓許許多多的中外游人贊嘆不已。夏爾巴人也由此逐漸走上了富裕的康莊大道。真沒想到,方興未艾的邊貿和旅游,使這個昔日貧瘠落后的邊陲小鎮到處流淌著一種國際化的氣息,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
在離開樟木鎮的前夕,我們特意去參觀了中尼友誼橋,它像彩虹般地橫臥在大峽谷的急流之上,標示著中尼兩國的分界線。橋的這頭屬于中國,橋的那頭屬于尼泊爾。當我們興致勃勃地到達橋的中間時,早在那里等候的尼泊爾邊防人員便迎了上來,一個個地同我們熱情擁抱,并為我們每人獻上了一條金黃色的哈達。雙方就像多年的老朋友重逢似的,有說不完的話,有敘不完的情。在友誼橋上,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尼兩國人民之間源遠流長的深厚友誼。
沉浸在友誼氛圍中的時間總是短暫的。不知不覺半個時辰過去了。當我們同尼泊爾朋友告別時,大家心里都有一種依依不舍之情。這時,我情不自禁地撫摸著胸前的哈達,然后又抬頭望了望盤繞在重巒疊嶂中時隱時現的中尼公路,不知怎的我忽然感到這條公路就像一條綿延千里的哈達,系著友誼和祝福,一頭連著尼泊爾,一頭連著我們中華民族。而樟木,就是這條千里哈達上的一個吉祥如意結。
中尼公路,一條飄過國界的哈達。
中尼公路,一條穿越時空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