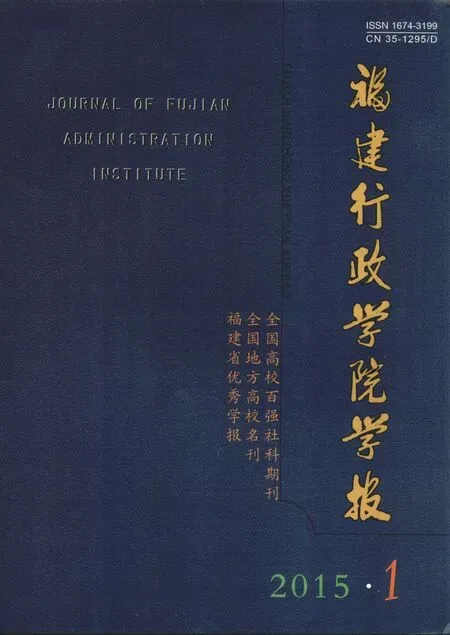合作工廠何以可能:論費孝通《江村經濟》的產權轉型實驗
李海榮
(中共中央黨校 科社部,北京100091)
“以農立國”還是“工商立國”,曾是20世紀前后困擾中國經濟轉型的根本難題之一,這與當時世界的整體格局密切相連。19世紀以來尤其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埠通商后,中國從以天朝為自居的“帝國時代”猝然進入諸國競技的“列國時代”,中華文明遭遇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它不同于以往的“一治一亂”的因循之變,而是一場大病變、一種總體性危機。因此,如何在世界新秩序中重新確立自己的位置以“保國保種”成為當時中國社會各界亟須解決的時代任務。反映在經濟建設上,便是“以何立國”之爭。
當時主張社會改良與社會建設的學者大致有兩種取向:要么“從傳統的要素中去重塑中國”,要么“從國際資本主義的擴張中去尋找中國”[1]。總體而論,費孝通在這一問題上是兩種取向兼而有之,“強調傳統力量與新的動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為中國經濟生活變遷的真正過程,既不是從西方社會制度直接轉渡的過程,也不僅是傳統的平衡受到了干擾而已。目前形勢中所發生的問題是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2]2。據此而言,中國的轉型并非全盤的西化,也不是傳統的復舊,而應是“開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3]614。
1938年,費先生利用對家鄉的調查材料寫成博士畢業論文《江村經濟》,該論文是費先生從社會學角度研究中國問題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主要探討了中國傳統生產的組織化及秩序問題,且論文的主題十分鮮明,即受西方現代工商業侵入劇烈的中國農村,手工業破產,土地權外流,傳統的農副經濟制度無法繼續支撐;而發展現代工商業成為重建農村經濟體系以致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必由之路。
一、傳統中國的產權與生產組織
費先生認為,以往爭論“以何立國”的“分歧之處是由于對事實的誤述或歪曲”,但“這不是一個哲學問題,更不應該是各學派思想爭論的問題。真正需要的是一種以可靠的情況為依據的常識性判斷”[2]4。因此,有別于以往的口舌之論與思辨之爭,在《江村經濟》中,費先生勇于拋棄一切學院式的裝腔作勢,將研究“社會事實”放在首位,用回歸事實本身的方式,科學地解釋了中國衰敗的經濟原因。
(一)“倫理所有”的產權形態
按錢穆的說法,鄉村作為人心秩序與社會體統的發源地,一直是傳統中國社會組織(包括城市、鄉鎮、山林和江湖四部分)的重心[4];梁漱溟進一步指出,“中國文化有形的根就是鄉村,無形的根就是老道理”[3]613。因此,要科學分析中國的事情,真正解決實際困難,就應將鄉村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認識老中國”,才能“建設新中國”,而“大抵社會組織,首在經濟上表著出來”[5],費先生首先考察了傳統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江村”,物的所有權劃分為“無專屬的財產”“村產”“擴大的親屬群體的財產”和“家產”四類,“個人所有權”并沒有被列出,它總是包括在家的所有權名義之下的。其中,最為關鍵的“家產所有權”,“實際表示的是這個群體以各種不同等級共有的財產和每個成員個人所有的財產”。可以說,中國傳統的物權關系是一種以“集體共意”為基礎的、能夠反映人倫關系的“家族共產”。
土地這一傳統社會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作為“家”的一種特殊所有物,它的形態也受此規范的制約。在使用權方面,土地要圍繞家族來進行,收益亦要依據家族成員來進行分配;涉及土地轉讓時,主要依照“差序格局”的原則進行,首先在族內轉讓,其次則可在征得家族成員同意的情況下實施族外轉讓;在代際分配過程中,基本按照“父系傳嗣、單系繼承”的原則,土地被一代代地劃分到接替“香火”的男性財產繼承人手中。
中國這種以家族為載體、以倫理為原則的產權組織形式,一方面降低了社會風險,增加了個人抵御社會危機的能力,進而形成了以家族為主要載體的社會照顧支持網絡。而這與西方以個人本位為基礎的產權形態大相徑庭。另一方面,盡管有人口控制的手段存在,但長此以往,個人土地的擁有量也漸漸趨向平均化,小農遍地就成為必然的結果。根據調查,“江村”極少有面積在6畝以上的地帶,絕大多數田地都在1~2畝。“狹窄的地帶和分散的地塊妨礙了畜力的使用,也妨礙了采用其他集體耕作方式。這是中國農業技術落后的首要原因”[2]141,同時也表明農業產出在“江村”已經極大化了,再在農業方面企圖增加收入已無可能。
(二)“農工相配”的經濟架構
我們再來算一筆“經濟賬”。在“江村”,職業分化程度很低,全村有2/3以上(約76%)的農業人口,而在正常情況下,單個家庭每年正常生活的最低開支中,土地收入僅占34%[2]98,145,所以,只靠農業收入不足以維持龐大的人口。在此種“匱乏經濟”情形下,一方面需要人們節省開支,養成知足常樂的節制精神,發揮文化對于消費的控制;另一方面還需要從農業之外去開源,尋求副業的支持。
盡管“自給自足”是對我國傳統小農經濟基本屬性的一般概括,但并不意味著農村社區與外界的完全隔離,而是說明鄉土社會經濟體系內部具有一定的完整性,能使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得到良性運行以達到收支平衡,唯有如此,一項社會制度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而獲得認可。
既然“江村”的農業收入有限,那么滿足當地社區正常生計的任務就要放到副業上面。除農業這一基本職業外,蠶絲業是“江村”的主要副業。據費先生統計,平均四口之家,單靠農業每年虧空約為131.6元;而當繅絲工業興旺時,除去成本一般農戶每年可盈余250元,這樣就足以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可見,“中國鄉村中工業的發達并不是偶然的。在農村經濟中工業是必要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國農業并不能單獨養活鄉村中的人口”;加之農業生產的季候性特點,使得農業與蠶絲業錯時而立成為可能,富余勞動力也得到消化。于是“中國的傳統工業,就是這樣分散在鄉村中。我們不能說中國沒有工業。中國原有工業普遍的和廣大的農民發生密切的關系”[6]4-5。這就是在傳統中國歷時彌久的農副生產相配合的經濟制度。
二、傳統經濟秩序的破壞與社會危機
自19世紀開始,中國社會便由于西方列強的進入而發生變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最初的破壞,還沒有到鄉村——無論是變法維新,或者是辛亥革命……等,都是先從上層中央政府改變起,再淺淺地間接地影響到鄉村;先從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壞起,才漸漸地延及到內地農村”[3]613。這種形勢到20世紀20年代發生了變化,鄉村的破壞也愈演愈烈,其間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入侵最為顯著,整個鄉村秩序經歷前所未有的惡劣遭遇。“驅逐農村工業的力量是有力和深入的。在它后面有軍艦和大炮的支持,‘帝國主義’是被很好地組織起來的工業國家。傳統的手工業工人是一些住在分散村莊里的農民,沒有組織歸屬感,沒有現代科學力量的幫助”[7]。這就造成“外國工業的侵入廢除了農村手工業,打亂了傳統機制”[2]79的局面。
傳統工業的收入急劇下降,借貸成為農民繼續維持生計的無奈選擇。盡管農村社區原有的借貸體系仍在發揮幫扶作用,但它“只能對付這個社區內部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不能解決普遍無力償付債務問題”[2]188,并且近年“經濟蕭條使拖欠人數增加,從而威脅著當地的信貸組織。這對現存的親屬聯系起著破壞的作用”[2]190。在這種農村金融竭蹶的情況下,城鎮資本流入農村也就成為必然。不過,由于傳統社會差序格局主導下的人際關系模式沒有改變,富于地方性的鄉土社會無力與城鎮建構起互補性的金融體系,高利貸也就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而無力還貸的農民只能出賣土地所有權,最終導致農村土地權外流,農民離地;沿海地區“80%以上的農民已經是佃農了”,“許多農民離開土地,變為沒有土地的勞動者。他們擁擠在通商口岸里,或者做工,或者當歹徒。那些留在鄉下的人掙扎著,他們面臨著高壓之下的苛刻的稅收、租息和利息。他們已到了窮途末路”[2]130;并且“是一直下去不回頭的一種鄉村破壞,鄉村純落于被破壞地位,破壞的程度日漸加深加重加速”[3]606。“農村地區工業的迅速衰退打亂了城鎮和農村之間的經濟平衡。廣義地說,農村問題的根源是手工業的衰落,具體地表現在經濟破產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問題上來”[2]198。
“19世紀的中國既受到西方經濟帝國主義的影響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8],在二者的裹挾下,中國經濟秩序首當其沖受到破壞,傳統的農副產業破產,緊跟著是君主政治的瓦解、家族治理的失序、倫理禮教的式微。費先生《江村經濟》的研究,某種程度上為我們提供了傳統中國的一些面相,揭示了傳統中國的生產組織及秩序在西方工業強勢入侵后遭受破壞的現實,同時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面臨的總體性危機。
三、“合作工廠”何以可能
總體危機需要總體改革,但“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2]199,目前,中國廣大鄉村面臨著“國內工業的衰落,高額地租的負擔使村民面臨著空前的經濟不景氣。村民難以取得貸款,或成為高利貸者犧牲品,他們的處境是進退維谷”[2]84。在沒有替代職業的情況下放棄傳統收入來源則將導致家庭收入的繼續減少。所以,“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2]201,“應當把工業引進農村,使農民能在農余時間從事工業生產”[9]。
中國傳統農副經濟的破產起于傳統工業(家庭手工業)的崩潰,但更根本的原因則是“鄉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2]200,這源于中西雙方所用“力”的不同,簡言之,可以歸結為機器動力對人力的勝利。“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0]
資本作為一種欲望體系、一種“異化”力量,發展到19世紀中葉,已經成為一種世界體系。它將世界各國,無論是工業發達國家還是經濟落后民族,都卷入世界市場之中。在這種大潮之下,世界的經濟秩序已經被資本主導,中國繼續堅持田園牧歌般的古樸生活已經不再可能;古老中華文明想在“世界列國時代”獨善其身也只能是一種幻想。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后起中國若想在世界新秩序中掙得一席之地,勢必要迎頭趕上,發展工業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農業現代化既是抗衡西方工業強國的手段,亦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內生動力所在。正是認識到這一點,費先生才著重提出從工業入手,“重組”生產秩序的方案。
但在“工商立國”的既定方針下,中國是走西方式的工業化擴張道路,還是“重組”傳統農副經濟?這是擺在社會改革者面前的一道難題。費先生給出的答案是,中國應依據傳統,生成一種新式的“鄉村工業”。
一方面,西方工業為主、都市本位的社會體制與中國農業為主、鄉村本位的文明路徑存在抵牾之處。中國都市是在外力脅迫下,首先以通商口岸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并不同于西方經濟力量在本國內部積聚-擴散的形成模式,它不是中國內部經濟力量集聚的結果。在費先生看來,“都市不只是一套建筑和街道,而是一套生活的習慣和做人的態度,有了都市的習慣和態度,這套建筑和街道才能利用來增進我們生活的幸福,不然,就會變成一個可怕的陷阱,成為人間罪惡的淵藪”[6]103-104。這從反面說明了中國工業的布局應放在鄉村。
另一方面,“新的得在舊的上邊改出來。歷史的綿續性確是急求改革的企圖的累贅,可是事實上卻并不能避免這些拖住文化的舊東西、舊習慣”[11]424。“我的另一信念是,蠶絲工業曾經是而且應該繼續是一種鄉村工業。我的理由是,如果我們把工業從農村引向別的地方,像很多工業家所做的那樣,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農民實際上就會挨餓。另一方面,我也很了解,工人們在城市里是如何生活的。農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廠去工作,掙微薄的工資,幾乎不能養活自己,她們離開了自己的家。這種過程既損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壞了農村的家庭。如果中國工業只能以犧牲窮苦農民為代價而發展的話,我個人認為這個代價未免太大了。”[2]149
退一步而言,費先生也注意到機器文明的流弊。一方面它造成了人的“異化”,使人依附于機器,容易導致個人的人格失調以及社會的波動與不安;另一方面也使人與人之間原本契洽的關系發生偏離,社區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壞,社會生活也發生了解體的現象。當然,這固然是機器文明的弊端,但并不意味著機器作為技術本身無法被利用,因為“利用機器時可以有不同的社會方式,并不是一定要西洋朋友所走過的舊路而一成不變”[6]397。換言之,技術本身可以嵌入社會結構之中,為人所用。
相較之下,中國傳統分散的手工業盡管在與機器工業競爭中式微了,但它遷就了人性,其精神應予以保存。“我們主張在舊的傳統工業的社會機構中去吸收西洋機器生產,目的就在創造一個非但切實,而且合乎理想的社會方式”[2]393。即將西方新式技術與中國傳統技藝精神融合,發展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式工業。
用技術下鄉改造傳統工業。“我們主張把機器逐漸吸收到傳統工業的社會機構中去,一方面使農村經濟得到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使農村工業因機器及動力的應用而逐漸變質”。這樣一來,既顧及到了我國原有的工業形式,又引進了現代工業的技術動力,二者的結合一方面能恢復已然式微的“鄉村工業”,對增加農民收入、安定社會秩序、以至積累發展現代工業的資本都有益處,另一方面則會使舊有的“鄉村工業”逐漸變質為現代的新式工業。
以“合作”原則組織新式工業,有別于西方資本占有的工廠形式。費先生強調“江村”合作工廠的基本原則是:合作工廠的所有權屬于合作社的社員;合作工廠成員身份的認定依據是自愿入股,成為股民便享有工廠的收益權;工廠的原料由社員供應,勞動力也來自社員。“這顯然是不同于資本主義大工業性質的工業形態,它并不是靠國家的法律強制來實現它的合法性,而是在鄉村社會靠農民的普遍承認來獲得自身的合法性;它不是掠奪農民的資源與勞動力,而是盡量從資源的最佳利用和勞動力的最佳安排來考慮;它不是要在草創階段就要千方百計地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而是要即刻挽救農村凋敝的“經濟生活。”這就是費先生于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中國經濟轉型的初步設想,即以“合作工廠”的形式融合現代產業與傳統倫理于一體,改革傳統的物權關系,構建新型的社區共同體。
四、討論與反思:現代化與文明轉型
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現代化是大勢所趨,中國作為后起國家,若要在世界體系中掙得一席之地,主動參與現代化并完成自身的文明轉型是一種必然選擇。
傳統中國作為典型的農業國,經濟轉型的實質是實現農業的產業化,“以工立國”。正如費先生所言,“現代文明來自工業,不是來自農業”,“我們必須拋棄農民思想。我的看法是除非80%在小農經營中的農民改變他們的職業,并離開在土地上勞作的老路,否則,中國將繼續顛簸難行。”因此,“我們必須走的第一步是把農民變成一個能離開土地的生產者。那意味著我們必須改變產業的結構。那時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條件才會改變”[12]。
(一)追述:“鄉村工業”的現代意義
費先生以“科學地認識中國社會”為己任,一生“志在富民”,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要走且可以走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發展路徑,力倡將中國工業化道路建立在傳統要素與現代技術之上,生成一種以“鄉村工業”為過渡產業形式,以及以農業產業化為目標的以農建工、以工補農的經濟轉型模式。
從當時鄉村建設“實驗”的立意與效果來看,費先生“鄉村工業”之于當代的學術與社會價值更顯著。費先生以合作為原則的新工廠有別于西式的資本工廠,其意圖是讓生產從家庭之中得到解放,避免“倫理”的牽扯,同時保留鄉土的倫理情感,讓經濟生產與社會生活相互契合。用現代社會學的術語說,引導工廠的經濟活動深度嵌入村落共同體的社會生活,既提升工廠的團結與活力,增強抵御經濟危機的彈性,又避免資本的剝削、人倫的衰退與人情關系的干擾,為傳統與現代的銜接奠定基礎。一言以蔽之,“鄉村工業”草創了“私人產權”與“集體共有”于一體的新型產權制度。
從歷史視野看,費先生“鄉村工業”是近代經濟轉型的一次突破,是傳統“家族共產主義”向“產業共產主義”轉型的重要嘗試,其意義重大不言而喻。然而,因戰亂與政權更替的緣故,沒能成型為真正中國特色的產權制度與產業模式。
此后,在相繼經歷人民公社、社隊工業后,中國農村又衍生出新的經濟組織方式,即“鄉鎮企業”。本質上來看,鄉鎮企業與“鄉村工業”同樣是農民集體經濟實體,是農村社區共同體為破解經濟困局,在文明轉型內生動力促動下自我創造的產物。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國基層鄉村的收入,也為工業化建設積累了資金。當然,由于脫胎于農村社區的社隊工業,鄉鎮企業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與政府色彩,產權形態也復雜多樣。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進行大規模產權改制,在催生新的產權形式的同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國家推行大城市戰略后也轉入低迷狀態。
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明確了將城鎮化而非城市化作為今后的發展戰略,突出了將圍繞“人”來推進新型城鎮化,這或許能避免新一輪的“造城運動”,亦可能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另一個拐點。
繼此之后,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在發展取向上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在農業經營體系上要“鼓勵農村發展合作經濟”,農村合作社成為新一階段農村建設的核心載體。
(二)討論:經濟秩序的重建與社會總體轉型
“秩序”與“進步”一直是社會學的中心議題,中西概莫能外。近代以來,中國努力追尋的是重建安定的社會秩序,達至國家進步,并在世界民族之林爭得一席之地。而中國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原有的組織機制在各種內外部因素的角力下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因此,重建社會秩序就成為中國完成社會轉型的關鍵一步。在社會秩序的眾多面向中,費先生最為關注的是經濟秩序的重建,畢竟生產的組織化及秩序問題,才是關乎民生的根本。就這點來看,費先生的社會學思想既抓住了時代的主題,又充滿了人文關懷。
當然,費先生也認識到,近代中國面臨的危機是一種總體性的,政治方面,帝制終結,士紳失勢,傳統的君主政治走向窮途末路;社會組織方面,傳統家族的影響力式微;文化方面,倫理禮教遭遇西方文明的強烈沖擊;經濟方面則如費先生分析得那樣,家庭手工業在西方現代工業的入侵下已然破產。就這些方面來說,中國僅僅改進技術,提高生產,只是進行經濟轉型是不夠的,中國社會需要再組織,更需要一種總體轉型。
文明轉型一方面需要社會結構的重構,另一方面需要個人人格的改變,以此消解社會與個人的罅隙,既能避免“社會”的缺席,又能防止二者之間產生斷裂。“當一種制度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時,甚至可能還沒有替代它的其他制度。困難在于社會制度是由人際關系構成的,只有通過一致行動才能改變它,而一致行動不是一下子就組織得起來的”[2]2-3。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所言,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后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制度與經濟賴以長期發展并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13]8。盡管中國的城鎮人口比重于2011年已達到51.27%[14],但“半城市化”現象仍很突出。每一類型的社會若想獲得安定的秩序與持續的進步,必定要奠基于人格系統與社會結構的完整上,而我們堅信“生活經驗促使人們轉向現代化”[13]9。所以,就此點來看,費先生提出中國要建設新式“鄉村工業”,走“工商立國”的道路,是企圖運用“工作經驗”促使中國傳統人格向現代人格轉變的一次嘗試,是將中西文化的各自優點進行綜合利用的一個嘗試;一方面著眼世界的現代化大勢,另一方面又顧及了中國文化的個性。因此,新式“鄉村工業”的建立不只涉及生產的組織化與秩序問題,亦有推動中國進行人格系統與社會結構轉型的涵義。
(三)反思:現代化與文明轉型
中國近代以來所遭遇到的危機,從經濟體系破壞始,后又蔓延到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等方面,但它并非瞬時的崩潰而是一種逐步的癱瘓,這固然是西方強勢入侵的結果,但也可就此看出中國傳統制度的堅韌。傳統中國雖然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下暫時式微了,但若以此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抹殺傳統文化的優點未免有失公允。傳統中國所孕育出的各種制度,是中華民族長期“位育”的結果,它與西方文化一起,構成人類文明的不同面相,因此并無優劣高低之分,只有文化個性之別。費先生晚年正是從這點生發出“文化自覺”概念,同時亦蘊涵了一種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
討論文化要注意國別性,經濟制度也是如此。一方面,中國傳統農副生產的經濟制度,是與傳統中國所具有的倫理禮教、君主政治、家族治理相嵌而生的,歷經兩千余年而不衰。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此種經濟制度在傳統中國具有很強的慣性,也表明它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尤其是經濟觀中的節制資本與制約精神相契合的。誠然,并不是說它就無缺點,制度運行久了難免存有流弊,技術應用的限制就是突出的一點,這也是它與西方工商業競爭失利的關鍵原因。但另一方面,西方的經濟制度雖與技術高度結合,極大激發了生產力的發展,物資豐盈的同時卻造成了欲望的無限增長,人性扭曲的同時社會也處于無序狀態。因此,中西文明互有利弊,不可簡單相較,而如何綜合二者的優點,也成為人類文明必須面對的問題。從這點來看,“中國社會變遷,是世界的文化問題”[11]312,社會轉型是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問題,也是人類文明無所遁逃的課題。正是從這點出發,費先生晚年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處世原則,寄托了費先生對世界人類文明發展前景的美好祝福。
試看今日中國工業化現狀,貫徹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無疑又走上了西方的老路,這點是費先生一輩學者竭力避免的。從更大的視野看,中華文明轉型的困局正在于在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中亦步亦趨,喪失了文明發展的自主性。而中國若訴求在西方國家構建的世界體系中找尋自己的位置,本身便是一個不可為的偽命題,在西方文化話語權下的中國現代化之路,其結果無疑是經濟上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文化上淪為小國,社會的整體轉型必然陷入茫然無序的混亂狀態之中。
“溫故而知新”,中國老一輩社會學人的智識,對當今快速轉型期的中國仍具啟發意義。中國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轉型之路,既不能固步自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在各自的文化圈中獨自打轉,亦不能盲目抄襲,生搬硬套,而應反思中西文明的利弊,綜合二者的優點,生發出一種新文化,引領人類文明走向前進。
[1]潘建雷,何雯雯.差序格局、禮與社會人格[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44-54.
[2]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2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
[4]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M].北京:三聯書店,2006.
[5]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
[6]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3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7]費孝通.中國紳士[M].惠海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8][美]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上冊[M].遲越,王紅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9]費孝通.鄉土重建與鄉鎮發展[M].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10]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12]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11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13][美]阿歷克斯·英格爾斯.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態度·行為[M].殷陸君,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