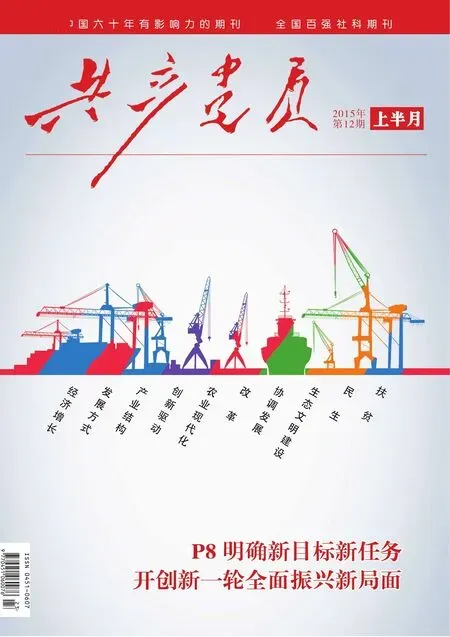再記巴彥抗日游擊隊
文/叢龍海
再記巴彥抗日游擊隊
文/叢龍海

王英超

1932年8月,巴彥抗日游擊隊攻占巴彥縣城后合影留念。前排中坐者為趙尚志
九一八事變,扯下了日本帝國主義蓄謀已久武裝侵華的面具,同時也拉開了中國人民特別是東北人民抗日戰爭的大幕。一批又一批抗日武裝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東北的白山黑水間與日寇浴血奮戰,巴彥抗日游擊隊就是其中一支著名的抗日武裝力量。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今天,再度記述巴彥抗日游擊隊的感人事跡,是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
響應黨的號召學生投筆從戎
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就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的宣言》,號召人民群眾武裝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其中,尤以在關內讀書的東北籍學生最為活躍。同時,黨更加認識到發展東北抗日武裝力量的重要性,向東北派遣大批干部,積極組織抗日武裝斗爭。
1932年4月,清華大學學生張甲洲得到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的支持,帶領中法大學法學院學生夏尚志、中國大學學生張清林、北平師范大學學生張文藻、清華大學學生于天放(于九公),以及在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留學、因抗議日本侵略東北而回國的鄭炳文,一行六人化裝成商人到達哈爾濱。當時,中共滿洲省委駐在哈爾濱。由于張甲洲在東北做過國際工作,很快就與滿洲省委取得聯系。滿洲省委經過研究,指示他們到張甲洲的老家巴彥組建抗日隊伍。
到達巴彥后,幾人立即開始著手組建隊伍。張甲洲利用自己在家鄉的社會關系,采取半公開的形式,重點爭取民團等地方武裝,同時動員士紳,積極聯絡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和工作,1932年5月16日,張甲洲等人在七馬架屯集合人馬,公開宣布成立抗日游擊隊,根據當時地方抗日隊伍的習慣,報號“平洋”,即平滅東洋鬼子之意。
實行抗日義舉隊伍發展壯大
巴彥抗日游擊隊組建之初,只有200人左右,步槍20多支,但由于隊伍高舉抗日大旗,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持。巴彥抗日游擊隊打出了這樣的口號:“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肯打日本都歡迎。”如此一來,不僅知識青年積極響應,更多來自鄉村的農民,城市的普通市民、工商業者、士兵和其他各色各樣的人物,為了抗日救國走到了一起,巴彥抗日游擊隊的隊伍迅速壯大。
隨著游擊隊的發展壯大,對于隊伍的管理和領導就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1932年8月中旬,中共滿洲省委派趙尚志(化名李育才)到游擊隊中工作,建立起以張甲洲為司令,趙尚志任政治部主任兼參謀長的司令部。滿洲省委又委派吳福海以滿洲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兼任游擊隊的黨代表。
張甲洲和趙尚志配合默契,致力于擴大這支抗日隊伍。他們堅持執行游擊隊建立之初制定的“反日大同盟”政策,吸納各個階級和民族的人員共同抗日救國。同時,他們充分認識到槍支和馬匹的重要性,隊伍每到一處,就向當地百姓進行抗日宣傳,動員說服地主有錢出錢、有槍出槍,還教育、改造落草為寇的土匪。這種做法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游擊隊很快發展壯大到600多人,變成騎兵大隊。另外,在趙尚志的建議下,在隊伍中挑選了一批品行好、年紀輕、身體素質好的小伙子,建立了模范隊。要求模范隊的隊員不準說黑話,不準損害群眾利益,必須起帶頭作用,為整個隊伍樹立榜樣。通過模范隊的帶動,整個隊伍的紀律更加嚴明,風氣更加良好,也使得游擊隊得到了更多人民群眾的支持。
聯合抗日力量攻取巴彥縣城
1932年7月7日,日軍占領了巴彥縣城,并扶持組建了偽政權。而此時,游擊隊力量尚薄弱,還無法與日偽勢力正面作戰。于是,張甲洲等研究決定將隊伍帶到巴彥西部地區,在外圍對敵作戰。
經過休整和準備后,游擊隊于7月16日對敵偽勢力占據的龍泉鎮發起進攻。龍泉鎮有警察所、自衛團等百余人的武裝,鎮上還有炮臺。作了充分準備的游擊隊采用智取配合強攻的策略,經過一上午的戰斗即攻入鎮內,繳獲百余槍支。游擊隊進鎮后,立即進行抗日宣傳,吸收人員擴充隊伍,同時對地主、富商進行說服教育,獲得了不少馬匹、子彈,增強了游擊隊的戰斗力。
經過幾次外圍戰斗,游擊隊實力擴充,力量增強,張甲洲等研究后決定對巴彥縣城采取行動。為了有力打擊敵人,游擊隊采取聯合友軍共同抗日的策略,聯系了在巴彥、呼蘭一帶活動的馬占山舊部才洪猷帶領的300余人的“才團”,又聯絡了“綠林好”率領的200余人的隊伍,共同攻打巴彥縣城。8月30日,游擊隊、“才團”和“綠林好”分別從三面對巴彥縣城發起攻擊。巴彥城內的偽軍、自衛團潰不成軍,抗日隊伍順利攻進巴彥縣城,駐守縣城東北的偽軍步兵營營長沈某被當場打死,偽縣長程紹濂化裝逃跑時被俘。三支隊伍進城后,嚴令士兵遵守紀律,不許騷擾百姓、搶掠財物,同時立即開展抗日宣傳,還開倉放糧,賑濟貧民。城內秩序井然,群眾反日情緒高漲,很多青壯年紛紛要求參加抗日隊伍,游擊隊力量進一步擴大。
進駐縣城一周后,才洪猷打算收編游擊隊,但游擊隊堅持在黨的領導下“獨立自主”,主張的是“聯合”而不是“附和”,所以經過商量,游擊隊撤出縣城,返回洼興橋一帶進行整頓,準備投入新的戰斗。
襲擊日本鐵路打擊日偽氣焰
1932年中秋節前夕,游擊隊獲悉呼蘭境內的康金井車站有日軍進駐,決定夜襲康金井車站。然而,當部隊行進到康金井站,并按照作戰計劃布置就緒后,卻發現站內并沒有日本兵。原來,車站確實來過十幾個日本兵,他們怕天黑后遭到襲擊,已經跑到綏化縣城去了。雖然夜襲康金井站沒有什么戰果,但對于鼓舞戰士們作戰的勇氣有很大幫助,也為后來游擊隊襲擊日軍鐵路進行了演練。
當年任巴彥游擊隊中隊長的王英超在其回憶錄中記述:“我們攻打下了巴彥縣城后,我帶隊到呼蘭北,扒了兩次鐵道,以阻止日寇軍車通行,又到泥河車站用炸藥炸毀了日本軍車。”另外,日偽時期的《濱江日報》報道過兩則日軍裝甲列車被顛覆及鐵甲車被炸的消息。一則報道是1932年10月12日,報紙上記載:日軍乘坐裝甲列車前往呼蘭、綏化等地討伐“匪賊”,然而裝甲列車行駛途中被“顛覆”,列車脫出軌道損壞,日軍特務曹長頭部撞傷,日軍只好偃旗息鼓,將列車修好后開回呼蘭。另一則報道記載:一輛由呼蘭開往綏化的鐵甲列車行駛到康金井站附近時,被“匪賊”事先埋在鐵道下面的炸彈炸壞,有一人受傷。
隊伍轉戰各處最終無奈解散
1932年9月,游擊隊從南、北、西三面合圍,攻入巴彥東北的小城東興鎮。原盤踞在東興鎮的敵人不甘心失敗,勾結其他一些反動武裝,糾集了1000多人大舉反攻。戰斗打得十分激烈,趙尚志、第二大隊長夏尚志等人受傷。游擊隊為保存實力,避免重大傷亡,決定暫時撤離東興鎮,回到姜家窯一帶休整。
游擊隊撤出東興鎮后,滿洲省委指示將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六軍江北獨立師,確定此后重點活動在松花江以北地區。隊伍遂以安達、拜泉等縣為目的地向西進發,打算與在該地活動的李克成、鄭炳文(巴彥游擊隊組織起來后回家鄉拜泉組織游擊隊)等會師,便于聯合西部地區的李海青、鄧文等抗日武裝共同抗日。同年12月初,隊伍行進到肇東、安達、明水、林甸、依安等縣時,打擊了此地重新冒頭的親日派漢奸和反動勢力,開展了廣泛深入的抗日宣傳和組織活動,撲滅了反動勢力的氣焰,擴大了抗日救國的影響。
1933年1月,游擊隊又揮師北上。但是,越往北,反動勢力越猖獗,給游擊隊帶來非常大的困難。由于沒能和李海清、鄧文等部會合,游擊隊又決定繼續東進,向湯原一帶進發。在經過綏棱一撮毛地方時,游擊隊經過十幾天的苦戰,才擺脫了偽山林隊“索利營”的糾纏,繼續向湯原行進。
經過連日戰斗,游擊隊隊員傷病增加,加上此時正值農歷年底,很多戰士在惡劣環境的影響下,更加思鄉心切,導致游擊隊連受軍事危機和政治危機雙重打擊。1933年1月18日,游擊隊行進到綏化黑山縣,隊伍即行解體,巴彥抗日游擊隊解散,領導骨干數人回哈爾濱聽候組織安排。
巴彥抗日游擊隊從成立到解散,僅8個月的時間。雖然存在的時間很短,但游擊隊踴躍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敵人屢次作戰,打擊了敵偽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而且,游擊隊積極宣傳抗日救國思想,發動人民群眾保家救國,對東北抗日形勢的高漲帶來積極影響。另外,游擊隊聯絡各種抗日武裝力量,建立“反日大同盟”,在實際中超前運用了抗日統一戰線,也對此后的抗日戰爭形勢有著深遠的影響。
□本欄編輯/牛澤群
本欄目與遼寧省檔案局(館)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