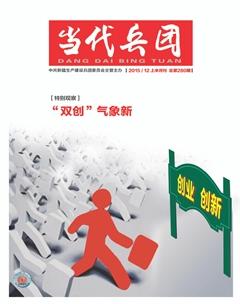情滿新疆
吳愛平 郭芳 李芳宇 葉石界
從喀什驅車300多公里,沿著塔克拉瑪干沙漠西北邊緣前行,來到三師五○團。2010年8月,廣東東莞援疆干部第一次抵達團場時,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感覺回到幾十年前,當地一盞路燈都沒有,到了晚上一片漆黑”。
五○團所在的三師、圖木舒克市,是共和國最年輕的城市之一。2004年,圖木舒克市正式掛牌成立。然而,直到2010年,這里的城鎮規模還遠遠趕不上東莞的大多數普通村鎮。
“當時整個市區面積只有七八平方公里,不到半個小時就能走遍。” 圖木舒克市副市長羅后盾出生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是典型的“兵團第三代”。他向記者回憶道,市區僅有七八條道路、零零星星的十幾棟樓房,“毫無城市的模樣”。
在新一輪的援疆建設中,首次將特殊體制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納入其中。5年前,三師、圖木舒克市成了廣東對口援建點。面對“一年365天有100天是浮塵天氣”的自然環境和連路燈都沒有的一片空白,廣東援疆干部如何在戈壁灘上,與三師、圖木舒克市攜手建起一座美麗的新城?
“千年沉睡古城”的等待
圖木舒克,這座成立僅十來年的城市,在3400多年前就有人居住,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
早在西漢時期,圖木舒克是西域36國之一的尉頭國所在地。公元75年,東漢班超率吏士36人赴西域,在圖木舒克山麓磐橐城(維吾爾語稱為“托庫孜薩來古城”,意為“九座宮殿”,后稱為唐王城)駐守17年。
然而,這座千年古城的輝煌在歷史中早已灰飛煙滅。如果沒有三師的駐扎,“圖木舒克”的名字也許會像新疆其他古地名一樣,逐漸湮沒。
三師的劉開發今年已經74歲高齡了,在上個世紀60年代跟隨部隊進疆,開荒種地。在第三師的檔案館里,一張張有著年代感的泛黃黑白老照片,記錄下當時兵團創業的激情歲月。
“最忙的季節,從早上3點半爬起來干活,一直忙到晚上9點半才收工。一個夏天就瘦了7公斤。”回望50多年前的歷史,劉開發興奮得兩眼放光,“當年硬是在荒漠里開墾出一塊塊土地。”
“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三師就已經擁有先進的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大型機械,在全國農業領域是數得上的典型。”早在孩提時代,羅后盾就聽慣了父輩們所創造出來的兵團最輝煌的歷史。
然而,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和兵團大多數團場一樣,圖木舒克慢慢陷入了發展的沉寂。“圖木舒克的經濟收入,大部分來源于種植棉花、蘋果、紅棗等農業。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工業發展一直停滯不前。當地唯一的一家電器廠,就是手電筒廠。”羅后盾的語氣有些無奈,直到2004年建市,圖木舒克一年的地方財政收入僅有1400多萬元。
經濟發展舉步不前,使得城市建設遙遙無期。以五○團為例,2010年前,團場僅有的一條馬路不足1000米,始建于上世紀90年代初,因年久失修,早已傷痕累累。“老軍墾”心酸地回憶道:“以前開拖拉機去20公里外的圖木舒克,根本不用手握方向盤,因為泥路已經形成很深的兩條溝渠。”
久遠的歷史長河中,圖木舒克曾經是西域繁華的“城郭之國”。這座沉睡了千年的古城,能否得到重生?
告別“沙窩子”“土塊房”歷史
1900多平方公里的圖木舒克,分布著16萬多人口,其中60%左右是少數民族。
圖木舒克面臨的城市化問題,在喀什地區具有典型性。由于經濟落后,很多地方仍然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模樣。
在戈壁灘上建起一座漂亮的新城,并非易事。“廣東援建不能搞花架子,要從解決當地老百姓最迫切的需要出發。”廣東援疆前方指揮部副總指揮,東莞市政府黨組成員,三師、圖木舒克市黨委常委、副師長黃少鋒表示。
劉開發講述了他的住房變遷史,代表了各族百姓的心聲。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部隊進入墾區,望過去是茫茫荒原。“創業之初,兵團職工住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地窩子。” 劉開發回想起當年的艱苦歲月,感慨不已。所謂地窩子,就是挖個土坑,鋪上樹條或葦把,然后糊上一層厚厚的草泥。“這個簡陋的窩棚,算不上真正意義的房屋”。
劉開發一家五口人擠在10多平方米的“地窩子”里。每年春秋,來自西伯利亞的狂風猛烈而頻繁。漫天黃塵呼呼地往地窩子里灌,鼻孔、耳朵里都灌滿了塵土。“后來條件好些,才慢慢住上土塊房”。
直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劉開發住進了四五十平方米的磚瓦房。遠離故土、扎根南疆50多年,劉開發三年前搬進了廣東對口援建的安居房。“感謝廣東無私的援助,讓我們過上像城里人的生活。這是我一輩子都沒想到的。”
告別“沙窩子”“土塊房”的歷史,讓各族職工群眾的幸福指數瞬間“爆表”。
56歲的亞生·司馬義,是五○團一中的退休教師。之前,他們家六口人住在有著30多年歷史的土塊房里,屋頂是用當地隨處可見的野麻鋪就的。每到下雨或是刮大風,一家人就憂心忡忡,擔心房子一夜之間倒塌。兩年前,亞生·司馬義住進了安居房。“115平方米的新房,各級政府補貼了3萬元,自己只花了9萬多元。”他感慨道。
搬進樓房,也給各族職工群眾帶來了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以前的土塊房沒有廁所,有的只能在荒地里挖坑解決。每到寒風凜冽的冬天,哆哆嗦嗦地上廁所是最痛苦的事情;以前的房子臟亂得很,吃飯時蒼蠅嗡嗡地亂飛,都害怕蒼蠅掉進碗里。”而現在,亞生·司馬義再也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了。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喀什地區,這樣的住房變遷史,不僅發生在圖木舒克市,還發生在喀什的伽師、疏附等地。
“十二五”期間,廣東援建安居富民房85322套,每套補助援疆資金1萬元,共補助8.53億元。以伽師縣為例,當地一半以上的各族百姓都住進了安居房。
越來越有珠三角城市的影子
羅后盾對珠三角并不陌生,他曾經在廣州市海珠區政府部門掛職1年。廣州等珠三角城市繁華的摩天高樓、濃厚的文化氣息、國際化的形象,讓從小生活在新疆的他羨慕不已。
東莞援疆干部來了之后,給圖木舒克帶來了難以想象的變化。“2010年之前,圖木舒克由于財政資金捉襟見肘,投入的建設資金總共不到2億元,這對于城市建設無疑是杯水車薪。這幾年時間里,圖木舒克投入了47億元,用于城市供水、供暖、道路等建設。”羅后盾比劃道,“這是原來的20多倍。”
5年時間里,圖木舒克不再是過去荒蕪的“土窩子”“野麻地”。除了寬闊的道路、漂亮的綠道、整齊的路燈,圖書館、博物館等城市配套就像搭積木般迅速建設起來。這讓人很難相信,在戈壁灘上還有這樣現代化的城市。“圖木舒克就像是戈壁灘上的綠洲,越來越有珠三角城市的影子。”羅后盾告訴記者。
城市公共服務的配套,也改變了過去各族職工群眾的生存環境。毫不起眼的氣象臺,卻是影響民生的大問題。“殘酷的沙塵、冰雹等,有可能使得幾百畝甚至上萬畝的棉苗被冰雹打掉、被風沙淹沒,斷職工群眾全年的收入。”中山援疆干部、圖木舒克市氣象局副局長夏冠聰說。
“以前沒有建氣象局時,各團場只能靠肉眼‘望天打卦,提心吊膽地將高射炮架在車上,隨時隨地跟著云層跑,射擊冰雹,但往往事倍功半。”夏冠聰表示,氣象臺建設,進入廣東援建工作隊的視野。圖木舒克有了“氣象千里眼”,直接減少了災害天氣帶來的危機。
與此同時,援疆帶來的不是簡單的建筑,更是改變了各族職工群眾的生活理念。圖木舒克市援疆辦副主任劉曄向記者舉例道,大城市里隨處可見的圖書館,對于曾經的圖木舒克而言都是奢望。就連老師緊缺的參考書,也需要到兩三百公里之外的城市購買。“圖書館即將完工,再也不用往返六七個小時跑到外地去買書了。”他說。
美麗的新城,留住了當地人才的腳步。
25歲的姑麗努爾·沙吾提,她的奶奶是五○團的第一代開荒者。和很多“兵團第三代”一樣,她也曾猶豫不決,是否要離開這塊凋敝的土地。“2011年暑假回家,發現在轟隆隆的機器聲中,城市變化得太快、太美了,差點找不到回家的路。”姑麗努爾·沙吾提大學畢業后選擇了留守,成為五○團電視臺的播音員。
圖木舒克實現了戈壁起新城的人間奇跡,這也是廣東民生援疆的縮影。
輸血,還是造血
喀什,古稱“疏勒”。
2000多年前,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辟了橫貫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作為古代絲綢之路的交通重鎮,喀什一直是客商云集的國際商埠。絲綢、茶葉等貨物,從這里源源不斷地運往中亞、歐洲等國家。
然而,昔日的絲路繁華,在歷史中早已灰飛煙滅。喀什漸漸陷入發展的沉寂。和萬里之外繁華的珠三角城市相比,落后的喀什仿佛身處另一個世界。兩地巨大的經濟發展差距,在廣東援疆干部的腦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39歲的黃漢云是一名典型的珠三角基層干部,曾先后擔任佛山市三水區樂平鎮副鎮長、南山鎮副鎮長。一年前,黃漢云跟隨廣東援疆隊伍入疆,擔任駐伽師縣工作隊產業就業組副組長、伽師縣經信委副主任,負責招商引資等工作。
“珠三角密密麻麻地分布著數以萬計的企業,僅樂平鎮就有600多家企業。而伽師縣的企業,去年加起來也僅有40多家。”伽師經濟之落后,讓黃漢云唏噓不已,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伽師縣的經濟發展尷尬,在喀什地區有著普遍性。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和兵團大多數團場一樣,三師、圖木舒克市慢慢陷入了發展的沉寂。“圖木舒克的大多經濟收入,來源于農業。”廣東援疆干部、圖木舒克市副市長劉建俊告訴記者。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圖木舒克工業發展一直停滯不前,零零星星地分布著工業軋花廠、榨油廠等小企業。當地唯一的一家電器廠,就是手電筒廠。”劉建俊的語氣有些無奈,“直到2010年,圖木舒克當年的GDP僅有38.6億元。”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喀什地區有著16.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這幾乎快趕上廣東的面積。然而,在2010年廣東援疆移師喀什之前,喀什的GDP僅有326.4億元,這個數字甚至趕不上珠三角一些經濟發達鎮。當地大多數老百姓依靠種田、放牧為生,過著年人均純收入3270元的貧困生活。
靠什么徹底改寫喀什貧窮落后的歷史?援疆的歷史抉擇,將遠隔5000多公里的喀什與廣東緊緊相連。廣東與喀什,一個是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東莞一塞車,全球電腦市場就缺貨”,是對繁榮的珠三角制造業最形象的描述;一個是閉塞落后的西部邊陲,等待著重現歷史的昔日繁華。
“與其進行輸血式的經濟援助,不如實行造血式的產業援助。”廣東對口援疆前方指揮部總指揮、喀什地委副書記方利旭表示,如果把廣東的優勢產業與當地的資源優勢相結合,把產業援疆與廣東的優秀企業拓展市場相結合,將給喀什的經濟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
用“廣東速度”書寫喀什歷史
廣東的產業援疆,正在改寫喀什貧窮落后的歷史。
方利旭告訴記者,據不完全統計,這5年時間,廣東共安排26.8億元財政資金投入產業援疆,引薦2400多家企業到新疆考察交流,全疆簽約、落地項目447個,計劃投資1918億元,實際到位資金459億元,帶來將近10萬人的就業機會。
2010年以前,喀什工業薄弱,沒有太多像樣的本地企業。“十二五”期間,廣東共投入援疆資金15億元,支持新建或重新規劃建設了疏附商貿城、疏附工業城、伽師工業園、圖木舒克市工業園、兵團草湖工業園等園區,受援地工業園區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轉變。
產業園由“紙上”正式落到“地上”。黃少鋒向記者講述道,2014年6月,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省長朱小丹率黨政代表團到三師、圖木舒克市考察,召開對口支援兵團工作座談會,確定了打造草湖200萬錠紡織服裝產業園的宏偉構想和藍圖。
距喀什城外23公里處,一場新的“工業革命”正拉開帷幕。這里是10平方公里的草湖產業園,廠房正迅速拔地而起。
“草湖產業園建成后,將成為全國一流、世界先進的紡織業基地,預計將產生超200億元的GDP,而整個三師、圖木舒克市去年GDP才近百億元。一個草湖產業園的問世,就等同于再造一個三師、圖木舒克市。更為重要的是,產業園能帶動5萬名勞動力就業。” 在黃少鋒看來,草湖不僅將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產業重鎮,還將成為產城融合的典范。
國家批準設立喀什經濟特區,廣東對口援疆的腳步越走越快,這個“五口通八國”的祖國西大門開始發力了。廣州新城、粵豐國際家具批發城、阿凡提樂園、嘉納仕摩托車、中廣核、廣新紡織、東純興紡織、美奧塑料、絲路電商、思科電子……數量眾多的重量級產業項目落地生根,給當地經濟注入了強勁的發展動力。
5年時間里,喀什正在發生歷史性的深刻變化。喀什的GDP由2009年的326.4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688億元;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由14.7億元增加到63.68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由207.8億元增加到702.68億元。
記者從這三組跳躍式的發展數據中,讀出了喀什的發展希望。
(題圖:吳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