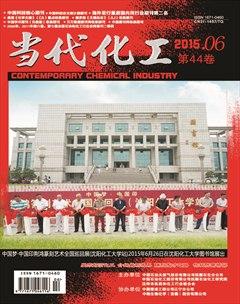煤熱解過程中S、N與礦物質作用情況綜述
何璐 趙夢祎 彭勃
摘 要:簡要介紹了礦物成分、S和N在煤中的賦存形態,詳述了煤熱解時S、N析出的形態以及礦物質和S、N相互作用的研究進展,并指出應加強煤熱解過程中S、N和礦物質作用機理的研究,以促進煤的清潔利用,減少環境污染。
關 鍵 詞:煤熱解;礦物質;S、N;相互作用
中圖分類號:TQ 5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0460(2015)06-1374-03
Discussion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N and Mineral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al Pyrolysis
HE Lu, ZHAO Meng-yi , PENG Bo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China)
Abstract: Forms of occurrence of S/N and mineral in coal were introduced, and forms of precipitation of S/N during the coal pyrolysis were expressed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ineral and S/N. It was also pointed out that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neral and S/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lean utilization of coal and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Key words: Coal pyrolysis ; Mineral; S/N; Interaction between S/N and mineral
眾所周知,煤炭在我國的能源結構中居于十分關鍵的位置,而且在未來可預見的一段時間里其位置是不可替代的。然而煤燃燒的揮發分產物中有大量含S、N的化合物,嚴重危害生態環境和生物健康。而且已有研究表明,熱解時煤中S、N分配與礦物組分緊密相關,這不僅為今后清潔利用煤炭資源提供了依據,也使對熱解時煤中礦物質和S、N之間作用的深入研究具有更重要意義。
1 煤中S、N及礦物質賦存形態
1.1 煤中S的賦存形態
硫含量因煤的類型不同而差異較大,含量從0.2%~11%不等,與煤的煤化程度深淺沒有必然聯系;而我國的煤含S量為0.04%~9.62%,大多數處于1%左右,約30%的煤其含S量高于2%。
一般地,從宏觀上講S在煤中有機S和無機S兩種存在形式。有機S存在形式比較復雜,主要影響因素為煤化度,當煤化度較高的時候,分子量較高的環狀有機硫在煤中占的比例較大,當煤化度較低時,分子量較低的脂肪類有機硫成為有機S的主要存在形式。而相關的研究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1]。無機S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鹽硫(Ss)和硫化物硫(Sp),礦物的硫化構成硫酸鹽硫(Ss)和硫化物硫(Sp)的主要來源,煤中含有的微量單質S一般被認為是黃鐵礦經過硫風化而形成的[2,3]。黃鐵礦是硫化物硫(Sp)的主要構成成分,除此之外還有磁鐵礦(Fe7S8)、閃鋅礦(ZnS)、磁鐵礦(Fe7S8)等;硫酸鹽硫(Ss)的主要構成成分為石膏(CaSO4?2H2O),同時伴有少量的綠礬(FeSO4?7H2O)等。
1.2 煤中N的賦存形態
煤中N的含量為0.3%~3.5%,處于1%~2%之間較多。一般情況下,有機煤N多與芳環結構相連,其中吡咯型N含量最高,為N總量的50%~80%;其次是吡啶型N,其含量0%~20%左右;最后是季氮,含量為0%~13%[4]。含N官能團有多種多樣,目前,專家定義了季氮(Quatemary)、氮苯(Pyridinic)和氮茂(Pyrrolic)為最關鍵的含N官能團。
1.3煤中礦物質種類及特性
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礦物質,無機化合物的總稱,主要包含Si、Al元素,也有Na、K、Ca、Fe、Mg等元素,同時還包括一些無機元素(單獨離散或與有機物結合)。其中,礦物組分大致可以分為五種,分別為硅酸鹽礦物質(如CaSiO3、黑云母)、粘土礦物質(如Al2Si4O10(OH) 2?H2O、伊利石)、碳酸鹽礦物質(如霰石CaCO3)、硫酸鹽礦物質(如石膏CaSO4?2H2O)、硫化物礦物質(如黃鐵礦FeS2)等。而以無機物形式存在的元素多和有機物相互結合,形成鈉、鉀和鈣等的羧基鹽。
2 熱解過程中S的遷移及與礦物質的作用
2.1 熱解過程中S的遷移
煤熱解時S遷移是個極復雜且重要的過程,影響因素也很多。煤熱解時各類含S化合物隨溫度升高逐漸分解,熱解所得各種含S化物向煤氣、焦油及半焦中遷移。300 ℃左右,脂肪硫燃燒;400 ℃左右,黃鐵礦S和芳香S中C-S鍵會發生斷裂;500℃以上,雜環噻吩型S化物開始燃燒;590 ℃以上,硫酸鹽S才開始釋放。
(1)S在揮發分中的存在形態
一般認為,COS、CS2、H2S和SO2為煤熱解時候所釋放的S的四種存在形式,H2S是硫鐵礦S和脂肪族S分解形成的,其是一種揮發性的含S化合物。隨著煤熱解的升溫,硫化物首先反應生成自由基,隨后和H原子反應生成H2S和烯烴。當溫度升至200 ℃的時候H2S逐漸析出,H2S的析出速率最大值出現在500~600 ℃左右,且一直保持到900~
1 000 ℃。
H2S是煤熱解時候所釋放的S最主要存在形式,SO2、COS和CS2含量較小,COS和CS2受到煤階和黃鐵礦的影響。低階煤更易形成COS、CS2;黃鐵礦減少,COS、CS2的量減少。已有相關研究證明,在高濃度的揮發分里,甚至在較低溫度250~300 ℃,FeS2即可釋生成FeS放出CS2氣體。而當溫度升至800 ℃以上時,FeS2開始與烴(如甲烷)反應,在消耗一定量H2S的同時生成CS2,并且隨著溫度的升高CS2的生成量也越多。熱解時S和CO結合形成COS。少量的SO2則可能來自高溫下硫酸鹽(Ss)或者砜的分解。
(2)S在半焦中的存在形態
現在普遍認為,半焦中S的存在形式主要為CaS、FeS和MgS,且查普利的研究顯示,含S的官能團是半焦里S存在的主要形態,分別為:芳香型含S化合物、非揮發性的無機含S化合物以及縮合程度較高的平面噻吩,這些化合物中的S和煤中的C以C-S鍵的形式結合,形成穩定的有機物。劉艷華等[6]有研究表明,一些燃料S以硫酸鹽或亞硫酸鹽的形式殘留于半焦中的。
2.2 熱解過程中礦物質對S遷移的作用情況
(1)熱解時CaO與S作用機理
經過不斷的研究,最終證明CaO與S的反應分為兩個步驟[5,6]:第一步,CaO與含硫氣體發生化學反應,如式(1);第二步,在第一步進行到一定階段后,產生的CaSO4會形成一層“保護膜”阻隔了含硫氣體與CaO分子的接觸反應,這種情況下進入第二階段,即Ca2-和O2-開始向CaSO4表層擴散,并與含S氣體作用[7,8],如式(2)。
CaO+SO2+(1/2)O2→CaSO4 (1)
Ca2-+O2-+SO2+(1/2)O2→CaSO4 (2)
CaO與S的反應過程中包含有極其復雜的氣體擴散與表面反應之間的相互耦合[9,10]。該反應遵循大部分氣固反應的規律,反應速率以及轉化率的大小都由固體物的孔隙結構決定[11,12]。
(2)熱解時CaO /Fe2O3與S作用機理
楊立寨等[13]發現,Fe2O3在200~700 ℃與SO2不發生反應,并且大量研究數據顯示,當煤中存在氧化鐵時,可以催化CaO與S反應。原因在于,Fe2O3能阻止CaSO4形成致密的“保護膜”,使得固體物的孔隙結構不會發生巨大的改變,從而使得硫化反應更快速的進行。
用純CaO進行脫硫反應時, SO2會氧化生成SO3,再與CaO結合,最后反應生成CaSO4,如式(3)。
CaO+SO2+(l/2)O2→CaO?SO3→CaSO4 (3)
當放入催化劑氧化鐵時,二氧化硫分子和氧氣分子會在氧化鐵的催化作用形成SO3,SO3再與Ca(OH) 2反應生成CaSO4,完成這兩個過程后,該反應的活性在下降的同時,反應率和轉化率得到相應的提高了。反應過程如式(4)和(5)。
Ca(OH)2+Fe2O3+SO2+(1/2)O2→Ca(OH) 2+ Fe2O3?SO3 (4)
Ca(OH)2+Fe2O3?SO3→CaSO4+Fe2O3+H2O (5)
普遍認為在脫硫的反應過程中,SO2氧化成SO3是反應比較緩慢的一步,即是控速步驟,當加入Fe2O3粉后,催化作用使得該控速步驟反應加快,從而使得硫化反應整個過程加快。
3 熱解過程中N遷移及礦物質的作用
3.1 熱解過程中N的遷移
煤在熱解過后會形成焦油、半焦和熱解煤氣,而N則以不同的化合物形態存在其中。留在半焦中的N占30%~50%,釋放到煤氣中的N有10%~20%,而以凝聚態存在于焦油中的N占10%~15%。
(1)揮發分中N的存在形態
煤氣中N的主要存在形式為HNCO、HCN和NH3等,當與氧化劑(如羥基自由基)接觸時可反應生成NOx,也可以與NOx進一步反應生成N2。Li等人[14]發現,煤熱解時,N最初形態為HCNO,接著HCNO又作為熱解前驅物,經過一系列的化學反應生成NH3和HCN,最終產物中的NH3等于反應過程中NH3和HNCO的總和。
HCN是煤熱解生成的物質里最主要含N化合物,并且HCN生成量與煤熱解時的溫度呈正相關;不僅如此,NH3生成量與煤熱解時的溫度也是呈正相關,但是不同的是,850 ℃是NH3生成量最多的溫度,當溫度高于850 ℃,NH3生成量開始下降。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觀點為,HCN為煤快速熱解的產物,而煤慢速熱解時NH3在產物中占有相當大比例[15]。并且煤階與HCN生成量有直接關系,HCN生成量隨著煤階升高二減少,并且當煤熱解時,部分HCN也會形成NH3。HCN和NH3的大部分是揮發分二次反應產物。
目前,人們對N在煤焦油中的存在形態看法不一,主要有兩種觀點:①N從原煤進入焦油中后,其形態沒有發生變化;②焦油中吡啶N、吡咯N的相對含量和原煤不同,而且季氮已經不存在與焦油中。
(2)半焦中N的存在形態
季N、吡啶N和吡咯N在N的半焦形態中也是存在的,并且結構相對更加穩定。經過實驗表明,半焦中N的存在形態受溫度影響很大,用XPS對氮官能團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季氮的完全降解溫度是1218K;吡啶型N的分解量則與溫度呈正相關,1488K時其分解量可達50%~80%;當溫較高時,不夠穩定的吡咯型N會向更為穩定的吡啶型N轉變,最后隨熱解溫度進一步升高,全部吡咯N都可形成吡啶N。
3.2 熱解過程中礦物質對N遷移的影響
(1)熱解時煤原生礦物質對N遷移的作用
Wu Z[16]、 Ohtsuka Y等提出如果忽略煤中孔隙結構的影響,脫除煤的礦物質再對煤進行煤熱解,其產物的結構發生了變化,最明顯的變化就是N2峰值轉化率溫度區間的變化和N2量的減少以及焦氮含量的增加,但焦N所增加的量不足以彌補減少的N2量。而針對熱解制焦過程來講,整體流程依然是隨著反應的進行,焦氮會減少,N2會增多,但與原煤的反應相比,N2量呈明顯下降趨勢。又有關于低階煤熱解的研究表明,煤在脫除礦物質以后,揮發分中的氮結構、含量等基本不變,但NH3、N2產率相對大大減少,NH3的釋放溫度得到很大的提高。
(2)熱解時添加物Ca對N遷移的作用
Ohtsuka Y等[17]研究發現,在450~600 ℃的溫度下,外加的NaOH、KOH和Ca(OH) 2可以促進脫除礦物質的煤熱解時NH3的釋放,抑制HCN形成,其中Ca作用最為明顯。Wu Z、Tsubouchi N等[18]研究發現,煤熱解時,Ca可抑制N進入到焦和焦油中,從而對N2和NH3的形成起到催化作用,但在1000℃以下事Ca對N2形成是抑制作用。
(3)熱解時添加物Fe對N遷移的作用
Mori H等[19]在研究中都發現了Fe可以在煤熱解過程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在900℃的試驗溫度下,低階煤熱解,添加Fe催化劑與否是唯一變量,結果顯示與原煤熱解相比,NH3、HCN以及焦N量有所減少,而N2含量相應增多,但揮發分中總N含量在降低;之后模擬反應證明:煤熱解時,Fe可以改變N在產物中的分配,抑制HCN生成,把焦N轉化為N2,從而使N2含量升高,焦N含量降低。
4 結 論
(1)煤熱解過程中,其原生礦物質以及外加礦物質對S、N的遷移具有一定程度的催化作用,且其作用機理各有不同,加強不同種類礦物質和 S、N作用機理的研究,對煤炭清潔利用具有重要意義。
(2)巧妙利用煤原生礦物質對S、N作用機理,改變NOx、SOx的分配方式,以達到清潔燃煤的目的,這也是煤轉化為清潔能源的一種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孫成功,李保慶.煤中有機硫形態結構和熱解過程硫變遷特性的研究[J].燃料化學學報,1997,25(4):10-20.
[2]李瑞.中國煤中硫的分布[J].潔凈煤技術, 1998, 4(1): 44-47.
[3]高連芬,劉桂建, Chou Chen-lin,等.中國煤中硫的地球化學研究[J].礦物巖石地球化學通報, 2005, 24(1): 79-87.
[4]劉艷華,車得福,徐通模.利用X射線光子能譜確定及殘焦中硫的形態[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04,38(l):25-30.
[5]李斌,杜霞茹,李慶峰,等.[J].環境科學,2004, 25(1): 149-153.
[6]Hsia C, Pierre G RRa, ghunathan K, et al. Diffusion through CaSO4 formed during the reaction of CaO with SO2 and O2 [J]. AIChE Journal, 1993, 39(4):698-700.
[7]Hsia C, Pierre G R, Fan L S. Isotope study on diffusion in CaSO4 formed during sorbent-flue-gas reaction [J]. AIChE Journal, 1995, 41(10): 2337-2340.
[8]Bhatia S K, Perlmutter D D. A random pore model for fluid-solid reactions(Ⅱ): Diffusion and transport effects [J]. AIChE Journal, 1981, 27(2): 247-254.
[9]Bhatia S K, Perlmutter D D. The effect of pore structure on fluid-solid reactions: Application to the SO2-lime reaction [J]. AIChE Journal, 1981, 27(2): 226-234.
[10]Hartman M, Coughlin R W. Reaction of sulfur dioxide with limestone and the influence of pore structure [J].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1974, 13(3): 248-253.
[11]Bhatia S K. Analysis of distributed pore closure in gas-solid reactions [J]. AIChE Journal, 1985, 31(4): 642-648.
[12]Duo W, Laursen Klim, J, et al. Crystallization and fracture: Product layer diffusion in sulfation of calcined limestone [J].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2004, 43(18): 5653-5662.
[13]楊立寨,祁海鷹,由長福,等.中溫條件下氧化鐵對氧化鈣脫硫的活化作用[J].化工學報:研究論文,2003,54(1):86-89.
[14]Li Chunzhu, Nelson P F.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release of nitrogen from coals pyrolyzed-bed reactors[C]. In: 26th Symp (Int) Combustion, Combustion Institute, 1996, 3205-3211.
[15]Aho M J, H m inen J P, Tummavuori J L. Conversion of peat and coal nitrogen through HCN and NH3to nitrogen oxides at 800℃[J]. Fuel, 1993, 72: 837-841.
[16]Wu Z, Ohtsuka Y. Remarkable formation of N2 from a Chinese lignite during coal pyrolysis[J]. Energy & Fuels, 1996, 10(6): 1280-1281.
[17]Ohtsuka Y, Wu Z. Nitrogen release during fixed-bed gasification of several coals with CO2: factors controlling formation of N2[J]. Fuel, 1999, 78(5): 521-527.
[18]Tsubouchi N, Ohtsuka Y. Nitrogen release during high temperature pyrolysis of coals and catalytic role of calcium in N2 formation[J]. Fuel, 2002, 81(18): 2335-2342.
[19]Mori H, Asami K,Ohtsuka Y. Role of iron catalyst in fate of fuel nitrogen during coal pyrolysis[J]. Energy & Fuels, 1996, 10(4): 1022-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