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的錄音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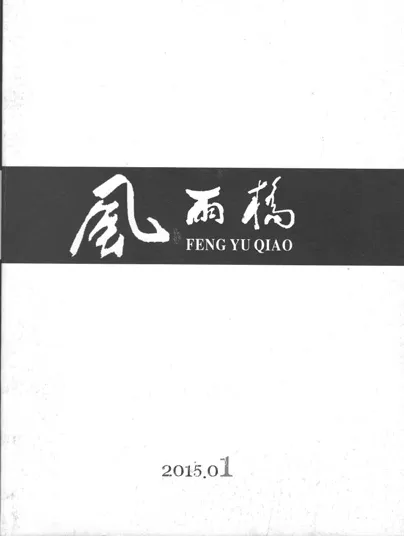
選自《風雨橋》2015年第1期
時光將你制作成標本,零碎地躺在我模糊的記憶里……
——題記
錄音機,像一位老者慢慢地退出了歷史舞臺。我也開始遺忘,我的記憶里曾經有過它的痕跡。那天閑來無事,在家整理東西的時候,在床底的角落里發現了那臺蒙上一層厚厚灰塵的錄音機。那是哥哥年輕時候時常帶去走寨的“寶貝”。那早已被時光遺落在角落的錄音機觸動著我的心弦,記憶一下子飄回那段美好的歲月。
是什么樣的機緣,使錄音機突然闖進我們苗家人的生活,我已無從知曉了。只記得那是20世紀9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間,那個幾乎與世隔絕的苗寨竟突然“冒出”了很多的錄音機。突然有一天,哥哥竟然也提著一臺嶄新的錄音機神氣地走出家門,跟著鄰居家哥哥去走寨。后來姐姐才說,是爸爸和哥哥去打工回來的那個夜晚買的。他們還一起圍著那臺錄音機興奮地搗鼓了大半夜,只有我睡得跟頭小豬似的才不知道。白天,我們姐妹喜歡偷溜進哥哥的臥房去“研究”哥哥的“寶貝”,僵硬地偷學著哥哥把磁帶放進去,然后托著下巴聽那咿咿呀呀的歌聲,感覺特別好玩。每次哥哥從外面回來,發現我們偷玩他的錄音機,就會罵我們,我們就像一群曬場上偷谷子吃的麻雀一樣,受驚之余一拍而散。每天挨罵,每天照樣偷偷玩。
錄音機除了用來聽歌之外,還有一個特別的作用:錄情歌。這也是我家錄音機成了哥哥的專屬品的原因之一。年輕后生們晚上帶著錄音機去走寨。用錄音機把晚上坐夜時的情歌對唱錄下來。那些感人精彩的瞬間無一不被記錄下來。錄音機儼然成了那時苗家兒女的牽線紅娘。其實,那時候我哥剛進入青春期,十五六歲的年紀,羞澀得不敢開口唱歌。聽寨子里的女孩子說,人家女孩子叫他跟自己對兩句,他都羞澀得不敢回答。他更喜歡讓鄰居家的哥哥唱,唱贏那些女孩。鄰居家哥哥歌唱得好,好多女孩子醉心于他的歌聲。曾有女孩子不顧家人反對,鐵了心想嫁鄰居家哥哥。
兒時的我最期待夜晚的來臨。我們姐妹的臥房窗戶正對著大路。那條大路是年輕后生們去走寨的必經之路。吃過晚飯,我們姐妹會早早躲在臥房里,趴在窗戶上,看著哥哥屁顛屁顛而又故作老成地提著那笨重的錄音機出門,然后等待著別家的年輕后生們三五成群,陸陸續續經過我家門前的大路。他們每個人手里都拿著手電筒,排成一排,像極了天上明亮的星斗。他們其中的一兩個人提著笨重的錄音機,挺直了腰板走在最前面,神氣十足。他們把音量調到最大,放著前個夜晚跟年輕女孩纏綿悱惻的情歌對唱,整個村寨都能聽到那千回百轉的情歌。苗家的年輕人含蓄,羞于在長輩面前唱情歌,因此平時很少有機會聽到的歌聲此刻更能勾起人們傾聽的欲望。聽到歌聲的大人們更是津津有味地討論著剛剛飄過的歌聲,究竟是哪家女孩跟哪家男孩之間的對唱。那時候,我們在夢里時常聽見鄰家坐夜時飄出來的情歌,那低回婉轉的歌聲夜夜裝扮著我們童年的美夢。我想,那時候我們的生活,因為歌聲,有了很多的期許和等待。
那時候我總想,長大了,我也要學唱情歌,也要像鄰居家哥哥一樣,擁有醉心的歌聲,用歌聲打動自己喜歡的人。可是還未等我長大,那歌聲慢慢離我遠去了。那時候我并不懂是為什么,為什么路過我家門前去走寨的年輕后生越來越少,那錄音機飄出來的歌聲漸漸遠去。我忍不住好奇,問母親。母親說,年輕人都你追我趕地出去打工了,哪還有空來走寨,哪還有空來唱歌啊,不過等他們回來以后,村里又可以恢復熱鬧啦。于是我開始夜夜期待人們快快歸來。
將近春節時,外出的人們陸陸續續地回來了,然而,他們幾乎個個都變了樣。尤其是年輕人,新潮的衣服,新潮的發型,看得人眼花繚亂。年輕后生們吃過晚飯,洗過澡,精心打扮了一番后,便邀上好友,三五成群去走寨。也有的膩煩了走寨,跟著中年男人一起鉆進鼓樓旁邊的代銷點(商店),在這里扎堆烤火也是一件樂事。我哥也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那套從不給我們姐妹碰的西裝和那雙皮鞋,還學著別人把頭發一齊往后梳,露出寬寬的額頭,帥氣十足。我們姐妹看著哥哥,眼饞得要命,只是不好意思吵著嚷著讓媽媽給我們買新衣服。打扮完了之后,再從他臥房里小心翼翼地搬出他心愛的錄音機,仔仔細細地把錄音機擦得锃亮锃亮的。一切準備就緒后,隔著窗戶喊鄰居家的哥哥,欲邀他去走寨。我們一猜便知他想去看望下寨那個他心儀已久的女孩兒。“哎,時間還早著咧,不如先去代銷點看別人打會兒牌?聽說昨晚他們搞大的,吳老二家大兒子贏了好大一筆。今晚我們也湊湊熱鬧去!”“別凈跟著去學壞!好好去走寨!”母親一聽要去看別人賭錢,氣不打一處來,壓低了聲音教訓哥哥。“好,好,我不會去的,再說我也不會打。”哥哥有些不耐煩地敷衍著。
在外面辛苦了一年半載的人們身上終于有了錢,錢袋鼓鼓的,揣在兜里,聊天聊得膩了,不自覺地就打起了錢的主意。誰先發起的,也沒人在意了,總之人們開始在代銷點里扎堆賭錢。有錢的、沒錢的,站在旁邊看都開始蠢蠢欲動。有時走在巷子里,會碰巧聽到木樓里傳來吵架的聲音,而吵架的內容多半與賭錢有關。聚在代銷點里賭錢、打牌開始慢慢成為人們主要的娛樂方式。人們茶余飯后閑聊時竟不知不覺多了一個話題:賭錢。“我家那沒良心的,昨晚也悄悄去賭了,還騙我說只是在旁邊看別人賭。聽說你家老大昨晚也去了。”“什么?他不是說去走寨了嗎?輸了嗎?”“聽說德平那小兒子昨晚賺了幾百。”……我呆呆地坐在火堆旁邊,聽著她們你一言我一語,聊得越來越起勁,我才發覺,似乎人們更關心昨晚誰輸了多少,誰贏了多少,而對誰對歌贏了,誰對輸了,似乎已經沒那么津津樂道了。年輕后生們也會積極響應、追趕這種“潮流”。我哥每天晚上吃完飯,就迫不及待地拿著手電筒溜出家門。我媽朝著他的背影喊:“不帶上錄音機啦?”他頭也不回地說:“不帶了,那東西太重,帶著不自由。”后來,家里買了電視,哥更是嫌棄那笨重的錄音機,直接把它丟棄在角落里;而我們姐妹也漸漸喜歡上其他新鮮的事物,不再覬覦哥哥曾經的寶貝了。
新鮮的事物、新鮮的思想慢慢改變著苗家兒女。他們加緊了步伐,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想要跟上時代的腳步,變著花樣地去追隨新的娛樂方式,卻再也無暇也不屑于花心思去唱歌,也沒有時間來你儂我儂。曾經苗家人的“寵兒”,苗家兒女的“紅娘”,苗族山歌的承載者,被人們遺忘在角落里,蒙上了厚重的灰塵。長大之后,在外面求學,偶爾回到家,從鄰居家的音箱里飄出來的高調的歌,從《嘻唰唰》到《小蘋果》,聽到的都是那些最新的流行歌曲,而童年記憶里隨處飄散的苗族情歌,卻再也沒有回響過。
看著那臺蒙上灰塵的錄音機,我開始懷念那段時光,懷念那承載著苗家兒女纏綿情思的錄音機,懷念那夜夜伴我入夢的婉轉歌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