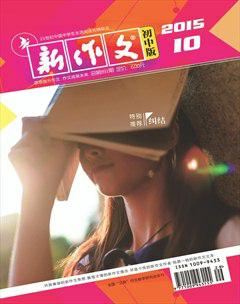花間的秋千
李宙怡
校園一隅,有一座很大的花壇,花壇正中擺著兩架秋千。秋千是云杉木制的,自然素雅的木頭紋理將其點綴得恰到好處。
花壇里四季都有花兒開,春天的紫藤蘿,夏天的梔子,秋天的菊,冬天的梅。
每天中午,我總會抱著自己要寫的小說,和揚揚一起坐在花海里的秋千上,推敲小說中的人物、情節,還有文字。
春光和煦,清風微拂,一陣幽雅的芳香飄到了我們面前。紫藤蘿從花架上細軟地垂下,淡紫色的花瓣交迭在一起,仿佛一道瀑布,紫色的水流中閃動著幾點銀光,細看之下,其實是白色的花蕊。藤蔓隨風曼舞,如同少女噴過了香水的飄逸長發。我和揚揚坐在秋千上,蕩呀、蕩呀,討論著小說應該如何開頭。揚揚認為:“你可以描寫一段草長鶯飛的環境,然后只聽珮環叮當,她就忽然出現在了墻頭,又一躍而下,同時出現的還有兩個丫鬟模樣的美麗少女。”“我覺得這本小說是寫一個姑娘的故事,開頭應該寫一個男子。”我說。“好主意,”揚揚道,“那就寫一個年輕男子在酒樓里見到了她?”“不如寫一個算命先生為一位公子算了一卦,說是他會在申時見到一個蒙面的姑娘?”我問。揚揚補充道:“而且這個姑娘在用兵器寫書法?”于是我就落筆了。紫藤蘿從花架上飛漱而下,我的筆尖也如流水一般在紙上滑過,不經意間,幾頁紙就被文字蓋滿了。
夏日的陽光雖炙熱似火,但有了梔子花的馥郁清香,人心頓時感到涼爽了許多。看著青翠欲滴的灌木叢上白凈嬌嫩的梔子花,總是不免心生歡喜。我與揚揚坐在秋千上,蕩呀、蕩呀,我把前一天新完成的段落讓她過目,她連連叫好。我又面露為難之色,向她道:“寫到這里我不知如何繼續了,不若這樣,現在我是慕容鳳,你是文天嬌,你手無寸鐵地站在梳妝臺前,我闖了進來,拔出劍威脅你交出刀訣。現在你把你的心理活動還有要怎么做講一下?”揚揚想了一會兒,回答:“我會故作鎮定地對他說:‘非君子也!要是人們知道你是這樣得到這部刀訣的,恐怕你在江湖中也無處立足了!”我接道:“那我也就殺了你滅口。”揚揚回話:“我的武功不是很高強么?見你真要動手,我就拔下發上的金釵,把釵當作判官筆使,又可以通過釵送出劍氣。如何?”我拍手,喜道:“好!”梔子花靜靜地香著,我感到筆下的文字也漸漸細膩了起來。
秋天,枝頭的樹葉變黃、發枯,像折了翅的蝴蝶,紛紛落在地上。花壇上種了一圈雛菊,弱不禁風的模樣,卻經歷了蕭瑟的秋風的洗禮。落葉、雛菊,一派清新又有些落寞的情調。我與揚揚坐在秋千上,蕩呀、蕩呀,討論著小說應如何結尾。“你寫文天嬌最后被救活了吧,這樣她就可以和肖香蘭在一起了。” 揚揚說。我掃視著秋千四周的花叢,總覺得這本小說需要一個傷感的結尾。我搖了搖頭:“不,雖然文天嬌是善人,但如你所說的話,豈非又要落入皆大歡喜的俗套中去了?”“好吧,倒也有理,但你總不能讓好人死去讓惡人活著吧?”我們邊蕩著秋千,邊討論了良久。最終決定這樣結尾:“第二年春,肖香蘭又來到了文天嬌的墓前,前一年他栽下的桃花開得艷紅,就如兩人初次見面時文天嬌的朱唇。而慕容心在毒殺了文天嬌后也由于自認罪大惡極而服毒自盡了。”
冬日中只有梅花傲然綻開,暗香浮動。梅花是可愛的淺紅色,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我與揚揚坐在秋千上,蕩呀、蕩呀,琢磨著章節的題目如何取才好。我提議用詞牌、曲牌名作為標題。“好啊!你看第一章提到了算命先生,就叫“卜算子”;這章里文天嬌用金釵來對敵慕容鳳,可以題作“釵頭鳳”;結局中寫桃花的紅色就如文天嬌的朱唇,不如稱為“點絳唇”。紅梅凌寒獨自開,迷倒于自己的馨香,我和揚揚也不畏寒冷,陶醉于自己的文字。
一年又一年,我與揚揚早已不是當年那兩個懵懂無知的孩子,但我們仍喜歡在午后坐在秋千上,沉浸在花香中,蕩呀蕩呀。因為此時,我們的心已經飛到了自己的文字中去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