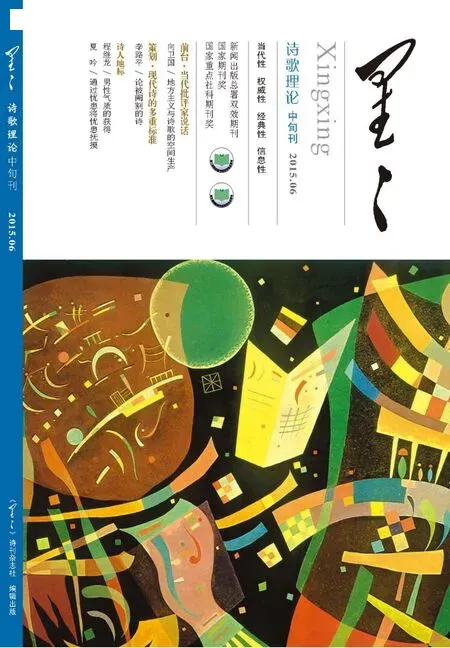詩歌的現實性與“詩性”
余 陽
詩歌的現實性與“詩性”
余 陽
何謂“詩性”?雅各布森將其屬性界定為“自我指涉”的,即“當詞被作為一個詞,而非被命名的對象的純粹再現或某種情緒的爆發來感知時;當話語及其組構,其意義、其外在和內在的形式需由其自身,而不是無關痛癢地參照現實來估價時”,“詩性”便能顯現出其自身。也就是說,“詩性”的顯現,往往是通過詩歌自身所具備的、為詩歌這一體裁所獨有的比喻性和超越性來實現,從而使詩歌在其字面意思之外,還能“另有所指”。恰因為此,在以詩人寫現實的過程中,就要考慮如何能既保住詩歌的“詩性”,又使其不至于完全脫離現實,成為虛有其表之物。就像我們放風箏時,需要什么材質的線,粗細如何,具體放多長,傾斜的角度,收放的時機,這些因素都需考量,風箏才能放得高遠,又不至于飄走。
在北野的《正是一年中牛羊轉場的時節》中,這位北疆詩人所抒發的情感,始終與其所描繪的景象是渾然一體的。“河流獻出了石頭/山林獻出了松果/而運送酸雨的云塊也從草原上空/忍痛經過”,在此處,河流、山林、云塊都成為動作的主語,甚至有了“忍痛”的感覺,生命與生命之間,因此建立起關聯,并融于一體,達成了一種情感共通,表現出自然所受到的創傷。在詩中,河水、雨霧、牛羊、馬駒等都被賦予了靈性,彼此相互映襯。而詩中的“我”,只是“驕傲伴隨著心碎/淋著雨爬上了/望不見親人的山坡”,“我”也只是這些生命中渺小的一員,而并非這種靈性、這種情感共通的主宰者。詩人在詩中所勾勒出的,是各種生命其靈性的融合;詩人的抒情,亦是對生命靈性的感受,而非控制。此外,除了描述性的語言,詩人還用了幾個“但愿”,“但愿我的馬駒不在其中/而我的孩子/那命中注定的城市孤兒/但愿他們/不再走山羊的路/住狐貍的窩”……以此表達他的希望,然而,這樣的“但愿”,或許也暗藏著愿而不得的隱痛。在充滿靈性的自然中,詩人謙卑的歌唱,引領著讀者將目光投向感受的更深處。
截然不同于北野,韓作榮的《溫情——寫給妻子》,講求的是“恰到好處的溫度”,語言質樸,語氣平常,頗有些“去抒情”的意味。詩中講的,是人們所格外熟悉的生活場景,看電視學菜譜、看養生節目、踢鍵子、打乒乓球等等,完全沒有拉開與讀者之間的距離。然而,在我們讀完之后,再慢慢回味咀嚼,詩歌的超越性和比喻性方才慢慢浮顯。對生活典型場景的提煉、片斷的截取、輕輕的慨嘆,整體構成了一個所謂“生活”的復雜意象,它既不過分消極,也不過分昂揚,只在各種細節的縫隙中,去觸碰生存狀態的本真。而詩題“溫情”,或許既意指和妻子間的情意,也指向詩中平和的態度。
而汗漫的《早春,為祖父祖母合墓》,則獨樹一格,充滿了自由的想象。“我看到那口桐木黑棺已經出現裂紋的右側面/仿佛一艘舊船的右舷/一個農婦獨自在無邊泥土中漂泊多年/如今回到渡口/等待丈夫的新船下水”,詩中的“我”就像一個故事的觀看者,來“看”祖父母的合墓,“看”他們的“重逢”,而最后,“我”其實也一樣,回到妻子身邊躺下,“仿佛也是黑色桐木或者水墨荷葉”,就像被“我”所看到的故事里的主角,像“我”的祖父母一樣。生存與死亡,生命過程的循環與延續,通過這樣的“看”而被聯結起來。錯雜在一起的真實與虛幻,將視覺與思考一并作了延伸。
哈羅德·布魯姆在《讀詩的藝術》一文中講到,詩本質上是比喻性的語言,集中凝練,故其形式兼具表現力和啟示性。比喻是對字面意義的一種偏離,而一首偉大的詩的形式自身就可以是一種修辭(轉換)或比喻。因此,過于斬釘截鐵的措辭是對詩性的傷害,詩歌在與現實接近的同時,或許也對詩人提出這樣的要求,即始終真誠地懷抱謙遜的態度,懷抱對自然、對生命、對所指之物的謙卑之心,從而去打破一種固有的邏輯,把那種由經驗所累積出的理所當然的東西破壞掉。從三首詩中,我們看到詩人對顯現“詩性”的不同的探索,既體現出詩人的不同個性,也展現了各種可能。而今后不同個性的詩人們更多的嘗試和探索,或許也值得我們期待。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