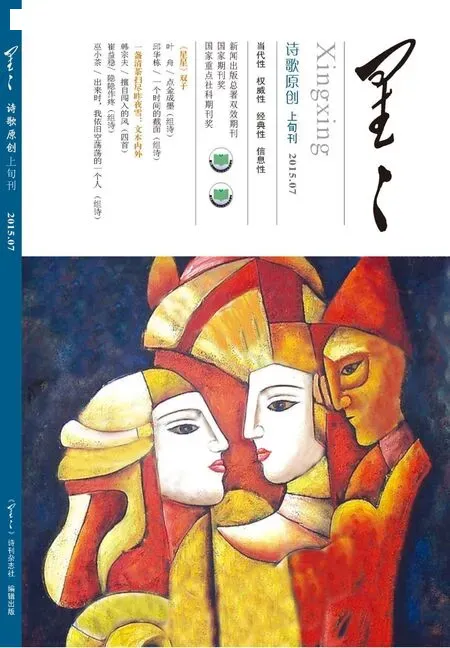豬圖騰 狗兄弟
崔益穩
豬圖騰 狗兄弟
崔益穩
我家三代與豬有緣。爺爺和父親均是老家方圓幾十里有名的殺豬匠,為日本鬼子和八路軍都殺過豬。我剛參加工作時在肉聯廠與豬打過十年交道,如今一不注意,豬常入我的文章和詩行。
在原生態的農村,豬狗幾乎是朝朝暮暮不分家的兄弟。父輩殺豬賣肉時,也常干些販狗殺狗的營生。在我童年的彩色記憶里,有關豬狗與人的真實故事生動得讓人忍俊不禁,越想越回味無窮。
這里要說到兩個詞語:忠誠和奉獻,在這兩個畜牲身上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在當下時代高鐵和物質洪流的呼嘯沖擊下,人類喪失的最快最多的恰恰是這兩個詞語。所以,我一次次將筆觸伸向它們,一次次在內心將它們呼作“兄弟”。所以,故鄉的蕎麥、草垛、青菜之類的美物在我詩行里恣肆汪洋。
更多的人蜂擁進入城市,豬們狗們也以不同方式闖入城市。因我頻頻將當下人的生存狀態置于城市與豬狗的背景下,不少朋友常指著街上豬狗半開玩笑譏諷我,看啊看,老崔的兄弟們來了!
狗兄弟怎么了?豬兄弟怎么了?我才不惱呢,如今這世界上能和它們平起平坐的多嘛?多少次酒酣之際。我拍案左右反問,現在有幾個人保證活得比一條狗還要忠貞不二?
在記憶里那個質樸而貧窮的年代,一頭豬好比一座化肥廠,是一個家庭變富的精神圖騰。一只狗等于一尊守護神,對于一個村莊的長治久安何等至關重要。斗轉星移,它們進入城市了,除了血液里仍流動著原始的基因,它們也以固有的神態延續其獨有的生活方式。我在郊外一座現代化的養豬場看到,被稱作太湖品系的雜交豬,被鐵柵欄箍在不足一平方米的鐵框內,從生到死不能轉身,不能越雷池一步。可它們依然那么憨厚與從容 ,以一口一口的粗料變為一坨坨肉。這不是奉獻精神,是什么?朋友送我幾斤這種豬做成的臘肉,一遍遍叮囑這是“生態豬肉”,可我品嘗后發現與記憶中的土豬肉味大相徑庭。嘿嘿,也許這就是當下時代的況味吧。在街頭與小區間竄來竄去的狗太可憐了,相比于隨時都可在鄉村野田撒歡調情的祖輩,它們如今連談情說愛的場所也沒有了。
我家狗的故事更加令人唏噓。母親撒手人間后,與她朝夕為伴的狗送給了鄰居。去年鄰居因拆遷搬往集鎮,將狗裝入麻袋帶走,準備給它安排寵物狗一樣的悠閑生活。可狗堅決不從,一次次被捉走,又一次次跑回來,毅然回到它消失已久的狗窩里。看它可憐,鄰居只好在我老家墻角瓦礫處,以磚頭就地搭了一個簡陋洞。今年回去過年,我一心找它,甚至欲抱住它一遍遍致敬:我的狗兄弟!可惜未能如愿,它或許成了一只流浪狗,或許成了別人的盤中餐。但我為它慶幸,他肯定沒有客死他鄉。狗尚且如此忠貞于故土,何況人呢?
豬圖騰,狗兄弟,怎能不讓我放眼正被城市化瘋狂進攻與掠奪的故土。一排排風景如畫的房子麻將牌般被推倒,清亮的小河被爛透的水草瘀塞了。最心疼不過的是,每次與鄉親們照面,聽到的是一個又一個我熟悉的名字,誰誰走了,誰誰又走了,得的多是與環境污染有關的怪病。在城頭登高遠望故鄉的方向,依稀可見老家四周的生命之燈一盞盞熄滅了,只剩下門前幾棵老樹在推土機的轟鳴中茍延殘喘。這又使我自然地聯想到詩,想到那些曾經花哨、浮躁的文字游戲。我不可能改變活生生的現實,但我可以記錄,可以呼喊,真實、真摯、真誠,以詩人之眼光燭照未來。
一位大詩人說,所有的詩人開始都是“最初的洞察者,詩人中的王者,真正的上帝。”但是,最初的洞察者會蒙上紅塵之翳,王者變成了奴隸,上帝變成了棄兒。區區數年,很多詩人面前的豬們狗們,不過是行走與長肉的動物而已。而我要在疼痛里與它們一起行走。
在疼痛里飛翔與行走,是多么殘酷的糾結。生活之惡在踐踏,而我自己竭力用詩歌在拯救。每每讀寫滾燙的分行文字,都會想到波特萊爾那只追隨海船的信天翁,它有天高海闊的胸懷,它有搏擊風暴的堅強翅膀與心臟……可我總是不自覺地一下子聯想到豬與狗的形象。
洗潔劑一樣的時代之潮,每個人都得異化,但在異化面前得清醒,得堅守!我有足夠的內心勇氣聲明,我要繼續大聲將豬狗們稱兄道弟。我要用筆留住時間和人性最純粹的部分,故我真實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