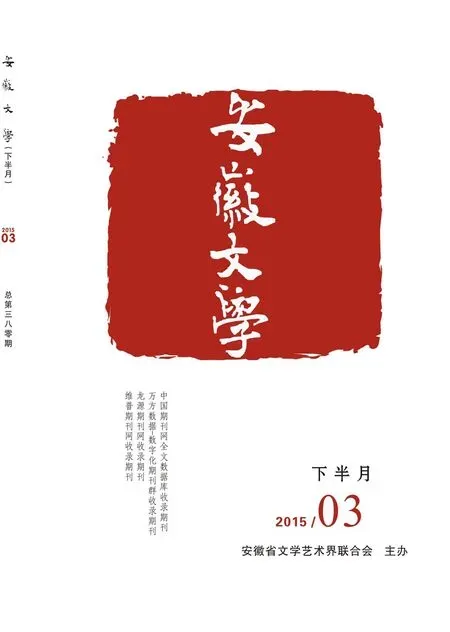《飛越瘋人院》的象征意義分析
孫孝云武漢大學
《飛越瘋人院》的象征意義分析
孫孝云
武漢大學
摘要:《飛躍瘋人院》生動地描寫了發生在精神病院里的瘋狂事件,展現了大護士拉契特象征的權利制度及病人麥克墨菲象征的人性自由間的巨大沖突,揭露了病人們在醫院所遭受的殘忍壓迫,以及對極其苛刻的控制手段所做出的英勇反抗。通過大量地使用隱喻性象征,作者肯·克西深刻地批判了不斷使人類被機器化進而喪失人性的制度化社會。
關鍵詞:象征瘋人院聯合機構制度化
肯·克西是美國20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同時也被人們認為是“垮掉了的一代”中反社會文化的風向標。他的代表作《飛越瘋人院》發表于1962年,小說生動地描寫了以麥克墨菲為代表的精神病人和以護士長拉契特為代表的醫務人員之間的沖突,記錄了病人們在醫院所遭受的壓迫,以及對極其苛刻的控制手段所做出的英勇反抗。肯·克西通過大量的象征描寫來揭露機械化社會使人喪失人性淪為機器的本質。
一、麥克墨菲——自由的化身
麥克墨菲沒有穩定的工作,為了逃避勞動改造而假裝精神失常,進入精神病院治療。他崇尚自由天性快活。他用狂野粗魯的笑聲來應對所有試圖馴服他的清規戒律,暫時激活了瘋人院死寂的世界(11)。正如酋長布羅姆所描述那樣:“當他初次走進病房就放聲大笑,這是自由的笑,這是真實的笑。我意識到已多年未聽見如此震撼的笑聲了。”(11)在大護士拉契特的監管下沒人敢放肆大笑,而麥克墨菲的笑聲充滿力量和自信,感染著病房里所有的患者,幫助他們釋放壓抑已久的內心能量。他反抗一切限制約束,努力爭取患者基本權利。他不會讓“聯合機構”使病人成為他們的高壓控制下生產出的產品。例如他號召病患投票取決看球賽的權利,并且獲得斯皮維醫生的支持來將雜物房改造成棋牌室。他追求自然解放天性。組織狂歡為朋友帶來了酒精和性愛,來釋放他們在令人窒息的精神病院中長期約束的天性。他組織病患出海釣魚。面對象征自由的大海,精神病者暫時擺脫掉病房里噩夢般的生活,重拾激情、自信和希望。麥克墨菲是自由戰士,時刻準備擊垮一切限制和約束。他是精神病人的救星,不遺余力地支持他們,幫助他們恢復尊嚴和自信,恢復生機和活力。然而正是由于他對權利制度的蔑視反叛,對解放自由無畏的斗爭,讓這個機械化社會無法容忍,所以最后等待他的是前腦葉白質切除術,將他塑造成為社會“無公害產品”。
二、大護士拉契特——絕對權力的代表
在《飛越瘋人院》中,大護士是精神病院的女統治者,代表著絕對的權利。她絕非致力于悉心治療病患的善良白衣天使,而是在乎如何高效管理病患的獨裁者。在大護士的操縱系統中,病人任其擺布。布羅姆登的眼中,這個病房被聯合機構(combine)管理控制,而護士拉契特就是確保聯合機構及時高效運轉的核心部分,確保聯合機構的齒輪朝著一個方向運行(28)。如果誰阻擋這個機構運行,或者改變其運行方向,那么她就會運用各種措施或者懲罰。
各種條規限制就是拉契特控制精神病人的精神武器。病房里的病人被剝奪了自由,剝奪了作為人類的基本權利。他們無法看自己喜歡的節目,聽自己喜歡的歌曲,不允許質疑不允許反抗。他們的作息時間嚴格按照日程表來執行,但每當有病人希望日程表能稍加變動時她總是毫不猶豫地拒絕,聲稱改變合理安排的作息對病人的治療無益處。事實上這些條條框框的限制使病房成為監獄,人們像機器人一樣生活,毫無治愈可言。
電擊治療和腦白質切除術是大護士拉契特控制病人的終極手段。這些措施以治療病人的名義來實現對病人身體的殘酷懲罰,起到對病人威懾的作用。病人切斯維克要求拿回香煙被拒,變得憤怒而失去控制,而麥克墨菲和布羅姆登痛打了大護士跟班華盛頓之后,都接受了電擊治療。在當時人們對電擊治療了解甚少,但不可否認的是電擊治療毫無治療效果,只會通過物理手段殘害人的思維,剝奪人的思想,布羅姆登總是產生各種幻覺,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過度電擊造成的。比起電擊,更令人發指的是腦白質切除術。由于見到好友比利迫于大護士的言語譏諷而羞愧自殺,麥克墨菲不顧一切要殺死這位間接兇手。但最終他仍然被制服了。在實施腦白質切除術后,麥克墨菲“眼神空洞無神,就像那些木乃伊一樣”(278),而再也不是以前生機勃勃的戰士麥克墨菲了。通過對病人的大腦造成無法修復的傷害,這些治療手段猶如給病人判下死刑一樣,因為人一旦被剝奪了大腦,被剝奪了思想,就與活死人無異。
三、瘋人院——制度化社會的縮影
小說標題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譯為杜鵑窩或者飛越瘋人院)中的杜鵑窩“cuckoo’s nest”是瘋人院的戲稱。這一詞在文中出
處來源于布羅姆登的祖母在他小時候給他讀的一首歌謠:“叮叮當,叮叮當;好漁婆,手腳長,捉住母雞籠里關,金屬的鉗子彈性的鎖,三只白鵝成一伙;一只飛向東,一只飛向西,一只飛越了杜鵑窩。”(280)這首小詩正好包含了小說三個主人公。護士長拉契特是“漁婆”,將所有的病患關在牢籠中。“東”和“西”象征著兩種極端力量,拉契特象征絕對控制,而麥克墨菲象征絕對自由,“一只飛越杜鵑窩”則暗示最終布羅姆登成功逃離了精神病院的囚籠。
杜鵑窩也許僅僅是瘋人院的一個趣名,但杜鵑窩卻也是大自然的一個陷阱。作者戲謔地邀請對文明和自然的機制之間進行比較,但是一般將杜鵑和瘋癲聯系在一起主要是因為杜鵑殘忍的行為。在自然界里,杜鵑把它們的蛋放在別的鳥窩里。由于新生的杜鵑和其他的繼兄妹間沒有聯系,待它們長大后,它們會把其他的蛋甚至活的小鳥扔出去。這是一個借居者變成暴君的過程,無序、錯置和競爭主宰了任何合理的設計。文明的陷阱和自然的陷阱又有什么不一樣呢?酋長布羅姆登孩童時期與父母平和地生活在印第安納部落里,后來美國政府為了建大壩供電而強制性購買了部落的村莊,“美國內政部用一個碎石機埋葬了我們的小小部落”(7)。大壩代表著破壞一種生活方式以服務于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機器。美國白人的做法無異于杜鵑,占領他人領土,破壞他人傳統生活方式,讓自己的白人文化成為主流,使印第安納少數族裔的文化逐漸邊緣化,甚至消失殆盡。
精神病院是制度化社會的縮影。這個世界被叫做“聯合機構”的機器所控制。聯合機構中存在由大護士拉契特為代表的絕對權威體系,存在機器流水生產線產出的“產品”似的病患,存在議會似的“民主”會議,看上去是在為病人謀福,實則是互揭傷疤互揭痛處的虛偽會議。在這個令人窒息的世界中,沒有娛樂,沒有笑聲,沒有人權,沒有自由,更別提對精神病人的恢復和治療。聯合機構是一個同化個人來實現自身利益的實體,是一個對于阻擋其前進道路的任何東西無情鞭打、切割和清除的機器(7)。聯合機構代表整個制度化社會的機構,作者用對聯合機構的象征性描寫來影射壓抑人性的現代體制。
四、結語
在《飛越瘋人院》小說中,肯·克西巧妙地將象征融入小說主題中。精神病院就是社會的縮影,聯合機構是社會的管理體制,主人公麥克墨菲是這一機構中的自由戰士,而護士長拉契特則是鎮壓一切叛逆的權威代表。通過對象征形象貼切的描寫,作者矛頭直接指向當前社會使人機械化一致化的傾向,麥克墨菲與拉契特的沖突揭露出向往自由的人類與壓抑人性制度化管理社會的沖突。小說最后以布羅姆登成功逃離為結尾象征著作者肯·克西的積極態度。酋長布羅姆登砸碎了通向自由世界的玻璃,砸開了讓光明進入,讓希望進入,讓人性流入的縫隙。
參考文獻
[1]肯·克西.飛越瘋人院[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