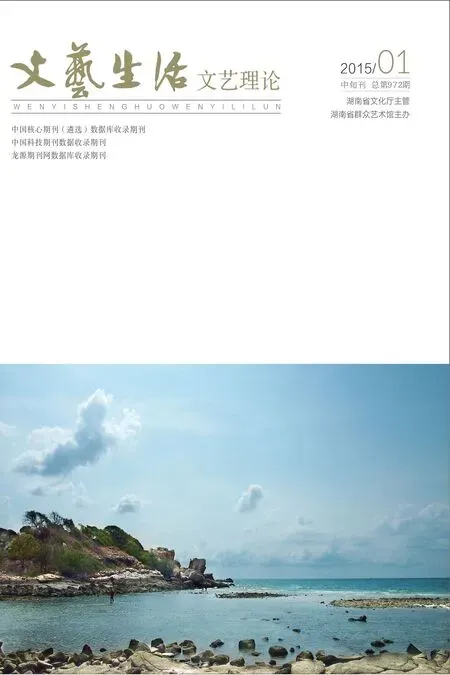世紀末詩歌衰退表現初探
康碩
(山東大學,山東 濟南 250100)
世紀末詩歌衰退表現初探
康碩
(山東大學,山東 濟南 250100)
20世紀90年代的詩歌無論從歷史價值、社會地位、文化環境、審美取向、現實意識、詩歌成果、創作群體哪個層面看,其成就都不能與其它的文學體裁同日而語,更不能與之前的詩歌相提并論。其走在了歷史、社會、文化和現實的邊緣,在一定程度上講,可以說詩歌在20世紀90年代衰退了,然而其衰退的表現形式卻是多方面的,本文對此進行探討。
90年代;詩歌;衰退;表現
作為一個詩的國度,從歷史上看,中國的詩歌曾長期被視為文學的正宗。進入到20世紀,詩歌作為白話文學變革的先驅,引領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與演變。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伴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和一系列“斷代性”事件的發生,文學的地位發生了一些轉變,作為時代最敏感的神經——詩歌,其境遇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90年代詩歌的最大變化便是衰退,并且有多方面的表現。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對90年代詩歌衰退現狀的界定與評價,是從宏觀方面與整體發展的角度衡量,因為一個時代的詩歌成就并非個人或某團體所能代表。
從20世紀90年代起,詩歌不論從歷史價值、社會地位、文化環境、審美取向、現實意識、詩歌成果和創作群體哪個層面看,成就都不能與其它的文學形式同日而語,更不能與之前的詩歌相提并論。下文具體探討。
1.90年代詩歌不受政治話語、主流意識形態、大眾庸俗文化的約束,同樣也不是時代的代言人,而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性,從這種角度講,對詩歌發展無疑有益,但縱觀90年代詩歌發展的總體概況,令我們大失所望。90年代的詩歌對中國詩歌發展的方向并未明確,潛在寫作的挖掘力度遠遠不夠,對于詩歌發展的貢獻微乎其微。
2.普通大眾對于詩歌的成就與發展也失去了信心,我們與其說90年代的詩歌缺少了讀者的回應與認同,還不如說全民對于詩歌的現狀和未來失去了信心。詩歌依附于商業,文學的自覺性遠去,詩歌與商業為伍。在商業化、市場化和世俗化浪潮的沖擊下,之后各種外來文化潮流如洪水猛獸般沖進我國的傳統文化圈,象征人類精神領域的文學成了眾矢之的,詩歌所在的文化環境極度惡劣。
文學發展的趨勢是文學由精英化走向平民化和大眾化,詩歌的皇冠地位也在隨之下降,詩歌在走向大眾化的過程中,必然經歷通俗化的階段,但是通俗化并不與低俗化與媚俗化等價。大眾對于詩歌的冷漠,甚至到了鄙視質疑的地步。詩歌在社會公共空間的占有量及影響力急劇下降,社會大眾的詩歌創造力與鑒賞力普遍淪落,社會人文精神素養與審美追求集體消退,這不僅是詩歌發展的悲哀,也是社會精神價值丟失的悲哀。詩歌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和走向了“邊緣化”。
3.90年代的審美取向走向了低俗、媚俗與庸俗。詩歌的粗制濫造,以無畏無懼的低俗描寫吸引著讀者,詩歌沒有時代的呼聲與印記,沒有超越社會現實與個人的思想情感,詩歌也沒有突顯出寫實的高度與深度。詩歌的現實精神被低俗的“非詩寫作”所代替,90年代詩歌逐漸走向了形式的散文化、內容的低俗化、語言的通俗化,詩歌脫離了其最基本的音樂美與高度的凝練性,內容上雖然體現著90年代的后現代性,但并未達到較高的藝術層次。詩歌以低俗的追求取悅庸俗的公共大眾,最終引導詩歌的主流寫作傾向走向了低俗化、媚俗化和庸俗化的審美傾向,詩歌成了小圈子運動,僅限于自娛自樂。
“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個人化寫作”、“口語化”寫作、“日常化”寫作、“敘事性”傾向,這些被冠以具有90年代色彩的詩歌寫作傾向名詞,從來沒有建構起關于這些寫作主張完整的理論體系,同時體現了90年代詩歌創作主張與寫作界的混亂,有的創作主張對于詩歌的發展起到了極其消極的意義。這些表明,90年代詩歌的審美主導傾向存在著嚴重的寫作誤區,價值追求存在著嚴重的偏離失衡。
4.20世紀末的“盤峰會議”表現出了詩人在創作上沒有突出成就的同時卻走向了分裂。90年代的詩人成為世俗的群體,呈現出了“痞子化”傾向,缺乏應有的責任感與批判意識,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顯得彌足珍貴。90年代的詩人根本沒表現出在商業和世俗環境下的精神焦慮,他們無情地調侃和解構詩歌。“90年代的詩人,成為一群詞語造成的亡靈。”①
詩歌在90年代缺乏天才式或具有高度成就的詩人,詩人以解構為樂趣,解構中未曾想起價值的重構。詩人的變質便是詩歌衰退的表現之一。
5.從詩歌成就上看,90年代的詩歌主張多元,其實是混亂的狀態,“知識分子寫作”注重哲理與命運的思考,承擔與反思的傾向,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我國傳統社會中“士”階層優良傳統的回光返照。這種自覺承擔為90年代的詩歌擺正了應有的態度,但在詩歌本身來說,大多數詩歌存在著說理的意味,同時帶有較強的玄言色彩,語言顯得累贅啰嗦。“民間寫作”是生活反詩意的代表,但是詩人卻忽略了生活與詩歌并不等同。詩歌作品抓住了時代的特點,卻忘記了詩歌自身的特點,表明了詩人對于現實生活的急躁處理和詞語的機械堆積。部分作品包含的低俗端倪,為后來“下半身”寫作埋下了禍根。民間本是文學產生的源泉所在,在90年代卻成了庸俗與低俗的代名詞。極端的口語化探索,也使其詩歌走向了庸俗與低俗的死胡同,從長遠來講,其對詩歌的消極作用遠遠大于積極作用。
詩人對于“口語化”、“日常化”和“詩到語言為止”的主張使詩歌喪失原型,以犧牲詩歌的藝術審美張力與社會歷史價值為沉重代價,我們必須承認,詩歌與語言并不等價,語言只是詩歌的承載方式,語言作為一種工具表達著我們的思維。“個人寫作”與“多元化”傾向,表明了當下詩人被“邊緣化”的現實處境,事實上詩歌的“個人化寫作”堂而皇之地瓦解了詩歌的意義與價值。“知分子寫作”成了“民間寫作”的對立面,顯得水火不容,“個人化”寫作與“敘事性”傾向的本質是對文學自覺的自覺追求,但在90年代成了自娛自樂、任意解構的代名詞,“日常化”與“口語化”具有濃烈生活氣息的寫作主張,而在90年代成了對生活碎片的任意組合,對低俗的不斷追求。
90年代詩歌發展的最終結果和極致性展現是“下半身”詩歌極具膨脹,對肉體過分迷戀、對低俗刻意追求,正如沈浩波所說:“我們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們都這樣了,我們還怕什么?”②詩歌從“語言的時代”到了“身體覺醒的時代”,全民遭受著審美的辱沒與精神的調戲。
總之,正如王岳川所說:“在價值錯位的90年代,詩在偽詩中日益貶值。偽詩人們開始以輕賤戲謔的文字游戲,去掉了沉甸甸的價值關懷,使偽體驗走上了‘詩歌祭壇’。那些在語言操作中排列著長語句的‘詩人’,每日‘制作’的‘詩’實質上是給人們的‘非詩’——冷漠的敘述方式,隨意捏合的語言意象,疲軟情感的裸露,本真意識和血性情懷的消失,游戲與痛苦的轉位,這就是世紀末詩界的疲憊‘尊容’。”③20世紀90年代的詩歌成就確實難以讓人肯定,詩歌走向衰退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思考這些現象發生的復雜原因,為未來詩歌的發展提供借鑒。
注釋:
①歐陽江河.誰去誰留[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
②沈浩波.下半身寫作及反對上半身[J].詩刊,2002(15).
③王岳川.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208.
[1]歐陽江河.誰去誰留[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
[2]西渡.守望與傾聽[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3]王家新.從一場濛濛細雨開始[J].讀書,1999(12).
I052
A
1005-5312(2015)02-0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