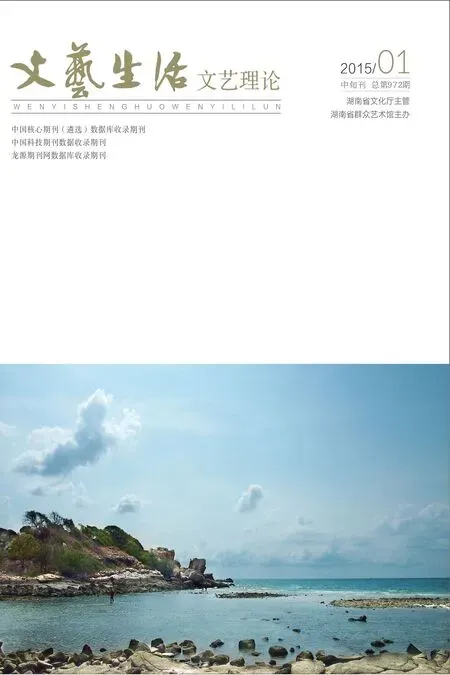淺談禪宗思想與古典園林
王鳳陽
(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天津 300072)
淺談禪宗思想與古典園林
王鳳陽
(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天津 300072)
文章通過介紹禪宗思想的產生背景與主要思想內容,論述了禪宗思想對古典園林多方面的歷史熏陶與影響,進而滲透到園林藝術創造中,極大地啟迪了古典園林的意境、美學以及空間結構的營造,使我國古典園林逐漸成為一種內在深邃哲理與完美形式和諧統一的藝術精華。
禪宗思想;產生背景;思想解析;園林意境;園林美學;園林結構
一、禪宗產生的時代背景
禪宗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宗派。主張修習禪定,故名。又因以參究的方法,徹見心性的本源為主旨,亦稱佛心宗。傳說創始人為菩提達摩,下傳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時稱“南能北秀”。
自佛教傳入中國后,禪學或修禪思想一直獲得廣泛的流傳,在東漢至南北朝時曾譯出多種禪經,禪學成為相當重要的流派。相傳菩提達摩于六朝齊、梁間從印度渡海東來,到洛陽弘揚禪法。因其禪法不為當時佛教界所重,乃入少林寺安心壁觀,以“二入四行”禪法教導弟子慧可、道育等。慧可從達摩6年,達摩授以《楞伽經》4卷。后隱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潛山東北),傳法于僧璨。僧璨受法后又隱于舒州司空山(今安徽太湖北),蕭然靜坐,不出文記,秘不傳法。唯有道信侍璨9年,得其衣法。后至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傳法,嘗勸道俗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可見其除依《楞伽經》外,還以《般若經》為依據。后住湖北黃梅雙峰山30多年,主張“坐禪守一”,并傳法于弘忍。其另一弟子法融在金陵(今江蘇南京)牛頭山傳牛頭禪。
弘忍得法后即至雙峰山東馮茂山另建道場,名東山寺,時稱其禪學為“東山法門”。其“蕭然靜坐,不出文記,口說玄理,默授與人”的作風,開中國佛教特有的禪風,對后來禪宗發展影響甚大。弘忍著名的弟子有禪秀、惠能、惠安、智詵等。惠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懷讓、青原行思、荷澤神會、南陽慧忠、永嘉玄覺,形成禪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兩家弘傳最盛。南岳下數傳,形成溈仰、臨濟兩宗;青原下數傳,分為曹洞、云門、法眼三宗;世稱“五家”。其中臨濟、曹洞兩宗流傳時間最長。臨濟宗在宋代形成黃龍、楊岐兩派。合稱“五家七宗”。慧能弟子法海集其言行為《六祖壇經》,是為南宗。神秀于弘忍寂后,至荊州當陽山玉泉寺弘禪,20余年中門人云集,是為北宗。神會先后在南陽、洛陽大弘禪法,南宗遂成禪宗正統,惠能宗風獨尊于天下。神秀北宗則門庭寂寞,傳不數代即衰亡。
二、禪宗主要思想解析
禪主要是人的一種精神修持方法,是信奉者的一種體悟真理或最高實在的方法,是其擺脫外界干擾,保持內心平靜,獲得智慧,獲得解脫的方法。禪宗因主張修習禪定而得名。它的宗旨是以參究的方法,徹見心性的本源。禪宗所蘊含的對本性的關懷,以及由此出發而展開的處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覺觀照、審美情趣、超越精神,體現出人類精神澄明高遠的境界,從而保持著相當持久的魅力。
要較為全面地了解禪宗思想,必須要追溯其淵源。《禪宗思想淵源》具體地論析了佛經對禪宗思想的影響。從此書中可以看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如來藏思想、揭示本心迷失緣由的唯識思想、以遣除掃蕩之不二法門為特色的般若思想、強調事事無礙的華嚴圓融思想等。禪宗思想提倡心性本凈,佛性本有,見性成佛。主要的依據是達摩的“二入”、“四行”學說。“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是憑借經教的啟示,深信眾生同一真如本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蓋,不能顯露,所以要令其舍妄歸真,修一種心如墻壁堅定不移的觀法,掃蕩一切差別相,與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無為。這是該宗的理論基礎。行入即“四行”: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與稱法行,屬于修行實踐部分。惠能繼承這一學說,在《六祖壇經》中主張舍去文字義解,直徹心源。認為“于自性中,萬法皆見;一切法自在性,名為清凈法身”。一切般若智慧,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若識自性,“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提出了“即身成佛”的“頓悟”思想。其禪法以定慧為本,定慧也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指“定”,“生其心”即“慧”。惠能從“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經文中,悟出了定慧等思想。禪宗的一切思想,皆從此義引申擴充而來。
三、禪宗思想對古典園林的影響
(一)對園林意境的影響
一個好的園林,必然會令人賞心悅目,賞心悅目的結果是身心俱暢。“賞心”是意旨的、含蓄的,“景”屬于物質形態的范疇。唐人王昌齡在《詩格》把“境”分為三類:物鏡、情境、意境。物鏡是指自然山水的境界;情景是指人生經歷的境界;意境是指內心意識的境界。按照王昌齡的說法,園林中用來“悅目”的景觀體現物境與情境的融合,而“悅目”之后帶來的“賞心”效果則體現了情境與意境的融合。
意境作為一種審美追求,自古以來一直為中國的文人雅士所神往,已經深深積淀于中華民族的藝術心理之中。禪宗對園林藝術的影響必然體現到了對意境的影響。早在唐宋時期禪宗思想對意境理論與實踐進行了大舉滲透并打下深深的烙印。主要表現在唐宋文人、藝術家對禪意的追求,在藝術創造中漸漸出現了一種意境和禪境交融一體的審美崇尚。“空寂”、“空靈”的韻味漸漸成為藝術意境的一種重要的美學追求。正是禪宗對“空”的解悟,形成了禪宗特有的思維方式及理論體系。受禪宗“心”所感知的世間“萬法”皆虛幻的影響,中國園林藝術鄙棄刻意模擬和機械復制客體對象的粗俗,追求情景交融、心物合一、虛實統一的藝術境界。
(二)對園林美學的影響
禪宗充滿著對自然山水景物的意趣。山水花木等大自然景象經常被用以暗示禪境,禪悟也普遍在自然景象中觸發。若以禪的眼光看待自然,則自然之境與禪境無異,所謂“青青翠竹,總在法身,郁郁黃花,自在般若”。自然山水,園林環境,可以使人感受到不受外界束縛的天然性情,故而禪悟與山水、園林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禪道與自然之間,禪境與山水、園境之間靈犀相通,如此,園林設計中在審美觀念或情趣上滲入禪宗思想,也就順理成章。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種以禪宗思想為基礎的審美觀念,牢固地根植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也植根于中國古典園林的造園活動中。中國園林的山水性情,飽含自然情趣,它的藝術魅力,全在立意深邃,造景奇妙。在禪宗的濡染下,中國園林從“物我同一”、“虛靜空靈”提升至美學追求的高度,形成了它特有的寫意化的自然之美和詩畫般的空靈之美。那種物我兩忘,以小見大,以芥子納須彌的境界,給人以物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享受。在世界造園系統中,這種寫意的、空靈的境界獨樹一幟。
(三)對園林空間構造的影響
禪宗對有限與無限的自然空間的體驗,為園林這種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藝術提供了審美體驗的無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與大自然的根本界限。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構筑了文人園林中以小見大、咫尺山林的園林空間。在禪宗看來,能勝多,只有簡到極點,才能余出最大限度的空間去供人們揣摩與思考。人們可以從微小精致的景觀中見到廣闊渺遠的宇宙,感受“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國”的美妙,體味“天地一東籬、萬古一重九”的永恒。充滿禪趣的文人園林多顯露出以小為尚的傾向,特別是在明清時期園林面積一般不大,經過造園者的精心構思、巧妙安排,空間有限的園林就能“小中見大,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尋之峻”。
(四)兩者相互交融
在園林藝術發展歷史中,關于審美特征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到禪的精神影響是如何通過文人士大夫審美情趣的變化,滲透到園林藝術創造中的。禪宗對中國園林文化的影響既深且遠,與儒道并立。同時,對中國民族文化反思時是回避不了禪宗的。對于園林美學而言,是中國文化具象化了的,相對于詩、畫等純藝術,園林藝術中的實用成分使它獨具文化特色。一方面它的物質形態增加了我們探詢期間的文化心理因素的難度,另一方面園林藝術的實用成分,也就是園林與人的日常現實生活的密切關系,卻也使它與人的文化心理的聯系,更為生動可感,更為自然切近,成為實用文化心理自然流露的產物。
從這個意義上講,園林藝術又比那些純藝術門類更直觀地反映了當時特定的文化心理、精神信息。保留至今的古典園林,成為讓觀賞的現代人身臨其境地體味前人心靈的暢游地。抽象的東西在這里完全生活化、具象化。對于禪宗這樣的人生藝術來說,園林是極好的體現場所。因此,體現在園林中的文化也更值得我們探索研究。
四、結語
中國古典園林中充分體現了禪宗思想的哲學特征與精神,并與禪宗的思想匯合一起,形成一種文人特有的恬靜淡雅的趣味,浪漫飄逸的風度和樸實無華的氣質與情操,這也就促成了中國古典園林情景交融的美學與哲學精神。
今天,人們生活在快節奏的技術化時代,心理疾病、精神空虛已成這個世界的常見病之一,人們的心靈常感無家可歸。充滿禪意的城市園林,能給當今的人們一片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所以,在現代園林的規劃和設計中,進一步繼承和發展禪宗美學這一古老偉大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彭一剛.中國古典園林分析[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6.
[2]黃河濤.禪與中國藝術精神的擅變[M].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4.
[3]萬葉,葉永元.園林美學[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1.
[4]夏照炎.意境概說[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
[5]方立天,華方田.中國佛教簡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TU986
A
1005-5312(2015)02-01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