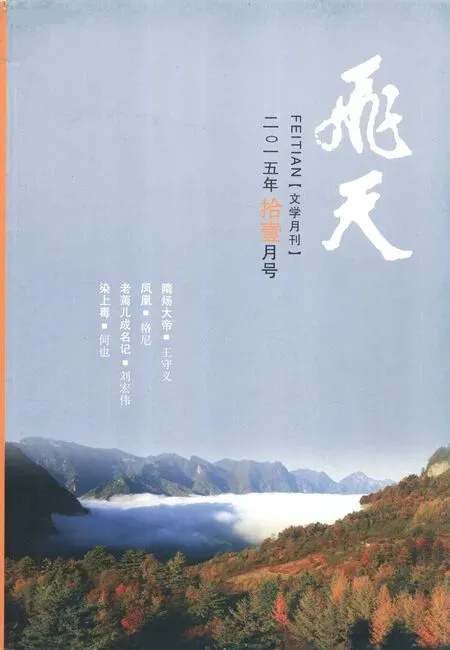那一抹站立的風景
李瓊
那一抹站立的風景
李瓊

人的一生都會經歷同樣的遭遇:出生——死亡,只不過所用的時間長短不同罷了,有的人從出生到死亡只有短短的幾天或者幾年,有的人或許是幾十年或者更長,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它如同種子一般植入人的腦海里,隨時隨地都會生根發芽。在又一次看到街頭廣告欄的訃告時,心中只能感嘆著生命的無常,感嘆著那生離死別的一瞬。可是,誰又能抗拒得了生生世世的輪回呢?亦如春天之景象,花開花落,年復一年,時光的腳步永遠也不會因為誰的悲憫之心而停留,唯一留下的是大浪淘沙后沉淀下來的厚重和精華,這些由最簡單的善良、最平凡的關愛、最樸實的執著而構成的精華,猶如一道難忘的風景,深深雕刻在記憶深處。
遙望著秦巴深處綿延的大山,那山是蕭瑟而沉寂的,看不見一絲春的氣息,在那山的胸腔里,悄悄孕育著春天的希冀。朝陽如母親溫暖的大手,緩緩地拂過山梁,仿佛在安慰淘氣的孩子。山坡上那一片片農田中已有了勞作的身影,那是在黑土地里尋找希望的人們,整地、送糞、挖地邊,將昔年的失望和不舍隨著裊裊青煙,飄散在廣袤的天邊,再把那份期盼深深地種在并不肥沃的土地里,用汗水和勤勞精心培育,朝朝暮暮地陪伴,不離不棄地等待,一顆忐忑之心惶惶地揣測著秋天的結果,那種癡迷和執著深深地刻在了如年輪般的皺紋里,一道又一道,直至生命終結的那一刻。恍惚中又回到了秦巴深處那座高高的山梁上,那里散落著三三兩兩的人家,一棟古老的瓦屋被煙熏得黑漆漆的方椽子,墻壁上嵌著方格木窗欞,檐下露出的梁上有浮雕畫扇,檐口上是一排滴水狀的檐瓦,依稀還能看到曾經的輝煌。裊裊炊煙在挺直而滄桑的屋脊上飄蕩,一抹清瘦的身影佝僂著背,在柴堆旁摟著柴草,那是我的奶奶,曾經日復一日不知疲倦地勞作著,為一家人的生活忙碌。每天清晨,奶奶第一件事就是給我做早餐,送我去上學后,跟著大家一起下地干農活;那時農業社吃大鍋飯,隊長一聲令下,安排干什么,社員就得干什么,放工后才能干點拾柴打豬草的活。可想而知,當年的奶奶是多么忙碌。
我生活在一個特殊的家庭,家中除了爺爺奶奶外,還有兩個叔叔,其中年長一點的叔叔是爺爺領養的;父親是奶奶的長子,也是母親家的上門女婿,母親因病去世后父親不愿再回奶奶家,只把年幼的我送了回來,于是我便加入了這個特殊家庭,鳩占鵲巢,堂而皇之地享受著爺爺奶奶的養育和愛護,甚至還剝奪了本應小叔享受的母愛。于是,體弱多病的我在爺爺奶奶善良無私的愛和寵溺中漸漸長大。有關父母的點滴漸漸模糊,特別是母親長的什么樣都不記得,記憶里只有爺爺奶奶那消瘦而布滿皺紋的臉龐和被歲月壓彎的脊背,以及那深入骨髓里的憨憨的善良。在我記事的時候,知道山下的河邊有一個孤獨而年邁的老人,生活在一座水磨坊旁邊,奶奶說他是我的太爺爺,奶奶去磨坊磨面的時候會帶著我和小叔一起去。在奶奶磨面的時候,我和小叔就會去太爺爺家里玩。太爺爺脾氣古怪,而且很吝嗇,吃的東西寧愿放壞了也舍不得給別人吃,年幼的我們很惡作劇,常常會惹得奶奶替我們挨罵。山里人都用竹子編竹簍來盛放東西,收了核桃包谷都放在竹簍上,在火塘里生上火慢慢地熏干。那時沒有市場,收獲的東西只能作為家庭生活的必須品,所以太爺爺固執地不肯拿出來給小孩子糟蹋。在磨坊里待久了,便耐不住寂寞,也或是肚子餓了,去太爺爺家里最多是在火塘里燒土豆,坐在火塘邊上,仰望著竹簍縫隙里的核桃,饞得人口水都要流下來了,但太爺爺不為所動,只給我們燒土豆吃。于是,小叔趁太爺爺不注意的時候,拿著長竹竿在竹簍的縫隙里搗幾下,啪啪掉下來幾個核桃,我和小叔趕快撿了核桃就躲到院子里,用石頭砸開來解解饞。反復幾次,終于被太爺爺發現了,一頓臭罵,連帶著奶奶也被罵了。唉,吝嗇的老頭!奶奶磨完面后,又給太爺爺洗衣服做飯,甚至從山上的家里,大老遠地給太爺爺送吃送穿,幼小的我們很是困惑,也不理解個中緣故。多年后還為他的吝嗇耿耿于懷。爺爺告訴我,奶奶是太爺爺家抱養的,抱養了奶奶后,太爺爺家又生了兩個男孩,就是我的舅爺。從那時起他們就對奶奶不好,非打即罵,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讓奶奶起床生火燒水,為一家人做早餐,一邊帶弟弟們,一邊做家務。奶奶成年后招了上門女婿,等到生了我父親的時候,就被太爺爺從家里趕了出來,而且還不讓帶走我父親,是太奶奶把父親偷偷領到后門口讓奶奶帶走的。善良的奶奶從不說當年太爺爺是如何虐待她的,只記得太爺爺對她的養育之恩。在太爺爺年邁的時候,是奶奶盡了贍養義務,并為他養老送終。當年奶奶為了照顧垂暮的太爺爺,在那一道山梁上留下了無數的足跡,這些足跡也深深地烙在我心里。在此后的歲月里,每每走過山梁上的那條羊腸小道,奶奶匆匆的腳步聲依稀回蕩在耳邊,那日漸佝僂的背影恍惚還在眼前,仿佛遠去的是歲月的年輪,只有奶奶那顆善良的心如彩虹般在時空里穿梭,照亮我人生的旅途,也時刻警醒著我的良知,忘掉該忘掉的,只把那份人間無私的愛和善良深深地根植在心中。
記得奶奶常說的一句話是“吃虧是福”,她也是潛移默化地用行動在實踐著這句樸實的真言。在我的記憶里,奶奶從未與鄰居發生過口舌之爭,而且盡己所能地幫助別人,給鄰居家照看孩子、喂豬喂雞;鄰居家的孩子放學回來,不回自己家,挎著書包先在我家吃完飯才依依不舍地離去;鄰居家孩子闖了禍被大人打了不敢回家,奶奶會護著他們,管吃管住;他家大人知道孩子一定在我家,很放心地找都不用找,知道奶奶會給送回去的。記得那時候鄰居下地干活,家里也是從來不鎖門的,因為有奶奶給照看著。奶奶的熱心在那個小山村是出了名的,在農業社吃大鍋飯的年代,每家的口糧都很緊張,連自家人都不夠吃,可奶奶從不吝嗇,每每有過路的人來歇腳吃飯,都會給做飯吃,開水管夠;就是叫花子來要飯,沒有熟食,米面也會給得足足的,生怕人家會挨餓。爺爺有時不耐煩嘮叨奶奶窮大方,可奶奶總是說出門在外不容易,只有懶窮的家沒有吃窮的家,于人方便也是與于方便。就是有人借了東西不還,被人偷了園子里的菜,她也不會聲張,也不許我們計較,總是用那句“吃虧是福”來告誡我們。奶奶不識字,也講不出大道理,沒有侃侃而談的華麗辭藻,沒有喋喋不休的說教,但她的行動卻在詮釋著簡單的愛,也是用行動給我上著人生的第一課。在奶奶慈祥的目光里,為我播種的是善良,收獲的是濃濃的溫暖,因而我此后的路走得平坦而順暢。
歲月流轉,時光變遷,當年我帶著對奶奶深深的眷戀、對小山村的不舍,踏上了人生另一段旅途——參加工作,此后陪伴奶奶的時間是少之又少,節假日回家也是來去匆匆,而思念的藤蔓幽幽地滋長著,一頭牽著奶奶,一頭牽著我。在無數個過往的日子里,奶奶把愛濃縮成一道站立的風景,常常在黃昏時遙望著我離去的方向,那雙不再清亮的眸子里滿含著期待,每每有從山下趕場回來的人,先打問可曾看見她家那個丫頭。我每次回家時,在村里人的嘴里總能聽到一句話:“你奶奶剛才還在路口上等你來著!”當年因為自己的少不更事,對那一抹站立的風景未曾留意,同時也未曾留意奶奶日漸彎曲的脊背,總是理所當然地享受著奶奶無限的慈愛。暮然回首,時光偷走了容顏,歲月已暗淡了心情,不經意間也帶走了曾經擁有的綿綿親情,那一抹站立的身姿也永遠重疊在那道山梁上。
酒越窖越香,情越久越濃,思念越久越綿長。再一次回到曾經生活過的小山村,還是那條彎彎的小路,還是那座雄渾的大山,還是那道挺拔的山梁,卻再也看不見當年的人,聽不到熟悉的聲音,那座老屋也因歲月的侵蝕而改變了容顏。如果真的可以穿越,我真想回到曾經的歲月里,伴隨著親人匆匆的腳步,行走在那道山梁上,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