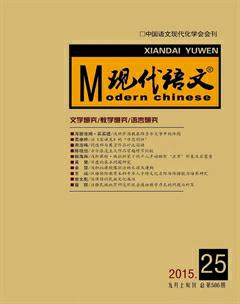古米廖夫詩歌中的中國形象
摘 要:古米廖夫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杰出詩人,現代主義流派阿克梅派創始人。他一生情系中國,并創作和翻譯了數首關于中國的詩歌。本文主要從比較文學形象學角度,分析了古米廖夫詩歌中的中國形象。
關鍵詞:古米廖夫 異域情調 中國形象
古米廖夫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杰出詩人,現代主義流派阿克梅派創始人。他有關中國詩歌的創作,一方面借鑒了這個東方神秘國度的傳說與神話,同時也與自身獨特經歷息息相關。古米廖夫就讀的皇村中學,正是俄國黃金時代詩歌先驅普希金就讀的學校。這里的中國式亭臺樓閣曾經深深吸引著普希金,并激發和喚起過他的創作靈感。與普希金相同,古米廖夫也未曾到過中國,卻在他短暫的一生始終情系中國,并在作品中數次提到中國。由此推之,這些跟中國有關的陳設與景物肯定也會給敏感的古米廖夫留下印象,激起他對中國的向往,同時也為古米廖夫中國意象的創作提供了樣本。
如果說兒時的皇村花園是他興趣的源泉,那么法國留學期間對中國文化的耳濡目染則成為日后古米廖夫創作中國形象的直接動力。詩人在巴黎留學期間,結識了俄羅斯畫家岡恰洛娃和拉里昂諾夫并和他們成為好友,這兩位畫家又恰好衷情于東方藝術和文化。這樣看來古米廖夫詩歌里中國形象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這些形象也反映出古米廖夫對中國的了解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
一、東方中國——和平安逸的王道樂土
法國學者卡雷將形象研究定義為:“各民族間的、各種游記、想象間的相互詮釋”[1],明確表現古米廖夫對中國形象整體詮釋的詩作主要見于創作于1909年的《中國之旅》,全詩譯文如下:“空氣在我們頭頂清新、哨響/犍牛把糧食運進谷倉/倒斃的羊羔交給廚子宰割/在銅勺里伏特加酒升起泡沫/究竟為什么煩惱把我們的心靈啃噬/為什么把我們的心靈折磨/最好的姑娘能給予的/也不會超過她所擁有的/我們大家都深知兇惡的痛苦/離棄一切神圣的樂土/同志們,我們大家都相信大海/能揚帆前往遙遠的中國/只是不要遐想!幸福將掛在好大喊大叫的白鸚鵡嘴上/茶園里皮膚黝黑的小孩/使我們的心扉充滿熾烈的熱情/在玫瑰色的浪花中我們將迎接遠方,大銅獅將使我們驚恐萬狀/夜間在棕櫚旁我們將夢見什么/清馨的樹汁將怎樣使我們迷醉/節日般快樂的時光/我們在海船上將歡度的那幾個星期……/在醉心的事業中你難道沒有體驗/臉色永遠緋紅的,我們的教師拉伯雷/胖大肥重的,仿佛大桶卡托酒/把自己的智慧用斗篷掩蓋吧/你將成為中國少女的稻草人/腿上纏以綠色的常春藤/當船長吧。我們請求!我們請求!/替代木漿我們把命運托付給長竿……/只要能在中國拋錨停泊,縱然在旅途中我們遇到死亡!”這首詩表達了詩人對于“到中國去”的強烈渴望,由此確立了古米廖夫筆下中國形象的基調。與古米廖夫其他異域題材詩歌往往記錄詩人漫游經歷不同,本詩并不是他前往中國旅游的真實記錄。這里與其說是書寫,不如說是“想象”更恰如其分。
從創作背景看,本詩屬于古米廖夫初期作品。此時詩人剛二十出頭,年輕氣盛,富有無限浪漫主義激情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愿望。年輕的古米廖夫此時已從巴黎回國,并且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非洲之行。“白鸚鵡”“茶園”“皮膚黝黑的小孩”“大銅獅子”“棕櫚”“清馨的樹汁”“綠色的常春藤”,在形象的塑造上運用的是形象學方法中書寫異國情調的一種慣用模式——空間的斷裂,即攝取那些在被注視者文化中被視為風景秀麗的自然美景,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享受異域美景。從被注視者角度看,這些意象并不是典型的中國形象。也許是深受詩人非洲之旅的影響,古米廖夫把中國幻想成一個熱帶王國,也可以被認為是歐洲人眼中東方情調的代表。詩歌中的“中國”,與其說是中國,不如說是詩人自己構建的一個王道樂土,一個神圣不可侵犯的彼岸世界,而這個樂土與世界正是與西方現實世界截然對立的。這里我們并不是要討論詩人構建的中國形象與現實之間的真偽,更多關注的應是形象塑造背后的主體因素。即古米廖夫作為注視者在傳遞言說中國這個他者形象的同時,傳遞的一種自我形象。
我們知道,西方人自古以來就熱衷于對異國的探索。自從馬可·波羅出版了他的游記后,歐洲人就把關注點逐漸轉向了古老的東方中國。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東方為打破西方的禁忌提供了可能性或想象的余地。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從17世紀開始,“異國主義”變成了烏托邦的一個重要成分。西方人對異國的探索,主要是尋找一種與自己社會不同的異域,尋找一種原始社會,藉以擺脫原罪的重負,代替對上帝的尋找,同時也是為了批判自己的社會和文化,因為盧梭等人就認為歐洲文化把西方人變成了非人道的人。[2]然而從19世紀開始,隨著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西方人不再將中國視為文明典范,而是令人生厭的、可怖的和社會陰暗的反映,對中國持一種蔑視嘲笑的態度,這點可以從歐洲世紀末小說把中國視為屈辱對象那里得到印證。
既然如此,為何古米廖夫對未曾謀面的異域中國如此高歌頌揚?僅僅是為了滿足內心的好奇,還是另有原因?
回顧古米廖夫的經歷,他對中國的了解除了上文提到的在他成長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皇村中學外,更多來自書本閱讀或友人談資,同時與他所處時代密不可分。古米廖夫被視為阿克梅派創始人,阿克梅派正是從俄國象征主義中分離出來的一個派別。盡管阿克梅派的正式成立在1913年,但古米廖夫在1905-1910這段時間的創作已經開始實踐他意欲擺脫象征主義理論的嘗試。“異域情調的描繪不僅是創建‘他人世界的一種方式,而且還是與象征主義進行論爭的一種手段”[3]。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形象的塑造被賦予了更廣闊的意義。盡管這種塑造還不成熟,還有明顯的象征主義詩風影響。
在法國學者米利耶·德特利看來,西方文學中這些幻想的美好中國形象恰恰表明了詩人對現實的不滿和厭惡,“中國只是浪漫主義詩人理想的合適的代名詞,一個夢幻的自由空間,在那里詩歌是合理的行為,遠離日常生活的平庸和拘束”。[4]王向遠也有過類似的觀點,“時空視差是造成涉外文學中將異國異族理想化、觀念化,并使之成為‘烏托邦文學的必要條件之一。當作家們不滿本國的社會現實的時候,就可以渲染、美化異國情調,將某一外國或外國文化作為理想寄托”。[3]說古米廖夫筆下的中國形象是與西方社會格格不入也好,還是對象征主義的一種反抗手段也罷,對中國向往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為中國是他閱讀和想象的結果,所以才造就了古米廖夫在中國形象塑造上的“不真實”。而且這種形象不是“復制式想象”,而是一種“創造性想象”。
二、中國姑娘——溫順惆悵的美好女性
“中國人”伴隨著“中國熱”曾經給歐洲人增添了無盡想象。18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近代中國的衰落,歐洲人對中國由贊美轉向批評者居多,中國人在歐洲人作品中大多是貪婪、自私、愚昧、丑陋的形象。古米廖夫詩作中的中國人主要是作為正面形象出現的,典型例子可見于發表于1914年的《中國姑娘》,全詩譯文如下:“蔚藍色的涼亭/聳立在河心/像編織的鳥籠/里面飼養著黃鶯/從這座涼亭/我觀賞朝霞/枝葉怎樣婆娑/有時我也觀賞/枝葉怎樣婆娑/輕舟怎樣滑行/環繞著/聳立在河心的涼亭/而在我的深閨/擺著一束瓷玫瑰/一只金屬小鳥/尾巴金光閃耀/我不相信這種誘惑/在絹帕上我寫下詩章/心平氣和地訴說/自己的愛情和憂傷/我的未婚夫愈加使人迷戀/盡管他禿頂和疲憊/可不久前他在廣東/考試門門及格”。此詩是詩人關于中國古代女子閨中生活的想象之作,類似于我國古代的閨怨詩。詩人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展示了閨中女子的心理活動,把孤單寂寞的少女比作“鳥籠里的黃鶯”。
同類題材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我國古代閨怨詩的代表——王昌齡的《閨怨》,“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同樣是寫女性,只是相對于古米廖夫,王的感情基調更有層次,起先“不知愁”接著又“后悔”。以樂景襯哀情,流露出的是少婦快樂表面下暗藏的寂寞。反觀古米廖夫的《中國姑娘》,從頭到尾如一股緩緩的暗流。就像詩中所述“心平氣和地訴說/自己的愛情和憂傷”。這個中國姑娘應該更加沉默和空虛,但是不會言說,也許愛情本身在詩人看來就伴隨著明媚和憂傷。“盡管他禿頂和疲憊/可不久前他在廣東/考試門門及格”。在這里我們看出古米廖夫想象的“未婚夫”其貌不揚,從“禿頂和疲憊”可知這是一個了無生氣的老者形象。而詩中的“中國姑娘”應該是年輕而富有朝氣的少女,這種“不對稱的婚姻”和寂寞的婦女形象類似于列夫·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寧娜》中安娜和其丈夫卡列寧,而我國古代對“未婚夫”形象的描寫可以參考《陌上桑》中羅敷的丈夫“為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這種形象是令少女愛慕的青年才俊。“可不久前他在廣東/考試門門及格”,可以看出古米廖夫對中國古代以科舉功名作為擇偶標準的認知和解讀。
古米廖夫是否讀過王昌齡的《閨怨》不得而知,但是他接觸閱讀過“閨怨詩”這一中國傳統詩歌題材是毋庸置疑的。古米廖夫曾經從法文轉譯過包括李白杜甫詩歌在內的中國詩集,這也是他詩歌中中國形象塑造的重要來源和想象根基。但相比《中國之旅》,《中國姑娘》已不再是意象的表面堆積,逐步上升到對中國“閨怨”題材的模仿。但這種“年齡差距的老少戀”,恰恰說明古米廖夫對于中國古代婚姻制度是沒有完全理解的,在模仿的過程中不自覺地作了俄國化的解讀。
1921年古米廖夫因為涉嫌“反革命陰謀案件”被蘇維埃政府當局處決,1986年在其百年誕辰時才被恢復名譽,在蘇聯文壇掀起了“古米廖夫熱”。至于他是否曾參加反革命,目前仍然沒有統一說法,這也造成了古米廖夫在中國接受和傳播的停滯,長時間沒能得到足夠的介紹和關注。有關他的原始資料一直沒有公布,至于他的詩歌作品更是少人問津。
我國學者樂黛云說過,“人們由于無法解決現實生活之中的問題和不滿,就會構造一個‘非我來與‘自我相對立,把一切理想的、圓滿的,在‘我方無法實現的品質都投射于對方,構成一種‘他性而使矛盾得到緩解。這里起主導作用的不一定是對方的現實,而是我方的需求”。[5]古米廖夫筆下的中國形象就是如此。無論是作為王道樂土的整體形象,還是作為中國姑娘的人物形象,古米廖夫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進行的這種跨文化解讀和想象,體現的正是作為想象者欲望的一種詩意。古米廖夫詩歌中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被西方創造出來的東方主義的具體代表,具有某種烏托邦性質。“借東方酒杯、澆西人塊壘”,這也許是古米廖夫創作中國形象的意圖所在。
注釋:
[1]轉引自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
[2]顧彬:《關于“異”的研究》,轉引自張鐵夫:《群星燦爛的文學——俄羅斯文學論集》,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頁。
[3]石國雄,王加興譯,[俄]弗·阿格諾索夫:《白銀時代俄國文學》,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頁。
[4][法]米利耶·德特利:《19世紀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轉引自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頁。
[5]王向遠:《比較文學學科新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頁。
參考文獻:
[1]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黎華譯,[俄]古米廖夫.古米廖夫詩選[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2003.
[3]張冰.白銀時代——俄國文學思潮與流派[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4]劉文飛.20世紀俄語詩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5]張鐵夫.群星燦爛的文學——俄羅斯文學論集[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
[6]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
[7]石國雄,王加興譯,[俄]弗·阿格諾索夫.白銀時代俄國文學[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8]谷羽.詩人古米廖夫筆下的中國主題[J].中華讀書報,2011,(6).
(張艷婷 山西大學文學院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