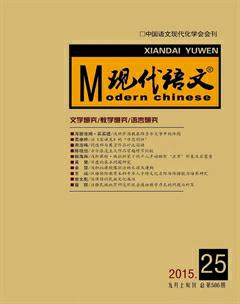“知道”的歷時演變


摘 要:關于“知道”由單音節詞復合而成雙音節詞的過程,學界關注尚少。本文主要探討單音節詞“知”“道”合成雙音節詞“知道”的歷時演變過程。通過查找語料可知,表示“明白、了解”之義的雙音節詞“知道”在南北朝時產生。
關鍵詞:知 道 知道
一、知
“知”在先秦時期作為單音節詞已經廣泛獨立使用(見表1),有動詞和名詞兩種詞性,一直沿用至今。大徐本《說文解字》:“知,詞也,從口,從矢。陟離切。”“矢”是箭的意思,因此段玉裁注為“識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知”甲骨文中寫成“”,金文中更加象形,加了“曰”旁,寫成“”,小篆中寫成“”,隸書中寫作“”,楷書中寫作“”。漢字經過了6000多年的變化,從商代甲骨文到魏晉的楷書中,“知”的字形變化始終與表示言語義的“口”相關。由此可知,“知”的本義為對于認識、了解的事物,可以脫口而出。
古人一直認為控制指揮人思維的是心臟,而不是今天科學研究所認為的大腦。人的內心對外在客觀世界有了自己的想法、感受,需要通過嘴巴表達出來,在心為“感受”,發之為“聲”,出口為“詞或者語句”。通過這一過程,可以把段注“識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和大徐本《說文解字》:“知,詞也。”聯系起來,即“知”的本義為從心到口的一個言辭過程。“知”的動詞和名詞兩種詞性相伴出現,言辭過程中的動作就是動詞“知”,言辭過程中說出來的內容就是名詞“知”。之后“知”的這兩種詞性廣泛運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內在的自我認識和外在的客觀世界的認識能力也在提高,動詞“知”和名詞“知”的詞義有所擴展延伸。
表1:“知”在先秦文獻中的出現次數
《黃帝內經》 293 《春秋左傳》 290 《莊子》 291
《禮記》 127 《管子》 206 《韓非子》 228
《尚書》 31 《老子》 136 《墨子》 157
《周易》 25 《論語》 72 《國語》 104
(注:該數據從山西大學圖書館國學寶典語料庫中所得,本表摘取了使用頻率較高的文獻,一些使用頻率較低的文獻未摘取,本著能夠說明“知”在先秦已經廣泛使用這一問題。下同。)
二、道
“道”在中國文化中可謂最重要的字眼之一。從先秦起,“道”作為單音節詞已經被廣泛獨立使用(見表2),有動詞和名詞兩種詞性,一直延續至今。“道”在金文中寫成“”,從行(街道),從首,表示人在路上行走之意;金文亦寫作“”或“ ”,另加了一“止(腳)”,更突出行走之意。在小篆中寫成“”,大徐本《說文解字》:“道,所行道也,從辵從首,一達謂之道。徒皓切。”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行道也。毛傳每云行道也。道人者所行。故亦謂之行。道之引申為道理。亦為引道。首者,行所達也。首亦聲徒皓切。古音在三部。”這就是說,“道”由“辵”和“首”兩部分組成,前者表行走之意,后者即表意又表音。那么,“道”的本義是指人或動物行走時腳底所留下的痕跡。從“道”的本義出發,不斷擴展“道”的內容,那么“道”的內容經歷了這樣一個不斷豐富的過程。
“道”的外延越向外延展,“道”越具有不可言說的神秘感。所謂“道恒無名”(《老子·第三十二章》),“道不當名”(《莊子·知北游》)。
“道”除了名詞的引申,還有動詞的引申。由“道”的本義可以得知,動詞“道”最后要達到使某事物順暢的效果。在這一點上,名詞“道”和動詞“道”發生了聯系,動詞“道”于是有了知道、言說之意。那么“知”和“道”后來同義連用也就理所當然了。
(1)零淚無人道,相思空何益。(南朝梁·吳均《詠雪》)
(2)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詩·鄘風·墻有茨》)
(3)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晴。(唐·劉禹錫《竹枝詞》之一)
“道”除了作為實詞的用法之外,還有虛詞的用法。相當于助詞“得”。
(4)鞍轡鬧裝光滿馬,何人信道是書生?(唐·白居易《和高仆射》)
(5)怨苦知多少,兩三人只道同做餓殍。(元·高明《琵琶記·五娘葬公婆》)
表2:“道”在先秦文獻中的出現次數
《黃帝內經》 187 《墨子》 107 《莊子》 209
《禮記》 184 《呂氏春秋》 172 《韓非子》 185
《周易》 69 《荀子》 151 《孟子》 71
三、知道
“知道”一詞在先秦時期已經出現,使用頻率不高。從三國兩晉南北朝開始,使用頻率激增。(見表3)
表3:“知道”在各朝代出現次數
先秦 漢 三國兩晉南北朝 隋唐 宋 元 明 清
61 60 170 269 1182 1205 3617 14184
“知”和“道”在先秦時期結合使用,并不表示今天所說的“了解、明白”之義。作為動詞的“知”獨自承擔著今天所說的“知道”之義,如《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作為動詞的“知”與作為名詞的“道”連用,構成動賓結構,最初表示“認識道路”之義,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五:“娥語曰:‘伯文,我一日誤為所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否?”隨后“道”的內容不斷擴展,逐漸表示通曉天道、地道、人道、事道等意。作為賓語的“道”有內容,即使是抽象的概念化的“道”。人們了解、明白了“道”之后,可以把這個“道”說出來,也可以不說出來,有時候即使想說,也不一定能說出來。這時,名詞“道”和動詞“道”就發生了聯系。為下文表述之清晰,這里把說出來的“道”稱為顯性的“道”,沒說出來的“道”稱為隱性的“道”。隨著“知道”使用頻率的提高,“知”和“道”的粘合度增強,“道”作為動詞有言說之意。隱性的“道”使用比顯性的“道”頻繁,與動詞“知”同義連用,“道”的言語義逐漸弱化,共同表示“明白、了解”之義,這一用法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出現,如僧祐《弘明集》卷八:“夫圣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后判者,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明之照。”
這時“知道”等同于“曉得”,“知”對“曉”,“道”對“得”。正好和本文第二部分“道”作為助詞相當于“得”這一用法相吻合。這一結構在使用過程中逐漸凝固,一直沿用至今。在這一演變過程中,“知”作為謂語一直穩固地表示“明白”之義,不因“道”的變化而發生變化(見圖1)。
圖1:“知道”的歷時演變過程
四、結語
“知”在先秦時期作為單音節詞已經獨立廣泛使用,從“知”表示由心到口的一個言辭過程的本義,得知“知”的動詞和名詞兩種詞性是相伴而生的。“道”在先秦時期作為單音節詞也已經獨立廣泛使用。有名詞和動詞兩種詞性,但是這兩種詞性的出現有先后順序,動詞“道”是在名詞“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從“道”表示人或動物行走時留下的痕跡這一本義出發,名詞“道”的內容不斷豐富擴展。由于“道”的內容容易給人們一種把某物理順、通暢的感覺,所以可以把名詞“道”和動詞“道”緊密聯系起來,動詞“道”于是有了“言說”之義。“道”還有作為助詞“得”的用法。
單音節詞“知”和“道”在先秦時期已經結合使用,但是使用頻率不高,只是作為動賓結構出現。漢代之后,“知道”出現的頻率提高,南北朝時期“知道”緊密結合為一個雙音節詞,“知”和“道”同義連用。之后,隨著使用程度的加深,“道”有了虛化色彩,相當于助詞“得”,可以與“曉得”一詞相對應。這一用法一直沿用至今。
參考文獻:
[1][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2011.
[2][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王雯雯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學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