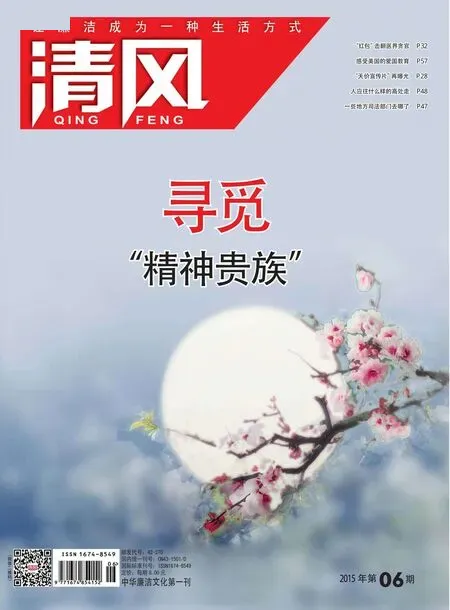“象牙塔”里的精神守望者
文_本刊記者 王義正
“象牙塔”里的精神守望者
文_本刊記者 王義正
大學等學術氛圍比較濃厚的地方被稱為“象牙塔”,因為這里是精神的殿堂,這里向社會輸出人才,也輸出精神。近年來,“象牙塔”卻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污垢頻現,讓人擔憂。然而,“象牙塔”中,不乏能夠堅持自我的人,他們醉心于學術,不過分追求生活享受,敢于堅持,更敢于放棄,因為在他們內心中有更重要的東西。
“北大教授”的另類選擇
雖然文人窮苦不是必然,但總歸要知得柴米油鹽貴,知得艱難困苦,才好保持思維的敏銳,所以清貧不是文人追求的,卻是對文人有益的。

2003年7月,張京華決定扎根位于永州的湖南科技學院,這并不是張京華的第一次“轉移”——上一次是從北大到洛陽。由于研究方向為“中古史”,北京雖然也是古都,但主要是明清時期,相比洛陽這座隋唐名城,后者與張京華的學術研究“更近”。2009年,張京華毅然離開北京,前往洛陽。
這個1979年考入北大后就不曾離開(畢業后留校任教,并被破格評為副教授),一待就是20年的“老北大”實在讓人有些琢磨不透:他放棄了北京的繁華,放棄了北大帶來的光環,一門心思往“窮鄉僻壤”鉆。
張京華本人對此卻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他所追求的學術研究。“如果在北京,工資可能很高,課題很多,但學術成果不會有在永州這么多。”張京華告訴本刊記者。
來湖南12年,也讓張京華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每天我會擠出6小時的時間讀書,并且沒有周末,所以每月有180個小時,每年有2000個小時,在湘10余年我有2萬小時的讀書時間,點校古籍、推敲觀點、撰寫論文,出版了20種書,交稿待出版的還有8種。”張京華說,這才是他向往的生活。
研究學術,才能叫學者;離開了學術,就不再是什么學者了。當下,一些學者卻因為現實生活處境尷尬:一方面要執著于自己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世俗的瑣碎。在精神追求和物質收益產生分歧時,有的人放棄了自己的追求而選擇了“面包”。但張京華覺得,古人所說“詩窮而后工”自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文人窮苦不是必然,但總歸要知得柴米油鹽貴,知得艱難困苦,才好保持思維的敏銳,所以清貧不是文人追求的,卻是對文人有益的。”
在大都市、重點高校的學者,坐擁千萬身家的人恐怕不少,那么做研究可能就別有途徑。選擇一個相對安靜的地方,等于是把“權錢”放在了次要地位,二者孰得孰失,恐怕難于定論。“富而可求也,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求或者不求取決于時勢,取決于理想。這之間說不上是不是無奈,但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求仁而得仁,歸根結底是價值觀念不一樣,關鍵還在于不同的選擇。
今年張京華有一部自選集《在經學外圍》即將出版。今后十年,他還有撰寫《經學通論》和《詩經學》的計劃。“我是學歷史的,史學講究求真求實,實際上,追尋真實就是最大的學問。我們作基礎研究、古典研究的,不能使人富貴,不能有一點實際的用途,所謂百無一用。我們尤其不能更改歷史、重演歷史。但是我們可以揭示真實可信的歷史,可以求善求雅,可以梳理人類文明演進的歷程,為人們找到感情和信仰的寄托,從而使人獲得自信,以點亮指示未來的明燈。”張京華告訴本刊記者。
翰林后裔的書香氣質
在現實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選擇中,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否則要么被物化,要么會“走火入魔”。

2008年就退休了的鄭延國現在的主要任務是看看書,練練字,接孫女上下學,同時還接受了長沙理工大學的邀請,成為學校的教學督導團成員,在教育戰線上繼續發揮余熱。2015年5月13日,本刊記者前往鄭延國教授的家中拜訪。
鄭延國住在長沙理工大學教師公寓,與周邊其他的新建筑相比,教師公寓顯得“老態龍鐘”:樓下壞掉的信箱和貼滿小廣告的樓道給人一種年久失修的破敗感。對于一個大學教授、高級知識分子而言,這多少有些與其身份不相稱。
但當本刊記者進入鄭教授家中的那一刻起,以上印象頓時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撲面而來的“書香”。“我的祖父曾是清朝的翰林院編修,我的伯父曾是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鄭延國將自己定位為“翰林后裔,書香世家”。
多年來,鄭延國一直努力繼承和發揚這股源自家族血液中的文人氣質。鄭延國的家不可謂不簡樸,但卻十分整潔。客廳中的小方凳和老靠椅給人一種世俗繁華中難得的親切感,屋中隨處可見的書籍讓人心神安逸。
本刊記者進門時,鄭延國正在寫一篇“千字文”,他說最近十分鐘愛寫這種小文章。雖然已經退休,但仍然很關注一些英文方面的學術問題,兩會時國務院翻譯對“任性”這個詞進行了漢譯英,引發爭議。這也引起了鄭延國的思考,他結合自己多年的翻譯和教學經驗,寫了一篇文章,發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對于如何保持一個文人應有的氣質和精神,鄭延國有自己的看法。在古代,無論是士大夫階層還是所謂書香門第,大多都是衣食無憂,所以,吃飽肚子是前提。“我不贊同飯都吃不飽還過于執著于學問。”鄭延國告訴本刊記者,據他所知,湖南大學附近有一個中年男人租住在一個很小的房子里,吃飯很簡單,沒結婚,也不工作,天天關在屋子里研究“紅學”。“這不是在追逐夢想,而是不負責任。”在現實和精神的選擇中,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否則要么被物化,要么會“走火入魔”。
當然,這并不是否定文人應有的“氣節”;恰恰相反,當下的很多文人、知識分子缺的正是“氣節”。什么是一個文人的氣節?鄭延國提高了嗓門說:“我祖父就是為了這個去死的。”1944年6月,長沙失守,日軍強迫鄭延國的祖父鄭家溉出任維持會長,但被其斷然拒絕,“我是中國人,寧死也不能為侵略者賣力。”后來,鄭家溉被日軍逮捕,并最終被槍殺。
鄭延國指著桌子上的幾本古籍告訴本刊記者,這是他這幾天剛從圖書館借回來的,雖然現在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他很滿足,看看書,寫寫文章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在鄭延國的書房里,一位朋友送給他一幅字:“學以為耕,文以為獲。”身居陋室,一心學問,這是鄭延國生活的真實寫照,更是鄭延國一直的追求。
一個博士的“耕讀”本色
雖然清貧,卻讓我感到很踏實、很幸福,很滿足,很感念,也很珍惜!

2013年12月,謝孝明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獲得了博士學位,卻出乎很多人意料去了貴州省社科院工作。在朋友和同學們看來,他明明有很多“更好”的選擇,他卻選擇了一個“清水衙門”。
謝孝明告訴本刊記者,像社科院這類單位的工資水平本就不高,加上自己是新來的,目前每個月的收入在3100元左右。社科院基本上沒有其他福利,新來人員也沒有過渡房分配。因為單位沒有過渡房,自己目前又沒能力購房,所以他只有租房一途。謝孝明的孩子在貴陽一中上學,愛人在家照顧孩子。為了方便孩子上學,他們在貴陽一中附近租了民房,房租每月2000元,占去了他月工資額的三分之二,加之貴陽的物價特別高,所以他們的經濟還是很拮據的。
不過,謝孝明對此十分樂觀,因為他覺得能和家人在一起,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很快樂。“告別了十多年的學生生活,每個月有了三千多元的工資收入做生活保障,一家人能夠和睦愉快地生活在一起,遠方家鄉的老媽媽身體安康,自己可以靜下心來讀自己喜歡的書,做自己愿意做的事。這樣的日子,雖然清貧,卻讓我感到很踏實,很幸福,很滿足,很感念,也很珍惜!”謝孝明告訴本刊記者。
其實,在到貴州省社科院工作之前,他去過廣東的惠州學院,那邊招聘教師。惠州學院工資待遇是比較高的,剛去的博士月薪就有8000~9000元。“只是那里的學術氣氛不太濃,所以,我沒去惠州。”直到現在,還有不少地方院校和單位為了引進博士,給他開出了非常優厚的條件和待遇,如百萬安家費、一百幾十平方米住房、十萬年薪,等等。但謝孝明沒有動搖自己的選擇。
謝孝明坦言,自己也曾做過發財夢,也曾跟朋友一起開過飯店、辦過公司,但后來發現這些都不適合自己,也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可能是受湖湘文化熏陶和源自岳麓書院很多老師甘于清貧、不慕榮華富貴思想的影響,謝孝明的內心里更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安靜的人。
謝孝明常對他的朋友說,他有兩個本色始終不會變:一個是農民的本色,一個是書生的本色。這兩個本色對他一生的意義非常重大。農民的本色讓他永遠保持一顆謙卑、樸素、平等和感恩之心;書生的本色讓他始終要牢記國之四維,禮義廉恥,要知出處大節和遵守做人的道德底線。